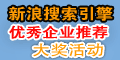| MBO與國資變局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6月12日 16:12 《智囊*財經報道》 | ||
|
文/趙波 只有強而有力的國家,才能推行新的有效的市場制度。 2003年4月6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在北京悄然掛牌。在此之前,財政部負責國有資產管理的國有資產評估處業已撤除,其相關職能正在向新成立的國資委
端倪已初步顯露。就在不久前,財政部發至原國家經貿委企業司關于《國有企業改革有關問題的復函》(財企便函【2003】9號)文件建議:“在相關法規制度未完善之前,對采取管理層收購(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行為予以暫停受理和審批,待有關部門研究提出相關措施后再作決定”,其原因是“由于法律、法規的制定相對于實踐活動有一定的滯后期,對這類交易行為現行法規和管理水平難以嚴格約束”,并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一些當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謀取不當利益”。 雖然財政部目前并未就此事形成專門文件下發全國,原國家經貿委相關部門也未有正式回應,通過官方媒體披露的這個信息還是給國內熱炒的MBO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已有業內人士認為,考慮到國資委的機構建設與工作開展尚需時日,財政部的這一舉措極有可能造成至少今年年底前事實上的MBO項目的難以審批。 這對于眾多熱衷嘗試管理層收購的國企與地方政府而言不啻于兜頭一盆冷水。就在此前,國內的眾多專家與媒體還在放言2003年將成為MBO年,MBO在中國的主流意識里已有上升成為一種先進的產權制度改革方式的趨勢。2003新年伊始,這種熱浪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我國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國有資產的有900多家,這其中的200多家正在積極探索管理層持股(收購)這一新的模式;MBO熱同樣波及到了大量的非上市公司,悄然間江浙地區早已暗流涌動并有多例MBO既成事實。 然而另類的質疑聲卻也頻頻響起。從國有資產的監管角度出發,這些質疑最終主要集中到兩個焦點問題:一是國有資產的轉讓定價問題(股價),一是收購者收購國有資產的資金來源問題。在已經實施MBO的公司中,普遍存在股票轉讓價格等于或低于帳面每股凈資產的現象,并且收購者對收購資金的來源大都諱莫如深。對于前者,不可避免的涉及國有資產的流失疑慮,而對于后者,同樣留給人們“空手套白狼”的巨大想象空間。 只是一種工具 是不是借助于專項的MBO基金以及信托機構的中介服務,就可以解決管理層收購的融資瓶頸與收購主體合法性問題?是不是通過市場定價、竟標等方式管理層以高于帳面每股凈資產價值的溢價收購,就會解決MBO在中國實施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是因為源于從技術角度來尋找答案,國內許多專家與學者才得以樂觀認為:相信在新的國資委相關政策配套推出后,MBO仍將大行其道,重現江湖。 果真如此嗎? 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有必要從MBO的歷史發展軌跡中尋求我們的立論根據,同時消除由于某些斷章取義對MBO造成的種種誤解。西方MBO的昨日,或許就是我們今天以及明天的一個縮影。 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五次大規模的購并浪潮,其動因與結果就是對資源的優化配置。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兩次并購浪潮,分別以形成橫向一體化的企業及縱向一體化的康采恩(康采恩:以實力最雄厚的壟斷企業為核心,以金融控制為基礎,把分屬于不同經濟部門的許多企業聯合在一起而組成,是壟斷組織中最復雜的一種形式。參加者形式上保持獨立,實際上受其中占統治地位的資本集團控制。即以一兩個特大型企業為核心,聯合了各方面各領域一大批企業所形成的超大型壟斷集團,它們簽定協議,共同銷售產品和采購原料,在商業上失去獨立性。)為主要特征,而始自20世紀中期的第三次浪潮誕生了龐大的混合聯合企業集團。可以說,前三次并購浪潮企業追求的是規模效應和市場份額的壟斷優勢。 然而企業規模膨脹以及多元化經營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管理難度增加及管理效率降低、經理主權凌駕業主主權之上等種種副作用。物極必反,作為大規模發生的集團化不佳表現的一種反彈,也是對初露崢嶸的知識經濟的一種回應,始自上世紀70年代,眾多的西方企業開始實施“回歸核心”戰略,這導致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第四次大規模購并:一些多種經營集團逆向操作,出售其非主導業務的子公司和分支機構,甚至從某些特定行業完全退出,以便集中力量發展核心業務;或者改變經營重點,將原來的邊緣產業確立為核心產業,從而出售其余部分業務(包括原核心業務)。在很多時候,公司總部更愿意將剝離出去的公司賣給原來經營公司的管理層,即所有權變更而管理層不變,這便是MBO。盡管MBO后來演變為反收購的有效工具,在很大程度上,MBO還是應該說是20世紀70年代公司分拆的產物。 然而,如果沒有衍生出來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譬如垃圾債券)作為前提條件,管理層同樣面臨難以籌措MBO所需的巨額資金的問題,正是杠桿并購這一最具投機色彩的金融創新,才使MBO成為可能。杠桿收購的興起與美國社會當時通貨膨脹、稅制修改、充足的金融市場條件密不可分,它提供的實際是一個企業高負債、高風險狀態下的資方溢價套現機會。從實證角度嚴格說來,在很多情形下,MBO只是杠桿收購所采取的一種策略或者形式,MBO必須通過杠桿并購這一金融工具來進行,這與我們國內絕大多數譯著以及專家學者從理論角度所稱的MBO是杠桿收購(LBO)的一種似乎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將MBO稱為LBO的一種,它就有意無意掩蓋了這樣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實質上,MBO絕不是目的,它只不過是資本運營(LBO)所借助的一個工具,它的過程只是LBO可能涉及的一個中間環節。在這背后隱含的是,企業已不再僅僅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物質生產單位,在資本的眼中,它已演變為金融投機(套現)的一個重要工具。 讓我們來看一看在杠桿收購領域曾經最負盛名的美國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公司的運作。 作為世界上最早運作MBO的公司,1975年,KKR決定收購羅克威爾公司的一個制造齒輪部件的分廠。KKR與被購分廠的管理人員攜手,以每股1美元的代價對該分廠實施了MBO(管理人員控股20%,KKR公司控股80%)。收購后由于改進了庫存品的管理,加強了收帳制度,削減了不必要的費用開支,而使公司的現金大量增加。5年后這家公司以每股22美元的價格賣與一家外國公司。KKR取得了豐厚的回報,當然,公司的9個高級管理人員一夜之間也都成了百萬富翁。 在這里,KKR的操作手法是,通過分析、研究來確定市場上那些營運業績不佳但卻極具發展潛力的公司作為收購目標,通過向外大舉借債(高負債的渠道主要是向商業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例如垃圾債券)收購目標公司,在取得目標公司的經營控制權后,通常是對目標公司進行分割整理,使公司形象改善、財務報告中反映的經營狀況好轉,待股價上升至一定程度后全部拋售大撈一把,還清債務后拂袖而去。很顯然,目標公司的管理層在其中只是布局的棋子,而一旦有礙全局大勢,就會被毫不猶豫的予以放棄。 這在KKR另一震驚世界的購并案雷諾.納比斯科(RJR Nabisco)公司的收購中表現的淋漓盡致。作為美國最大的食品和煙草生產商,雷諾.納比斯科公司是由美國老牌食品生產商Standard Brands公司、Nabisco公司與美國兩大煙草商之一的RJR公司(Winston、Salem、駱駝牌香煙的生產廠家)合并而成。雖然RJR Nabisco的食品業務在兩次合并后得到迅猛的擴張,但煙草業務的利潤豐厚,仍占主營業務的58%左右。由于感覺公司當時的股價被嚴重低估,1988年10月,以RJR Nabisco公司CEO羅斯·約翰遜為代表的管理層向董事局提出管理層收購公司股權建議。 管理層的MBO建議方案包括,在收購完成后計劃出售RJR Nabisco公司的食品業務,而只保留其煙草經營。其戰略考慮是基于市場對煙草業巨大現金流的低估,以及食品業務因與煙草的混合經營而不被完全認同其價值。重組將消除市場低估的不利因素,進而獲取巨額收益。 然而在新的競投對手KKR出現后,爭奪趨于白熱化。與CEO羅斯·約翰遜所計劃的分拆形成尖銳對照的是,KKR希望保留所有的煙草生意及大部分食品業務。雖然表面上管理集團的出價最高,然而董事局成員最終還是決定將公司轉讓給KKR。總價250億美元的華爾街有史以來最大的杠桿并購得以完成,KKR本身動用的資金僅1500萬美元,而其余99.94%的資金都是靠垃圾債券大王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發行垃圾債券籌得。 一直令筆者迷惑不解的是,國內有些主流媒體以及專家學者何以將此購并描繪成MBO的正面案例,又何以稱之為“陽光下的管理層收購”?如果僅僅因為競投保證了交易的所謂透明公正,然而通過競投規則的制訂我們卻很容易發現其利益取向。在董事局特別委員會制定出的競投規則中不僅要求競投者提案“不能附帶變賣任何RJR Nabisco資產的附加條件”,更必須“付給RJR Nabisco股東可觀的股票相關利益”。可見,在這里競投只不過是資本利益最大化的一種保證;并且,當我們尋找羅斯·約翰遜MBO動機的時候,我們發現管理層并不是出于對公司經營業績的考慮(實際上當時RJR Nabisco的經營業績極為出色),而是公司的股價被市場嚴重低估所帶來的巨大投機機會。所以,當妄圖以個人欲望凌駕于資本的意志之上時,羅斯·約翰遜的失敗也就不足為奇。羅斯·約翰遜MBO計劃的流產更從一個側面說明了MBO在杠桿收購中的作用與地位:MBO所難以擺脫的,是其背后資本利益這一只看不見的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此購并結束不久,垃圾債券大王邁克爾.米爾肯因掩蓋股票頭寸、幫助委托人逃稅、隱藏會計記錄等罪名被控而判監10年、賠罰11億美金,并被終生禁止從事證券行業,可見其中也并不都是“陽光燦爛”。隨著上世紀90年代的企業并購潮把美國股價推至高點,金融投機成本與風險隨之增高,我們看到,杠桿收購以及相應的MBO便不可避免地暫時歸于沉寂。不知某些業內人士何以得出MBO在世界蓬勃發展的結論? MBO斧正 在國內流行的MBO主流理論中,學者與專家們大多從管理層角度進行分析,卻很少有人從資方角度看待問題。實際上,從西方的購并歷史來看,MBO本身就是一個資本獲利套現的過程。資方在出售產權的過程中往往希望能在市價基礎上獲得一筆溢價,特別對于那些夕陽產業來說,因為發展前景并不樂觀,這種溢價效應便更為明顯。因而,對于資方而言,“能否獲得相對較高的溢價收益”成為其選擇出售方式與收購方的主要動因,至于所謂的MBO激勵問題、降低企業的管理層代理成本問題等等,根本就難以成為其考慮的首選因素,很明顯,在售出產權之后,再談論代理成本還有什么實際意義?所以,由于實施MBO所導致的對管理層的激勵效應以及代理成本降低等是MBO可能的后果或者說結果,而絕非MBO的原始目的。在這種目的與結果之間,是一種或然而絕非必然的聯系。當專家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站在管理層的角度上看待問題時,其立論根據便失去了中立的基礎,其觀點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失之偏頗。 從管理層角度來看待MBO的激勵作用以及代理人成本降低問題,國內的主流觀點(實際基本上是抄襲西方)這樣解釋,就是在MBO“股權集中”所導致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再結合這一前提下,MBO所造成的負債增加迫使管理層減少對自由現金流量的分配,從而使代理成本降低。這是因為,自由現金流量往往促使管理人員進行奢侈的支出(比如經營者高薪酬及津貼、可能揮霍公款、盲目擴張企業規模而忽視企業利潤等),而不是將其作為股息分發給股東,通過MBO增加負債,可以迫使這些現金流量被用于償還債務;此外,相對于股息的發放來說,管理人員對于償還債務的自由選擇余地相對較小。因而從某種程度來講,MBO代表的是一種債務約束行為,它通過平衡股東主權與經理主權,達到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深入分析下去,我們就很容易發現,這套理論的存在前提必須基于這樣一些基本假設:第一,管理層將企業認作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部門進行產業經營而非現代意義上的資本單元進行資本運作,也就是說,管理層必須沒有任何資本投機的動機與意識;第二,管理層在道德方面能夠進行有效的自我約束;第三,良好的法律環境及有效的監管體系。 筆者感覺已無任何必要對這種立論進行分析,我們只需看一看所有權與控制權再結合的典型產物—CEO們的所做所為,便可以知道這種思維是如何幼稚。從安然到世界通訊,從安達信到美林證券,一樁比一樁惡劣的一系列公司高管丑聞,讓我們看到私欲膨脹已經覆蓋了整個商業世界,以致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向國會所做的報告中,用“傳染性貪婪”一詞來形容在美國公司高層中盛行的病態文化與道德淪喪。當我們的專家學者們津津樂道于產權與經營權的合一所帶來的所謂激勵作用時,筆者讀到的卻是《財富》雜志這樣的調查結果:近3年的時間內,在公司股價高臺跳水、投資人損失了70%、90%甚至所有錢財的同時,美國1035家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和董事卻通過提前拋售套現他們的股票獲得了660億美元的巨額收入。通過《財富》我們同樣讀到了RJR Nabisco原CEO羅斯·約翰遜用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專程運送自己寵物狗的報道,也就是所謂的——CEO們過著狗一樣的生活。 我們不禁要問,對貪婪的激勵意味著什么?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是否已逐漸明晰這樣一條主線:隨著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這從某種意義上推動了新的金融工具的產生與發展,從而使物質生產部門(企業)的資本虛擬化程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從傳統的生產部門虛擬成為一個用以投機炒作的資本單元已經完全可行。垃圾債券、杠桿并購、MBO等金融工具的產生,不僅為美國企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融資思路,在發現和評估公司價值方面更被賦予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內容。然而當這種公司潛在價值在投機欲望推動下被泡沫化并無限膨脹時,股價與真實業績之間便失去了必然的聯系,此時這些金融工具便完全淪落成為少數人或團體攫取財富的得力工具。雖然,杠桿收購(包括MBO)在70—80年代客觀上曾為美國社會的高速發展作出過杰出貢獻,它也曾經將金融技術與激勵體制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然而MBO這種激勵作用以及代理成本的降低,卻只是其所帶來的一種可能的而絕非必然的效應。并且,我們還必須看到,MBO的成功實施還與社會功能結構(法律體系、信用體系等)的配套完善密不可分。因而MBO最終只能是作為一種工具,就一種工具而言只有使用上的優劣之說,而實無屬性上的好壞之分,關鍵是使用它的人與社會賦予其什么樣的角色與內涵。所以,當把MBO某些可能的功用片面夸大到神奇的地步,不是無知,便是別有用心了。 直面中國MBO 在中國,四通是最早嘗試通過MBO解決其產權虛置問題的企業之一。雖然四通的產權改革從嚴格意義而言并不成功,然而在國有股減持不得不喊停之后,人們似乎突然發現了MBO在產權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一夜之間,MBO被推崇倍至。 多少年來,試圖從產權角度來詮釋中國企業面臨的經營管理問題似乎已經成為一些主流學者的思維定勢,似乎一俟產權明晰,就可自發解決經營管理者的激勵與能力問題,就會引導企業走出困境。筆者不禁要問,民營企業產權明晰,為什么從整體而言同樣擺脫不了資產利用低效、經營管理水準低下等這些國營企業的傳統痼疾?由于無視經營性資產(物質性資產與人力資源)市場化流動對產業結構調整以及企業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理論上的滯后必然導致相應的社會配套體系缺失,這使中國企業普遍缺乏一種主動的、真正市場意義上的外部強行干預調控機制。這種僅僅從產權歸屬角度出發、試圖通過企業內部的方法改良解決社會功能結構性缺陷問題的理論,實將中國的經濟研究引向了死胡同。 如果僅僅從產權角度考慮問題,MBO解決的就是資產的歸屬而不是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中國MBO與西方的根本差異,MBO這一工具意義也就同樣徹底暴露無疑。通過MBO,我們可能會順利的將國有資產變更到私人手中,然而我們是否會喪失更為重要的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達至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最佳時機?從這個意義而言,東歐國家產權改革應該給我們以深刻警示:雖然通過MBO方式東歐得以迅速地實現了私有化,然而由于沒有解決產業功能結構方面的缺陷,其經濟發展依然難脫低迷不振的頹勢。 我們所擔憂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在社會功能與法律體系并不完備、缺乏有效監管、整個社會道德陷入深刻危機的環境里,所謂的產權明晰只不過是一個幌子——MBO最終被用來達至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 明白就里,我們就必須從中國MBO的操作流程與手法上進行深入分析。 一個典型的西方MBO購并應該如此:收購方一般要收購上市公司在外發行股份的90%以上,之后再對股權結構進行進一步集中,以保證管理層和中介機構對公司的私有化。這是因為,由于MBO收購必須要使用被收購企業的現金(通過發行債券或資產抵押等)來支付部分收購資金,所以收購方除管理層外其余的股東必須是關聯交易人,否則其他股東將因此而受到經濟損失。因此當企業進行MBO收購時,其他股東必然要求獲得同等待遇或選擇賣出股票,其最終結果是:當MBO收購完成后,被收購公司必然變成私有化公司而完成下市,從而使目標公司最終成為杠桿融資的載體和承擔者。 在這里我們看到,西方的MBO伴隨產權變更的是債務與風險向管理層的集中。而中國MBO的巧妙,卻在于既得利益者(管理層)在獲得控股權的同時卻將債務與風險向上市公司轉移,從而直接、間接侵占其他股東的應得利益。 這是因為,中國MBO恰到好處地充分利用了中國股市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同時并存的這一結構性缺陷。由于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巨大價差,MBO的目標所指,是通過收購非流通股達至一定比例后(一般不超過30%)獲得公司的實際控制權。而我國《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收購人持有目標公司30%股份后,如果選擇繼續增持才必須采取要約方式,這樣管理層實際上就可以通過非流通股的協議轉讓而不是全面要約收購實現對目標公司的實際控制。所以,在已有的MBO案例中,我們看到的MBO收購與公司發行在外的流通股根本無關,還沒有一家公司MBO買流通股,更不想通過MBO下市。如此,中小投資者因為根本無法參與其中而只能成為“被動知情者”。 這樣,當管理層利用上市公司的資信進行融資以完成MBO收購的同時,也就把融資的信用風險大部分轉移至上市公司也就是其他投資者的身上。 由于配股及新股溢價發行,流通股為每股凈資產增值作出了很大貢獻,與此形成對照的卻是一些非流通股(包括國有股和法人股)經常放棄配股。在這種情況下,MBO以低價位收購非流通股權,實際上是合法卻又極不公正地侵占了流通股股東的利益。 在這里還存在著一個理論上的巨大利益“黑洞”。 通過對2000年至2001年度實施配股或者增發的308家公司研究顯示,非流通股股東不管是否參與配股或增發,都能享受到每股凈資產的大幅增長。其中,參與配股將平均獲得28%的每股凈資產增長,不參加配股每股凈資產增長33%;而增發則更加“生猛”,非流通股股東享受的每股凈資產平均增長可高達72%。 于是我們就發現了這樣一個機會:只要你協議受讓非流通股的股價在每股凈資產基礎上的溢價不高于配股或增發后的每股凈資產增長,你就可能有利可圖。 我們可設立這樣一個模型:某上市公司管理層以截至某年某月某日上市公司經評估的每股凈資產(設為1元)為定價依據,溢價20%作為非流通股價格受讓6000萬股,收購完成后管理層實現對上市公司的控股,而好戲就在后面的再融資計劃中。 管理層控股上市公司后若選擇增發,每股凈資產增長率設為70%,扣除收購時20%的溢價,收益也將達到50%(3000萬元收益);若選擇配股,不管是否參與配股,其收益也在8%-13%之間。如果在配股或增發后選擇賣出套現,則收益遠不止此。 這便是理論上的“黑洞”,而在實際操作之中,還可能發生獲取控股權后以種種方式將不良資產溢價出售給上市公司所帶來的灰色收益。雖然在操作上有一定難度,然而一如我們看到的,這一切都已在現實中發生。 在貪欲的驅動下,一些企業在實施MBO的過程中,為了獲得較低的收購價格,不惜通過調劑或是隱藏利潤的辦法擴大上市公司的帳面虧損甚至直至上市公司被ST、PT;而一旦MBO完成,高管人員再通過調帳等方式使隱藏的利潤合法地出現,從而實現年底大量現金分紅以緩解管理層融資收購帶來的巨大財務壓力;更有甚者,一些企業的管理層在實施MBO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的關聯交易,致使資金嚴重外流以達到自己灰色收益目的。這一切必然導致上市公司資產流失、內源融資能力下降、財務風險加大,也就不可避免造成對其他股東(包括國有股)利益的惡意侵占與傷害。 這樣,我們就基本明晰了上市公司MBO的利益所在:第一,管理層把獲得利益補償的突破口選在了公司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價差上,通過低價獲取非流通股使得自己的控制權得以物化,而自己下一位的接手者在支付高溢價之后依然能在價差區間中獲得另一部分的超額利潤,從而實現自己與接受者的“雙贏”;第二,通過獲取上市公司股權取得的實際控制權形成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進而將上市公司完全轉變為自己撈取利益的工具。 我們看到,正是因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并存這一結構性缺陷,使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權演變成無風險獲取財富的象征。然而卻也正是MBO,為未來的股份全流通鋪設了無盡的障礙,使這種結構性缺陷又不得不延續下去。這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個疑問,國有資產為什么是“管理層”收購?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提及我國大多數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另一結構性缺陷,這種特色源自其設立時的“逃控機制”模式。流行的做法是將原國有企業的核心部分包裝上市,稱為“上市公司”,而非核心資產留下來叫“存續企業”,這個“存續企業”代表國家控股上市公司。“存續企業”的總經理(或稱法人代表)擔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由于“存續企業”與上市公司這種特殊的關系,不僅使大量的關聯交易成為可能,也同樣使非流通股權的協議轉讓變得曖昧不明。從大多數MBO案例來看,上市公司管理層收購不僅是自賣自買,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己批準自己收購。這樣就難怪有人一針見血地稱之為“沒有管理的管理層收購”。 由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行政任命,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員,所以他們與地方政府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這不可避免地使MBO成為權力資本與貨幣資本的盛宴,為什么是“MBO”也就在不言之中。 這一切似乎都與通過MBO明晰產權的原始初衷相去甚遠。如此,我們看到,國有股轉讓這一順應完善中國證券市場股權結構和中國經濟所有制結構之潮流的舉措,在MBO的旗幟下,卻基本變質為一場權力資本與貨幣資本逐利的游戲,而最終將為這場游戲買單的,一個是國有資產,一個是中小投資者(股民)的私人財富。 國資變局 于是,我們便找到了本文起始問題的答案。我們看到,即使解決了MBO的管理層融資問題與收購主體合法性瓶頸,即使通過競標等所謂“陽光下”的方式——管理層以高于帳面每股凈資產價值的溢價收購,由于不能根本解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并存以及“逃控機制”這兩個歷史遺留結構性缺陷與制度性問題,因而并不能消滅中國式MBO的內源動因與外源條件,那么它也就并不會解決MBO在中國實施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相反,它卻會使中國MBO的步伐加快,其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以及對股民的掠奪更加迅速。問題是,與巨額投機收益相比,產業利潤往往變的微不足道,這導致管理層實際上喪失產業經營動機,而當最終套現走人后——結局將不難想象。也正是因為不能消滅中國式MBO的動因與條件,當國資管理部門試圖通過嚴格監管與審批手段加以控制時,就極有可能使MBO走向隱蔽與秘密,也使MBO的信息披露更加朦朧與迷離。 這種征兆已經逐漸顯示。 就在國資委掛牌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9日,伊利股份(600887)發布公告稱,金信信托協議受讓伊利股份2802.8743萬國有非流通股已獲財政部批復,股份受讓后由國有股變更為社會法人股,金信信托從而成為伊利股份第一大股東。 批復的順利源于這單信托收購為金信信托所言的“自營投資”——按我國的法律規定,受托投資無法逾越財政部門的審批門檻。 一位業內人士這樣評價這單收購:“一出手就是2.8億的真金白銀,既不熟悉公司管理層,也不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只做戰略投資者。誰信?”另有業內人士直接點出了眾多上市公司規避監管、實施MBO計劃的“七寸”所在:無論是將國有股轉讓給非國有企業,還是由非國有控股的信托公司受托收購,當收購行為將國有股合法地變更為社會法人股時,MBO就成功了一大半。 威斯考特有句名言為信托業所樂于引用:信托可以和人們的想象力相媲美。當我們猛然發現悄然間信托投資公司參股或控制上市公司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證券市場的任何一個“派系”、作為“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信托公司卻沒有一例聲稱是“受托投資”時,可能一切早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之外。在我國由于《貸款通則》對商業銀行貸款有“不得用于股本權益性投資”的界定,企業債券發行也受到很多限制,因而在目前的金融體系內,惟有信托業因依據信托文件可進行靈活投資,參與MBO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礙;并且,雖然信托業保密條款會與證券業公開性原則產生沖突,然而由于我國相關法律在明確信息披露義務人、信息披露內容以及披露到何種程度等方面還缺乏明確界定,這無疑為MBO提供了絕佳的保護,使“影子”收購成為現實。 讓我們再來看看信托的背景:我國信托公司多數由國家創辦和經營,帶民營性質的信托公司屈指可屬。信托投資公司從一開始就承擔了部分的政府職能,許多地方信托也因之演變為當地政府的附屬物,主要服務于地方政府自籌的基本建設和固定資產投資。雖然歷經五次大規模的清理整頓,信托公司體制上的缺陷問題并未完全解決。獲準保留的信托公司,大部分仍然是地方政府控股的國有企業,機制基本依舊,人員基本依舊,管理基本依舊。 當我們許多專家、學者將MBO的融資希望寄托于信托的MBO基金時,是否考慮過信托公司自身的融資能力?實際上由于嚴重的社會信用不足和信用不良,歷史上中國的信托公司一直缺乏正常的信托資金來源而被推進“高進高出”的惡性循環之中;也正是由于沒有信用基礎,信托公司缺乏主營業務,只能“不務正業”而被稱之為金融領域的“壞孩子”,導致“兩面挨巴掌”。這種先天性功能障礙導致了信托的底氣不足。業內流傳的一個版本是,私募MBO基金可將手中資金作為信托資產,利率也并不高,關鍵在于幕后協議——管理層在實行收購的同時,以同樣價格將一部分股權轉讓給私募MBO基金。 對MBO感興趣的基金還遠不止此。在MBO基金設立的熱潮中,我們看到了管理135億美元資產的美國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與新疆德隆的聯手以及紅塔集團、深圳國投、花旗銀行和梧桐基金這樣的組合。 這樣,通過信托我們似乎看到了這樣一座隱隱約約的詭秘通道,它的一頭通向國企,一頭通向海外與民間。 正是因為我國信托這種獨有的特點,正是因為我國《信托法》已經頒布卻缺乏實施細則,筆者才有一種但愿是杞人憂天的疑慮,那就是權力資本與貨幣資本借助信托的力量得以更加隱蔽與迅速地將財富轉移。 尾聲與呼聲 讓我們側目看看我們的鄰居俄羅斯。 實際上,早在蘇維埃后期,俄羅斯便發生了“隱性私有化”,國有資產原來誰在管理,就歸誰占有,結果是出現了“高干民主”和“高干資本主義”,出現了“官員私有化”。1991年開始的轉軌,不過是對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的承認。通過俄式MBO,俄羅斯實際價值超過1萬億美元的500家大型國企,只賣了72億。然而由于法律以及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其他社會相關配套體系建設的嚴重滯后,它并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對經濟的整體控制能力卻嚴重降低,從而直接動搖了國家統治的基礎。 經濟投機到一定程度必然是投機政治。對政局動蕩以及資本“原罪”的憂慮必然導致資本外逃。據最新的官方文件披露,俄每年外流的資本為150億到200億美元(而我國初步測算為每年300億美元),相當于損失4500億到6000億盧布的最終需求,或者6%至8%的潛在增長率;伴隨還有大量的頂尖人才流失海外(中俄已成為人才流失最為嚴重的國家)。 令俄羅斯及普京們頭痛不已的是,如果國家嚴格按照法律拷問資本“原罪”,勢必造成不穩定的形勢,導致資本進一步外逃;然而如果置之不顧,國家公信以及統治基礎何在? 俄羅斯的轉軌過程因此呈現為不同利益集團與國家利益的沖突。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過程,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特有的轉軌沖突將使俄羅斯陷于長期衰退的不劫之地。 我們已經看到,它已從一個超級強權淪落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對于國際重大事務的參與實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這就是今日的俄羅斯。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示。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氣 ● 答疑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滾動新聞 > 正文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新浪網 北京市電信公司營業局提供網絡帶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