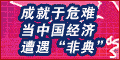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揪心疫情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5月10日 09:59 經濟觀察報 | ||
|
本報記者邵穎波(執筆) 戴佩良黃一琨北京報道 太陽升起又落下,晝夜仍像往常一樣輪回,但是突然間,北京人似乎已經無法分清現實與夢境的邊界。一個多月來,SARS的夢魘,盤踞在首都的上空,讓人們體會到空前的緊張、恐懼和煩躁。 不管是被嚇破膽躲在屋里拼命休息的人,還是那些耐不住寂寞出來當街跳舞的人,在這一段時間里,他都必須要在每天傍晚的時候知道那個數字——69,或者是96。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數字代表的確切涵義,也沒有多少人了解其中的故事,只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都不得不在心底盤算一下,自己會不會在哪一天成為那個數字的一個組成部分。更讓人難過的是,如果真的不幸成為其中的一個“1”,在一場集體性的災難中,在個人心中無比珍貴的生命,可能只剩下統計學上的意義。為什么關心疫情 如果我們自問,是什么原因讓我們所有的人如此一致地關心疫情的變化,可能得出的惟一結論就是它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你是平民百姓,那你必須根據這個情況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是政府官員,那你也必須根據這個情況來安排自己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與疫情沒有關系,那你的注意力可能更多地放在特殊時期的形象安排上面;當然,如果你是個生意人,下一步是賺錢還是賠錢你就得花更多時間來進行考量,疫情的發展變化是最重要的根據之一。 所以,現在我們就明白了一件事,所謂疫情,絕對不是僅僅指疫病本身在當時當地的情況——確診多少,疑似多少,治愈多少,死亡多少,病毒如何生長又怎樣傳播。事實上,對于SARS,我們想要知道的東西非常之多,它的過去和它的未來,本地與外地,交通和天氣,政府的管制與寬容。它的外延無比寬廣,你要了解的事情非常之多,甚至包括警察與軍隊的動向。你或許無暇判斷政府已經實施的措施是不夠嚴格還是已經超過了限度,但是你可以根據這些情況來猜測疫情的發展,如果疫情的發展本身是按照一種我們誰也弄不懂的規律在進行,這依然不妨礙你根據政府或者社區的措施來思考自己的行動。就是說,雖然在現時這個階段,你無法弄懂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必須知道的,那就是在這一場災難到來之時,你已經身處被動,于是,你必須了解更多的信息,而所有你想知道的,都是疫情。 這是人之常情,人之本能。因為違反了這種最為基本的意愿,4月20日,張文康、孟學農被免了職,關于“疫情已經被基本控制”的說法也隨風而去。 但是,我們又陷入了另外一種疫情信息的危機,這個危機不僅僅源于因為某些官員前期表現不佳所帶來信任危機,更主要的是出于我們對疫病本身的無知。不僅我們平民百姓對此一無所知,包括我們所仰仗的專業人士,他們分別進行研究,采取不同方法,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也得出相互一致或者完全相反的結論。在這些信息面前,我們無所適從。 我們最最想要知道的就是北京的疫情會在什么時間結束?臨危受命的代市長王歧山先生說得好,任何對疫情的判斷都像是在進行一場賭博,這是他第一次和公眾交流時對疫情本身所下的最為清晰的一個判斷,但也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判斷,它絲毫不能減弱人們強烈的求知本能,“賭博”仍在進行,有些機構和個人參與進來,提出自己的看法,更多的平民百姓必須努力找到一種打算要認同的主張。 但現在這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瘟疫亂情 我們基于事實而能夠相信的一個基本判斷是:迄今為止,北京現在是全球SARS病情最為嚴重的地區。北京的疫情發展不僅關系這里的1300萬人的生活,也關系到世界的各個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做到的不僅是動員所有力量來控制這里的疫情發展,也要讓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這里的每一個細微變化。 感謝政府的責任感和法律的要求,現在我們每天可以獲得疫情的核心內容,但缺乏可靠的權威的解讀仍使我們心中存在著太多疑惑。我們可以聽到草叢里蛇的肚皮劃過草尖時悉悉索索的聲音,但是我們不能知道這條蛇的毒性有多么大,它將游向哪里。 具體來說,現在我們還不能得到有關感染人群的詳細資料,不知道他們染病的具體細節,難以判斷誰處于高危人群,不知道到底有哪些傳染渠道,不知道在什么情況下治愈者可能復發,不知道北京的疫情與先前廣東和香港有多少不同,病毒又發生了什么變異?因為我們對于流行病學的基礎知識了解太少,不知道哪些數字或者圖表對于呈現疫情轉變更為關鍵,甚至,我們對于某些調查機構說95%的北京人滿意的結論如何得來也不得而知,就像我們不知道流調隊有多少人在工作,去了哪些地方,問了哪些問題,發現了什么結果一樣。于是,我們也和所有的人一樣拼命地搜集信息,或者不停地看那些零七八碎的報道,腦海也就呈現一種無法梳理的亂象。 5月4日,位于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的有關SARS病毒最新研究報告顯示,這種致命病毒的韌性,比原先想象更大,甚至可以在人體外存活長達數周。可是先前我們聽到的說法只有3-4個小時。這份報告里還說,這種類似流感的瘟疫,并不一定要直接接觸已感染的病人,只要碰過已污染的物質,就可能被感染。 但是香港、日本與德國進行的實驗室研究結果又不一樣,他們認為SARS病毒在人體以外的任何表面,可能存活數小時;而在人體排泄物中,它可以存活四天。 關于病情診斷標準的改變也讓人感到緊張。前不久WHO更新了SARS病例的定義,規定疑似病例的抗體、病毒核酸或病毒培養檢測結果,只要任何一項是陽性,就認定是SARS。這意味著WHO在鼓勵病原學檢測方法盡快投入臨床一線使用。而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地的醫生在診斷SARS時,主要依靠的還是量體溫、做胸透、查血象等臨床檢查。 研究似乎在證明病毒可能越活越長,傳播越來越容易,而且毒性也越變越兇,但是由這種病毒所引起的疫情如何發展卻始終不明。當我們需要受到鼓舞時,我們會看到樂觀的專家被請上臺來,他們說這種病可防可治,而且情況正在好轉;當我們需要進行更加嚴格的政府措施時,我們又會聽到相反的說法。情況就是這樣讓人無從判斷,5月3日,我們聽到鐘南山院士預測說,北京可能在5月中旬以后進入下降期。但是在7日,我們又聽到WHO表示:現在說北京SARS疫情已達高峰,還言之過早,目前仍無法判斷北京整個疫情走向。多變的病死率 在這非常時期,死亡成了人們必須面對的一個高頻出現的詞匯。而在這一無法回避的問題上,病死率的高低之爭也在科學家與政府官員們之間進行。關注這方面的不同說法,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北京疫情呈現出的模糊景象。 所謂病死率,又稱病例死亡比Death-to-case ratio,是某病患者中的死亡頻率,是觀察期內因某病死亡人數與同期某病患者數之比。這個一般以百分數表示的指標說明疾病嚴重程度,反映疾病預后,反映醫療質量。 在人們尚未完全掌握有多達六種變種的冠狀病毒的時候,切斷傳染源與降低死亡率成了減少恐慌、增強信心的保障。前者是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最怕媒體提到的問題,至于后者,至今仍是一個讓人揪心的謎團。他在5月2日檢查疫情防治工作時援引專家意見稱,1998年爆發的流感受感染的人數比這次多,病死率也達到8%,為此希望民眾能夠堅定信心。 就在有人指出北京疫情當中病死率高于其他地方的時候,全國防治“非典”指揮部科技攻關領導小組成員朱宗涵教授公開提出,北京非典患者死亡病例中近10%死因與非典無關。而從廣東臨時抽調來京的廣東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長肖正倫,面對本報記者提問時也表明了這一觀點,認為不應把過多的精力集中于現在的病死率數據,更重要的是看到趨勢;但他也向北京市有關方面提出了集中收治重病病人的建議,這一建議的重要目標就是降低北京的病死率。 但是另外一些國際同行們對此并不很樂觀。醫學雜志《柳葉刀》(Lancet)的研究表明,SARS的死亡率是20%。這是根據從2月20日到3月15日對香港1425名懷疑患有SARS病的住院病人的統計分析得出的。這項研究采用參變量分布的統計手段,60歲以上的患者死亡率是43.3%,60歲以下的是13.2%。 WHO負責SARS研究的Klaus Stohr博士認為,對病死率計算的統計學手段有很多種,并取決于不同的情境。WHO正在考慮改進他們的數據獲取和統計學模型。而在5月6日,該組織認為香港的SARS新增病例正在穩步下降,目前的病死率為11.7%。 《柳葉刀》雜志組織的研究認為對該病的流行病學調查表明,SARS的死亡率可能要高于官方衛生機構對它的估計。隨著疫情的繼續,死亡率會有不斷變化,但是除非有極為顯著的變化,否則SARS將是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 肖正倫認為北京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一些,確實看到北京的疫情有一些特點,原來有基礎病歷,年齡比較大的患者多一些,目前專家們也在努力尋找規律,并在考慮是否可能是北京病毒變得比較“毒”一點? 他認為其中的因素很復雜,不能單純說治療上有問題,關鍵是要調動所有的醫療力量上去。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朱宗涵則表示,隨著SARS疫情趨于平穩,加上醫務人員診斷、治療搶救的經驗不斷積累和對重癥病人的早期識別及搶救條件、力量的改善與增強,北京的非典死亡病例會逐步下降。 國外專家認為有可能有的病人感染病毒卻未發作,或是有的人癥狀很輕微,沒有就醫。如果這些因素確實存在,那么疾病的死亡率可能還會降下來。但在5月6日,WHO總干事布倫特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表示,SARS在中國還沒有到達發病高峰,現在談論疾病在全球范圍內消退為時尚早。疫情延展之后 一場SARS疫情的突發,讓很多人有機會回顧了人類歷史上的瘟疫發生史。的確,瘟疫本身歷史久遠,相伴而生的人類關于疫情研究、控制以及相關的科學發展也同樣源遠流長。流行病學調查已經成為了這一學科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為了摸索傳染病發生的原因和傳播的條件,以便及時采取合理而有效的防治措施,人們總是伴隨著瘟疫的發生而進行科學的調查,這些調查可以查明傳染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諸如傳染源、傳染媒介、傳播途徑、易感動物、影響傳播的因素和條件、疫區范圍以及發病率與死亡率等。在流行病學調查的基礎上人們也總結出了一整套分析方法,可以保證人類可以由表及里,去偽存真,發現規律,并對有效的措施作出正確的評價。 現在,人們在很多問題上存在爭論,比如北京市的防治措施是不夠,還是太過了,還是恰到好處。如果真實信息是在4月13日,而不是4月20日發布又會是什么樣子?北京市還會產生多少病人?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極限是不是媒體報道的6000人?超過這個數字會怎樣?老百姓該不該上街買菜?被推遲的集會該什么時候進行等等。無謂的爭論往往更使人感到無奈,只有真正的科學精神才應當是我們行動的指南。而所謂科學又絕不僅僅指醫學、流行病學和自然科學,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系統的學問體系都是我們應當而且必須尊重的。就像我們對付SARS病本身必須依靠全球的醫學科學家以及他們所在機構一樣,對付SARS疫情,我們也必須依靠所有的相關學科的專業人士共同研究來確定我們的綜合方案。所幸的是,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志于為此做出貢獻的人并不少見。 現在,我們已經得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客座教授曾強先生的一份建議。曾強先生認為,政府現在公布的每日疫情數字和累積數字,僅僅反映了城市SARS的歷史狀況,這些資料是根據政府已經控制的病人的情況做出的,但對正在和將要發生的危險并不能做出直接的反映。這位應用數學專業出身的人士建議通過數學模型的計算,建立起一套“城市傳染源危險指數”體系。從而科學地反映疫情變化的趨勢。曾強先生自己已經初步進行了這項研究。 當然,我們還知道,有各方面的專業人士在各自的領域內進行著有關研究,和曾強一樣,他們都各有所長。這些人的智慧應當是我們可以依賴的最大最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只是,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建立起徹底尊重科學的意識,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也許永遠都弄不清楚疫情的發展。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氣 ● 答疑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滾動新聞 > 《經濟觀察報》:SARS不應將我們隔開 > 正文 |
|
| 新 聞 查 詢 | |||||||||||||||||||||||||||||
|
| |||||||||||||||||||||||||||||
| |||||||||||||||||||||||||||||
網絡營銷成新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