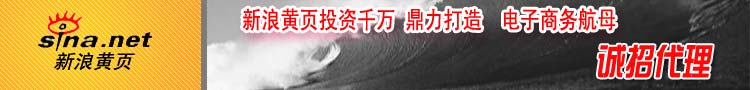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МW(xuиж)г║╓├╔э╙┌ґw╓╞Г╚(nииi)┼cґw╓╞═т╡─Г╔юР(l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http://www.sina.com.cn 2006─ъ09╘┬29╚╒ 11:19 ╨┬└╦╪Ф(cивi)╜Ы(jийng)
бббб╬╫└^МW(xuиж) ббббМж(duи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П─▓╗═м╜╟╢╚бв╥╘▓╗═мШ╦(biибo)Ь╩(zhи│n)▀M(jимn)╨╨╖╓юР(lииi)бг├┐╥╗╖N╖╓юР(lииi)╢╝┐╔╥╘О═╓·╚╦ВГМж(duи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J(rииn)╓кбг▀^(guи░)╚е╬╥МС(xiиз)╬─╒┬╘Ї╒f(shuин)▀^(guи░)г║╚ч╣√╥╘╖■Д╒(wи┤)Мж(duим)╧ґЮщШ╦(biибo)Ь╩(zhи│n)г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Дt┤ґґw┐╔╥╘╖╓Ющ╥╘╧┬╚¤юР(lииi)г║╡┌╥╗юР(lииi)╩╟╖■Д╒(wи┤)╙┌╒■╕о╡─╜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ВГ╓├╔э╙┌ЗЇ(guио)╝╥╚лю~╣йЁB(yигng)╡─╒■╕о┬Ъ─▄▓┐щT(mижn)╡─╜Ы(jийng)Э·(jим)╤╨╛┐ЩC(jий)ШЛ(gи░u)бв╜Ы(jийng)Э·(jим)╒■▓▀╤╨╛┐ЩC(jий)ШЛ(gи░u)гм╥╘╝░╒■╕о╚лю~╣йЁB(yигng)╡─╞ф╦№╜Ы(jийng)Э·(jим)╤╨╛┐ЩC(jий)ШЛ(gи░u)г╗╡┌╢■юР(lииi)╩╟╖■Д╒(wи┤)╙┌╞ґШI(yии)╡─╜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ВГ╓├╔э╙┌╞ґШI(yии)╡─╜Ы(jийng)Э·(jим)╤╨╛┐ЩC(jий)ШЛ(gи░u)гм╗Ґ╒▀╩▄╞╕╙┌╞ґШI(yии)гм╗Ґ╒▀╓іД╙(dи░ng)╖■Д╒(wи┤)╙┌╞ґШI(yии)г╗╡┌╚¤юР(lииi)╩╟╖■Д╒(wи┤)╙┌╔чХ■(huим)╣л▒К╡─╜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ВГ┤ґ╢р╓├╔э╙┌╕▀╨ггм╓├╔э╙┌└э╒У╜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ЩC(jий)ШЛ(gи░u)гм▒╚▌^│м├У╙┌╒■╕о╡─╒■▓▀Мз(dигo)╧Ґ┼c╞ґШI(yии)╡─╙п└√╘V╟ґгм▀@юР(lииi)МW(xuиж)╒▀╥▓╙╨╥╗▓┐╖╓Бэ(lивi)╘┤╙┌ШI(yии)╙р╤╨╛┐бг╜№Бэ(lивi)гм╬╥╙X(juиж)╡├╙╨╥╗╖NДЭ╖╓г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ґw╡─┴вИІ(chигng)бв└√╥ц╘V╟ґбг▀@╖NЕ^(qи▒)╖╓┐╔╥╘╖Q(chиеng)▀@Ющб░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cб░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бг бббб╥╘ґw╓╞Ющ╜чЕ^(qи▒)╖╓╡─Г╔юР(l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 ббббМв╜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Е^(qи▒)ДeЮщб░ґw╓╞Г╚(nииi)б▒┼cб░ґw╓╞═тб▒Г╔┤ґюР(lииi)гм╗ї▒╛Ш╦(biибo)Ь╩(zhи│n)╛═╩╟╜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э╙┌ЗЇ(guио)╝╥╔чХ■(huим)╜Ы(jийng)Э·(jим)ґw╓╞╓оГ╚(nииi)▀А╩╟╓о═тг┐╥╘╬╥╡─└э╜тгм╖▓╩╟╘┌╒■╕оґw╓╞╖╢З·Г╚(nииi)╚╬╙╨╣л┬Ъ╡─╛═╩╟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ёДt╛═╩╟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г╙╨╚╦╒f(shuин)гм▀@╥к┐┤МW(xuиж)╒▀ВГ╩╟╖ё╩▄?chие)?guио)╝╥╣йЁB(yигng)╢Ї╢ибг╤╘╧┬╓о╥т╛═╩╟╒f(shuин)гм╝┤▒у╘┌ґw╓╞Г╚(nииi)╚╬╙╨╣л┬Ъгм╓╗╥к▓╗─├╨╜╦обв▓╗─├╚╬║╬╜Ы(jийng)Э·(jим)Иґ(bидo)│ъгм╛═▓╗╦у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г╥▓╙╨╚╦╒f(shuин)гм▀@╥к┐┤МW(xuиж)╒▀ВГ?cии)┌╣л┬Ъ╔╧├┐─ъ╡─╣д╫іХr(shик)щg╢Ї╢игм╚ч╣√╦√├┐─ъ▀_(dив)▓╗╡╜╥╗╢и╡─┬Ъ─▄╣д╫і╠ьФ╡(shи┤)гм╥▓╦у▓╗╡├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г▀А╙╨╚╦╒f(shuин)гм╛═╩╟╦√╘┌╣л┬Ъ╔╧гм─├┴╦╧рСк(yийng)╡─Иґ(bидo)│ъгм╥▓─▄▒г╫C╥╗╢и╡─┬Ъ─▄╣д╫і╠ьФ╡(shи┤)гмб░╔э╘┌▓▄аI(yикng)╨─╘┌Эhб▒гм▒э├ц╔╧╕╔┬ЪД╒(wи┤)╗ю░╡╡╪└я╕╔╫╘╝║╡─╦╜╗югм┐╓┼┬╥▓ыy╚ы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г▀@╨й┘|(zhим)╥╔╢╝╙╨╞ф╡└└эбг╩╟╖ё╓├╔э╙┌ґw╓╞Г╚(nииi)╡─╣л┬Ъ╔╧гм╩╟╥╗ВА(gии)╗ї▒╛┼╨Фргм╦№╩╟╥╗юР(l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ї▒╛Ш╦(biибo)╫R(shик)гм╥╗░уШ╦(biибo)Ь╩(zhи│n)бг╡л╩╟гм╚╬║╬ДЭ╖╓Ш╦(biибo)Ь╩(zhи│n)гм╢╝▓╗┐╔─▄Ы](mижi)╙╨└¤═тгм╢╝ыy╥╘╫І╡╜╖╟┤╦╝┤▒╦бгВА(gии)Дe╡╪╒f(shuин)гм╓╗╥к▀@╬╗МW(xuиж)╒▀╘┌▀@ВА(gии)╣л┬Ъ╔╧─▄ЙҐ╗ї▒╛═ъ│╔╦√╡─┬ЪД╒(wи┤)╣д╫ігмЯo(wи▓)╒У╦√╩╟╖ё╩╟╚л┬Ъгм╩╟╖ёИґ(bидo)│ъ─├╚лю~╔є╓┴╖╓╬─▓╗╩╒гм╩╟╖ё═мХr(shик)╝ц╕╔╫╘╝║╡─╦╜╗югм╢╝▓╗╘┌╘Т(huид)╧┬бг бббб─╟├┤гм╩▓├┤╩╟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П──┐╟░╓╨ЗЇ(guио)╡─мF(xiидn)аюБэ(lивi)┐┤гм╦ї╙╨╣л╙╨╓╞╧┬╡─┤ґМг(zhuибn)╘║╨г╓╨╡─╜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МW(xuиж)╒▀гм╦ї╙╨ЗЇ(guио)╝╥╔чХ■(huим)┐╞МW(xuиж)╤╨╛┐ЩC(jий)ШЛ(gи░u)╓╨╡─╜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МW(xuиж)╒▀(╕і╝Й(jик)╔чХ■(huим)┐╞МW(xuиж)╘║бв╤╨╛┐╦ї)гм╦ї╙╨№h╒■ЩC(jий)ъP(guибn)▓┐щT(mижn)╓╨╡─╤╨╛┐ЩC(jий)ШЛ(gи░u)бв╒■▓▀╤╨╛┐Ж╬╬╗гм╦ї╙╨№h╒■╧╡╜y(tипng)╓і▐k╡─├╜ґw(Иґ(bидo)┐пбвыК┼_(tивi)бвыК╥Хбв╛W(wигng)╒╛╥╘╝░╕іюР(lииi)Ві╜y(tипng)┼c╨┬┼d├╜ґw)╓╨╡─╜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МW(xuиж)╒▀г╗╘┌╥╗╢иХr(shик)╢╬│╨У·(dибn)ЗЇ(guио)╝╥╔чХ■(huим)┐╞МW(xuиж)╤╨╛┐╗ї╜Ёбв╫╘╚╗┐╞МW(xuиж)╤╨╛┐╗ї╜ЁэЧ(xiидng)─┐бвЗЇ(guио)╝╥╜╠╬п╡╚╥╗╟╨╣л┘M(fииi)эЧ(xiидng)─┐╡─├ё▐k╤╨╛┐ЩC(jий)ШЛ(gи░u)╓╨╡─╜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МW(xuиж)╒▀гм╓┴╔┘╘┌▀@ВА(gии)эЧ(xiидng)─┐╡─╤╨╛┐╔╧╩╟╕╔╡─╩╟ґw╓╞Г╚(nииi)╡─╗юбг бббб▀@Ш╙╒f(shuин)Бэ(lивi)гм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ч╢ибг╧роФ(dибng)┤ґ╥╗▓┐╖╓╜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П─╣л┬Ъ╔╧═╦│ІБэ(lивi)╡─гм═╦ыx╨▌╡─гм═╦┬Ъ╡─гмыx┬Ъ╡─гм▒╗╟х═╦│ІБэ(lивi)╡─гм╡╚╡╚гм╝┤╘н▒╛╩╟╣л┬Ъ╔╧╡─╚╦мF(xiидn)╘┌│╔ЮщМW(xuиж)╨g(shи┤)╫╘╓і╔эгм│╔ЮщкЪ(dи▓)┴в╤╨╛┐╒▀г╗▐D(zhuигn)▄Й╩╨ИІ(chигng)╜Ы(jийng)Э·(jим)╥╘Бэ(lивi)гм╙╨╥╗▓┐╖╓╫╘╙╔┬ЪШI(yии)╒▀гм╥▓╝╙╚ы╡╜╜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ШI(yии)гм╞ф╓╨╙╨╫╘МW(xuиж)│╔▓┼╒▀гм╥▓╙╨┐╞░р│І╔эгм╔є╓┴╥▓╙╨╚╦Ф╡(shи┤)▓╗╔┘╡─║гЪw╖╓╫╙бг бббб▀А╙╨╥╗▓┐╖╓╚╦┐╔╖Q(chиеng)╓оЮщыpЧлМW(xuиж)╚╦гм║▄ыy╒f(shuин)╡├╟х╦√ВГ╩╟╘┌ґw╓╞Г╚(nииi)▀А╩╟ґw╓╞═тгм┐╔─▄╝╚╩╟ґw╓╞Г╚(nииi)╙╓╩╟ґw╓╞═тгм╝╚▓╗╩╟ґw╓╞Г╚(nииi)╥▓▓╗╩╟ґw╓╞═тбг╥╗╖N╟щЫr╩╟гм╥╗╨йМW(xuиж)╚╦╝ц╫Іґw╓╞Г╚(nииi)┼cґw╓╞═т╡─╩┬гм╘┌Г╔╒▀╓ощg╠Є╠ЄТ■Т■гм│І│І▀M(jимn)▀M(jимn)г╗╥╗╖N╟щЫr╩╟гмґw╓╞Г╚(nииi)╡─╥╗╨йЗЇ(guио)╝╥╣л┬Ъ╚╦ЖTгм╦√ВГ╡─╣д╫і┼c╜Ы(jийng)Э·(jим)╤╨╛┐║┴Яo(wи▓)ъP(guибn)╧╡гм╓╗╩╟╘┌ШI(yии)Д╒(wи┤)Хr(shик)щg╗Ґ╒▀╣д╫і╡─┐╒╧╢╓╨▀M(jимn)╚ы▀@ВА(gии)юI(lилng)╙Ґг╗╥╗╖N╟щЫrДt╩╟гмґw╓╞═т╡─╥╗╨йМW(xuиж)╚╦гм╘┌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c╜╠МW(xuиж)ЩC(jий)ШЛ(gи░u)╝ц┬ЪП─╩┬╜Ы(jийng)Э·(jим)╤╨╛┐╣д╫ібг ббббб░ґw╓╞Г╚(nииi)б▒┼cб░ґw╓╞═тб▒╜o╙ш┴╦╜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юоР ббббЯo(wи▓)╒У╩╟ґw╓╞Г╚(nииi)╡─▀А╩╟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ВА(gии)╣▓═м╡──┐╡─гм╢╝▄Q╔э╙┌╜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юI(lилng)╙Ґгм╗Ґ╛═мF(xiидn)МН(shик)ЖЦ(wииn)ю}гм╗Ґ╛═└э╒У(МW(xuиж)┐╞╜и╘O(shии))ЖЦ(wииn)ю}гм╗Ґ╒f(shuин)▓▀ЖЦ(wииn)ю}▀M(jимn)╨╨╤╨╛┐бг бббб╚╗╢ЇгмГ╔юР(l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Е^(qи▒)ДeЕs╩╟я@╢Ї╥╫╥К(jiидn)╡─бг бббб╫іЮщ╜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ґw╓╞Г╚(nииi)┼c╒╛╘┌ґw╓╞═т╫ю┤ґ╡─▓╗═м╘┌╙┌гм╟░╒▀╩╟╙╔╣л╣▓╪Ф(cивi)╒■╣йЁB(yигng)(╓┴╔┘╫╘╝║П─╩┬╡─┬ЪД╒(wи┤)╤╨╛┐╩╟╙╔╒■╕о┘Y╜Ё╓з│╓╡─)гм║ґ╒▀╩╟╖╟╣л╣▓╪Ф(cивi)╒■╣йЁB(yигng)г╗╥▓╛═╩╟╒f(shuин)гм╟░╒▀╩╟ґw╓╞╓з│╓╓Ї╦√╡─╤╨╛┐╒nю}гм║ґ╒▀Еs▓╗╚╗бг бббб╙╔╙┌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ЗЇ(guио)╝╥╣йЁB(yигng)╡─МW(xuиж)╒▀гм╦√ВГ╩╫╧╚╙╨МW(xuиж)╨g(shи┤)┬Ъ╖Q(chиеng)╡─Ш╦(biибo)╫R(shик)╥╘╝░╡╪╬╗╒J(rииn)╢игм▀@╨й╜ч╢и┤ґґw╚ч╧┬г║П─╫ю│є╝Й(jик)╡─╓·╜╠(╤╨╛┐ЖTМН(shик)┴Х(xик)ЖT)щ_(kибi)╩╝гм╥╗┬╖┼╩╔¤гм╓vОЯ(╓·╤╨)бв╕▒╜╠╩┌(╕▒╤╨╛┐ЖT)гм╜╠╩┌(╤╨╛┐ЖT)гм╤╨╛┐╔·Мз(dигo)ОЯ(┤TМз(dигo)бв▓йМз(dигo))гмМW(xuиж)▓┐╬пЖTг╗┼c┤╦╞╜╨╨╡─▀А╙╨Мг(zhuибn)╝╥╘u(pикng)Гr(jiид)╧╡╜y(tипng)г║?jiигn)╬╬╗М?zhuибn)╝╥гм╩б▓┐╝Й(jик)Мг(zhuибn)╝╥гмЗЇ(guио)╝Й(jик)Мг(zhuибn)╝╥г╗╚ч╣√╥к╘┌№h╒■▓┐щT(mижn)гм╥╘╣┘▒╛╬╗Ющ╗ї╡A(chи│)гм▀АХ■(huим)╙╨╠О╝Й(jик)╤╨╛┐ЖTбвПd╝Й(jик)╤╨╛┐ЖTбв╩б▓┐╝Й(jик)╤╨╛┐ЖT╓о▓юДeбг╧рСк(yийng)╡─╖Q(chиеng)╓^гм─│╨й═м╚╩▀АХr(shик)│гМв╞ф╙б╘┌╫╘╝║├√╞м╔╧гм╥¤╥╘ЮщШsбгґw╓╞═т╡─МW(xuиж)╒▀╛═Ы](mижi)╙╨МW(xuиж)╨g(shи┤)┬Ъ╖Q(chиеng)┐╔╤╘гм═мХr(shик)╥▓Ы](mижi)╙╨╚ч┤╦П═(fи┤)ыs╡─╔э╖▌Ш╦(biибo)╫R(shик)гм┤ґ▓╗┴╦╙╨╨й═м╚╩Х■(huим)╫╘╖Q(chиеng)╜╠╩┌бв╤╨╛┐ЖTгм╙╨╡─╚╦╙X(juиж)╡├▀@Ш╙▀А▓╗ЙҐ╔є╓┴╫╘╖Q(chиеng)б░╕▀╝Й(jик)б▒╤╨╛┐ЖTбг╙╨╡─╚╦╥▓╘S╩╟╨─╙╨▓╗╕╩гмХ■(huим)═и▀^(guи░)ъP(guибn)╧╡(╥▓╙╨╩▄╞╕╡─)┼кВА(gии)╝ц┬Ъ╜╠╩┌бв╤╨╛┐ЖT╓оюР(lииi)╡─╖Q(chиеng)╠Ц(hидo)бг╙╨╡─╚╦╗Ґ╘S│І╙┌СН╩└╝╡╦╫гм╗Ґ╒▀│І╙┌╨╤─┐гмХ■(huим)╙╨╥т╒f(shuин)╫╘╝║╩╟б░кЪ(dи▓)┴вб▒МW(xuиж)╒▀бг╙╔╙┌╘┌╬я┘|(zhим)╔╧╛л╔ё╔╧ґw╓╞Г╚(nииi)┼c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Е^(qи▒)Дeгм▓╗╩╟╢р┼c╔┘бв║ё┼c▒б╡─ЖЦ(wииn)ю}гм╢Ї╩╟╙╨┼cЯo(wи▓)╡─ЖЦ(wииn)ю}гм▀@╖N╘н╔·СB(tидi)╡─▓юДeгм║▄┐╔─▄╩╟Г╔юР(lииi)▓╗═мМW(xuиж)╒▀╓о╦ї╥╘▓╗═м╡─╔юМ╙╘н╥Ґбг бббб╙╔╙┌ґw╓╞Г╚(nииi)┼c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мгм╥╗юР(lииi)╩╟ЗЇ(guио)╝╥ЩC(jий)╞і╓╨╡─┬Ъ─▄▓┐╝■гм╥╗юР(lииi)╩╟ЗЇ(guио)╝╥ЩC(jий)╞і╓о═т╡─╫╘╙╔▀\(yи┤n)╨╨╚║ґwгм╦√ВГ╒╞╬╒╡─┘Y╘┤╛═▓╗─▄╧р╠с▓в╒Убг╩╫╧╚гм╤╨╛┐╜Ы(jийng)┘M(fииi)гмґw╓╞Г╚(nииi)╡─╫╘╚╗╙╔╒■╕о╠с╣йгм╕і╖N╒nю}╜Ы(jийng)┘M(fииi)бвэЧ(xiидng)─┐╜Ы(jийng)┘M(fииi)бв╤╨╛┐╗ї╜Ёгм┐╔╓^├√─┐╖▒╢рбг├┐эЧ(xiидng)╤╨╛┐╔┘ДtО╫╚f(wидn)╘кгм╢рДtО╫╩о╚f(wидn)╔╧░┘╚f(wидn)бгУ■(jи┤)╒f(shuин)гм─│╓╨╤ы╓╪┤ґ╤╨╛┐эЧ(xiидng)─┐╤╨╛┐│І░ц╥╗▒╛ХЇ(shи▒)╡─╜Ы(jийng)┘M(fииi)╛═100╚f(wидn)бгоФ(dибng)╚╗гм│¤▀^(guи░)╥╗╨й▓┐╬пбв╥╗╨йЖ╬╬╗╫╘╝║╡─╒nю}╩╟╖тщ]╒╨Ш╦(biибo)╓о═тгмЗЇ(guио)╝╥╥▓╙╨╥╗╨й┤ґ╡─╗ї╜ЁэЧ(xiидng)─┐Мж(duим)╔чХ■(huим)╩╟щ_(kибi)╖┼╩╜╡─гм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е╔ъ╒И(qилng)ЗЇ(guио)╝╥╕іюР(lииi)╗ї╜Ё╒nю}бг╡л╘┌ЗЇ(guио)╝╥┬Ъ─▄ЩC(jий)╞і╔╧╡─МW(xuиж)╒▀┼c▓╗╘┌╞ф╓╨╡─▀А╩╟╙╨╦їЕ^(qи▒)Дe╡─гмУQ╛ф╘Т(huид)╒f(shuин)гм├№╓╨┬╩╩╟▓╗═м╡─бг╝┤┴юґw╓╞═т╡─│╔╣жл@╡├┴╦─│эЧ(xiидng)╒nю}гм─╟╦√╥▓╛═╡╚╙┌╖╓Хr(shик)╢╬│╔Ющґw╓╞Г╚(nииi)МW(xuиж)╒▀гм▓╗╘┘╩╟ґw╓╞═ткЪ(dи▓)┴вМW(xuиж)╒▀╡─бг╝┤┴юП─╩┬╧р═м╒nю}╡─╤╨╛┐гмґw╓╞Г╚(nииi)═т╡─МW(xuиж)╒▀┘Y┴╧┘Y╘┤═мШ╙╠ь▓ю╡╪Дeбг╙╨╨й┘Y┴╧╩╟┐╔─▄═и▀^(guи░)┘П(gи░u)┘I(mигi)л@╡├гм╡л╙╨╨й┘Y┴╧╩╟ыy╥╘Мж(duим)ґw╓╞═тМW(xuиж)╒▀щ_(kибi)╖┼╡─бгэЧ(xiидng)─┐шb╢и┼c╘u(pикng)кД(jiигng)гм═мШ╙╩╟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ПК(qiивng)эЧ(xiидng)бг╫╘╝║│І╡─хX(qiивn)╫І│І╡─╤╨╛┐│╔╣√гм═и│г╙╓Х■(huим)╫╘╝║╘┘│ІхX(qiивn)╒╥Мг(zhuибn)╝╥╘u(pикng)МПшb╢ибг▒M╣▄?chие)?guио)╝╥эЧ(xiидng)─┐мF(xiидn)╘┌МН(shик)╨╨┴╦├дшbгм╡л╞фщg┬й╢┤░┘│ІгмМН(shик)ыy╥╘шb╢и╒У╕▀╧┬бг╓┴╙┌╗ихX(qiивn)щ_(kибi)шb╢иХ■(huим)гм╕№╩╟╗ихX(qiивn)┘I(mигi)║├╡─┤ґ┘u(mидi)ИІ(chигng)бг╒f(shuин)╡╜кД(jiигng)эЧ(xiидng)гм╚е╡╜╖╜╓█╫╙╡─б░╨┬╒Z(yи│)╜zб▒╔╧Юg╙[╥╗╧┬гм╒ц╜╨╚╦╡╣╬№╥╗┐┌ЫІЪтбгкД(jiигng)эЧ(xiидng)╓╨╡─╕пФбгм┼c╣┘ИІ(chигng)╓╨╕пФб┐░╖Q(chиеng)М\╔·╨╓╡▄бг▀@╥╗╟╨Мж(duим)╙┌ґw╓╞═тМW(xuиж)╒▀Бэ(lивi)╒f(shuин)гмыm╚╗Ы](mижi)╙╨─╟╨й┘Y╘┤гмЫ](mижi)╙╨╥▓┴Tгм┐╔─▄Х■(huим)╕№╔┘╨й╛л╔ё╬█╚╛бг бббб╒¤╙╔╙┌▓╗═м╡─╣йЁB(yигng)бв▓╗═м╡─╔чХ■(huим)╡╪╬╗гмЫQ╢иГ╔юР(lииi)▓╗═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і╫╘│╨У·(dибn)╡─┬Ъ─▄бв╪Я(zиж)╚╬бв╪У(fи┤)╪Я(zиж)╡─Мж(duим)╧ґ╛═┤ґ▓╗╧р═мбг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о┬Ъ─▄▀\(yи┤n)▐D(zhuигn)╓╨─│╖N┬Ъ─▄╡─│╨У·(dибn)╒▀гм╥▓╛═╩╟╒f(shuин)гм╦√ВГ╡─╤╨╛┐╩╟Ющ╒■╕о┬Ъ─▄╖■Д╒(wи┤)╡─бг╦√ВГ▒╪эЪ▀@Ш╙╫Ігм▀@╩╟╦√ВГСк(yийng)У·(dибn)оФ(dибng)?shи┤)─╪?zиж)╚╬бг╢Ї╟╥╦√ВГ╡─╚л▓┐╤╨╛┐▒╪эЪМж(duим)мF(xiидn)╨╨ґw╓╞┼cмF(xiидn)╨╨╒■▓▀╪У(fи┤)╪Я(zиж)гм▒╪эЪМж(duим)юI(lилng)Мз(dигo)╥тИD╪У(fи┤)╪Я(zиж)бгоФ(dибng)╚╗гм╦√ВГ╡─╤╨╛┐│╔╣√┐╔╥╘╙╨кЪ(dи▓)┴в╥К(jiидn)╜тгм┐╔╥╘┼cмF(xiидn)╨╨╒■▓▀бвмF(xiидn)╨╨└э╒У╙^№c(diигn)▓╗╥╗╓┬бг╡л╤╨╛┐│╔╣√╩╟╥╗╗╪╩┬гмМж(duим)═т╤╘╒У▒╪эЪ┼c№h║═╒■╕о╡─╒■▓▀▒г│╓╥╗╓┬бг╚ч╣√╦√│╘╪Ф(cивi)╒■╡─яИгм▓╗Ющ╒■╕о╤╨╛┐╒nю}╖■Д╒(wи┤)гм╚ч╣√╦√─├╓Ї╪Ф(cивi)╒■╣йЁB(yигng)╡─хX(qiивn)гмЕs╕╔╫╘╝║╡─╦╜╗ю╔є╓┴╕╔╨й╖┤╒■╕о╖┤мF(xiидn)╨╨╒■▓▀╡─╗югм╚ч╣√╦√╘┌╣лщ_(kибi)ИІ(chигng)║╧бв╗Ґ╒▀щ_(kибi)╖┼├╜ґw╔╧╡─╤╘╒У┼c╓▒╜╙┼·╘u(pикng)╣йЁB(yигng)╦√╡─╒■╕огм─╟╦√╛═╖╕┴╦ґw╓╞Г╚(nииi)╜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о┤ґ╝╔бг╥Ґ?yидn)щ▀@╩╟З└(yивn)╓╪╡─▀`╖╕┬ЪШI(yии)╡└╡┬гб╧р▒╚╓о╧┬гм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і╔є╓┴╫╘╙╔╡├╢р┴╦бг╦√┐╔╥╘═ъ╚л┬а(tийng)╙╔╫╘╝║╡─┐╞МW(xuиж)╤╨╛┐╡─│╔╣√╓╕╥¤╦√╡─╤╘╨╨гм╦√┐╔╥╘═ъ╚л╚╬╙╔╒l(shuик)╜oхX(qiивn)╜o╒l(shuик)╒f(shuин)╘Т(huид)бв╜o╒l(shuик)▐q╫o(hи┤)гм╦√┐╔╥╘ыS╨─╦ї╙√╡╪Мж(duим)мF(xiидn)╨╨╒■▓▀░l(fиб)▒э╘u(pикng)╒У╔є╓┴З└(yивn)ЕЦ┼·╘u(pикng)гм╓╗╥к╦√╘┌мF(xiидn)╨╨╡─╖и┬╔╖и╥О(guий)╓оГ╚(nииi)бг╦√╘є├┤╒f(shuин)▓╗Х■(huим)╙╨╚╦╒f(shuин)╦√▀`▒│┬ЪШI(yии)╡└╡┬бг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в╧у╕█МW(xuиж)╒▀└╔╧╠╞╜гм│╔╣ж╡╪╤▌└[┴╦▀@╖N╜╟╔лбг ббббґw╓╞═т╜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Ы](mижi)╙╨╣йЁB(yигng)┼c╥К(jiидn)╜т╓ощg╡─ъP(guибn)╧╡гм╥▓╛═Ы](mижi)╙╨┴╦└√╥цъP(guибn)╧╡гм╥╗░у╒f(shuин)Бэ(lивi)гм╦√ВГ╠О╙┌╕№┐═╙^бв╕№кЪ(dи▓)┴вбв╕№╫╘╙╔╡─╬╗╓├гм╥Ґ╢Ї╦√ВГ╡─╥К(jiидn)╜т╙╨╠╪Дe╓╪╥к╡─╥т┴xбг╬╥▀@Ш╙╒f(shuин)гм▓в▓╗╩╟╥к▌p╥Хґw╓╞Г╚(nииi)╡─МW(xuиж)╒▀гм╦√ВГ╫╘╝║╡─ГЮ(yинu)Д▌(shим)гм╜Ы(jийng)┘M(fииi)ГЮ(yинu)Д▌(shим)бв┘Y┴╧ГЮ(yинu)Д▌(shим)бв╚╦┴жГЮ(yинu)Д▌(shим)гм╢Ї╟╥╦√ВГ╡─╤╨╛┐│╔╣√╕№╚▌╥╫л@╡├╣┘╖╜│╨╒J(rииn)бг бббб╬╥╧ы╙╨┴╦╥╘╔╧О╫ВА(gии)╓і╥к▀Й▌Л╜Y(jiиж)╒Угм▒у▓╗ыy╤▌└[│ІГ╔юР(lииi)▓╗═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цМж(duим)ЗЇ(guио)╝╥╜Ы(jийng)Э·(jим)ґw╓╞╕─╕я┼c░l(fиб)╒╣бв├цМж(duим)ЗЇ(guио)╝╥╜Ы(jийng)Э·(jим)╒■▓▀бв├цМж(duим)╜Ы(jийng)Э·(jим)╔·╗ю╓╨│ІмF(xiидn)╡─╕і╖NмF(xiидn)╧ґ╜o│І╜тсМ╡─оР═мбг бббб╜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N┬ЪШI(yии)гм╦№▓╗╩╟╡└╡┬Ш╦(biибo)ЧU бббб╜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c╕іюР(lииi)П─╩┬▓╗═м╨╨ШI(yии)╡─╚╦╚║╥╗Ш╙гм╙╨╤к╙╨╚тгм╞▀╟щ┴ї╙√гм═мХr(shик)╥▓╫╖├√╓Ё└√бг╦√ВГ▓╗╩╟╥╗╚║╡└╡┬╛¤╫╙гм▓╗╩╟╥╗╚║Яo(wи▓)╙√│м╚╦бг╦√ВГ╥▓Х■(huим)ЮщхX(qiивn)╪Ф(cивi)Д╙(dи░ng)╨─гмЮщ├└╔лД╙(dи░ng)╨─гмЮщ├√╫u(yи┤)Д╙(dи░ng)╨─бг╦╬╒ц╫┌(┌w║у)б╢Дю(lим)МW(xuиж)╞кб╖▓╗╩╟╒f(shuин)г║╕╗╝╥▓╗╙├┘I(mигi)┴╝╠ягмХЇ(shи▒)╓╨╫╘╙╨╟зцR╦┌г╗░▓╛╙▓╗╙├╝▄╕▀Ш╟гмХЇ(shи▒)╓╨╫╘╙╨№S╜Ё╬▌г╗╚в╞▐─к║▐Яo(wи▓)┴╝├╜гмХЇ(shи▒)╓╨╫╘╙╨юБ╚ч╙ёг╗│ІщT(mижn)─к║▐Яo(wи▓)╚╦ыSгмХЇ(shи▒)╓╨▄З(chие)ёR╢р╚ч┤╪г╗─╨Г║╙√╦ь╞╜╔·╓╛гм╬х╜Ы(jийng)╟┌╧Ґ┤░╟░╫xбг─╟Хr(shик)╗╩╡█(╝┤ЗЇ(guио)╝╥╘к╩╫гм╡л▀@ВА(gии)ЗЇ(guио)╝╥╩╟╦√╝╥└я╡─)╢╝▀@Ш╙╠Ц(hидo)╒┘╠ь╧┬╫xХЇ(shи▒)╚╦гм┐╔╥К(jiидn)▀@▀А╩╟╙╨╨йВА(gии)╡└└э╡─бг╩╟╡─гм╫іЮщ╔чХ■(huим)│╔ЖTгм╒l(shuик)─▄ЙҐ╥к╟ґ╜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zиж)o╦╜г┐ бббб▀@└я┐╔─▄╙╨Г╔ВА(gии)М╙├ц╡─ЖЦ(wииn)ю}╥к╖╓╟хбгЯo(wи▓)╒У╦√┴в╫у╙┌ґw╓╞Г╚(nииi)▀А╩╟ґw╓╞═тгм╥╗╩╟╫іЮщМW(xuиж)╨g(shи┤)╤╨╛┐╡─╜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гм╢■╩╟╫іЮщ╔чХ■(huим)╔·╗ю╓╨╚╦╡─╜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бг╥╗░у╒f(shuин)Бэ(lивi)гм╫іЮщМW(xuиж)╒▀гм┐╞МW(xuиж)╥т┴x╔╧╡─МW(xuиж)╨g(shи┤)╤╨╛┐┼c╣ж└√║┴Яo(wи▓)ъP(guибn)╧╡┐╔╤╘гм╥Ґ╢Ї╦√╡─МW(xuиж)╨g(shи┤)╗юД╙(dи░ng)╫╘╩╝╓┴╜K╢╝▓╗─▄╙╨╚╬║╬╜Ы(jийng)Э·(jим)└√╥ц╚б╧Ґгм▓╗─▄╙╨╜z║┴╡─├√└√╥к╟ґбг╡л╩╟гм╫іЮщ╔·╗ю╓╨╡─╚╦гм╦√▒╪╚╗╥к╫╖╟ґ╜Ы(jийng)Э·(jим)└√╥цгм╫╖╟ґ├√╫u(yи┤)╡╪╬╗бг═ъ╚лМвГ╔╢╝╕ю┴╤щ_(kибi)Бэ(lивi)╝Г╢Ї╙╓╝ГМW(xuиж)╒▀гм┐╔╒f(shuин)╩╟┴╚╚Є│┐╨╟бг╗╪═√╓╨ЗЇ(guио)гмЪv╩╖╔╧┤_╙╨▀^(guи░)╥╗╨й╬─╚╦МW(xuиж)╩┐гм╟х╕▀╔ю╝Ггм┼c╩└╦╫╕┼╬┤┤ю╜чгм╔є╗Ґ┼c╖▓╚╦П─▓╗┤ю╘Т(huид)бг╡л╦√ВГ╢рЮщ╝╥╪Ф(cивi)╚f(wидn)╪Ю╡─╕╗║└╫╙╡▄бг╚ч╣√Ы](mижi)╙╨╦√ВГ╡─╕╕╨╓Тъ╩└╦╫╡─хX(qiивn)гм▓в╖e└█╫уЙҐ╡─╪Ф(cивi)╕╗гм╦√ВГ─▄╙╨яhяh╙√╧╔╡─МW(xuиж)╨g(shи┤)╔·╤─г┐П─╜KШO╡─╥т┴x╔╧╓vгмЫ](mижi)╙╨╜Ы(jийng)Э·(jим)└√╥ц╓з│╓╡─МW(xuиж)╨g(shи┤)╤╨╛┐П─Бэ(lивi)╛═▓╗┤ц╘┌гмМW(xuиж)╨g(shи┤)╤╨╛┐╡─╝Г┤т╨╘П─Бэ(lивi)╢╝╩╟╧рМж(duим)╡─бг┐┤╡╜▀@╥╗№c(diигn)╬╥ВГ╥к╒f(shuин)гм▀А╡╣▓╗╩╟Мж(duи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к▓╗╥кМТ╚▌╡─ЖЦ(wииn)ю}гм╢Ї╩╟╘┌─╟ВА(gии)М╙├ц╔╧╜o╙ш╜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Ы(jийng)Э·(jим)└√╥цбг бббб╜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Ш╦(biибo)ЧUгм╦№╓╗╩╟╥╗щT(mижn)МW(xuиж)ЖЦ(wииn)г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o╙шМW(xuиж)╒▀ВГ╡─╓╗╩╟╥╗╖N┬ЪШI(yии)бг▓╗╥к╒f(shuин)╜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э╡└╡┬гм╛═╩╟╒■╓╬МW(xuиж)╔є╓┴╡└╡┬ВР└эМW(xuиж)гм═мШ╙╥▓▓╗╩╟бг╫іЮщ┬ЪШI(yии)гм╦№┼c╔чХ■(huим)╔╧╞▀╩о╢■╨╨╥╗Ш╙гм▒╦┤╦Ы](mижi)╙╨╕▀╧┬┘F┘v╓о╖╓бг╒╛╘┌▀@╓╨щg╡─╚╦гм═мШ╙╥▓╩╟╕і╔л╚╦╡╚бг╘┌▀@└ягм═мШ╙╓v╡└╡┬(ВА(gии)╚╦╞╖╕ёбв┬ЪШI(yии)╡└╡┬)гм═мШ╙╓v┬ЪШI(yии)╦оЬ╩(zhи│n)бг бббб╨─ь`┼c╥Х╥░гм╝┤╡└╡┬┼c╦о╞╜гмГ╔╒▀╙╨─│╖N┬У(liивn)╧╡гм╡л╧р╗е▒│ыx╡─╟щ╨╬╥р╙╨░l(fиб)╔·бг▓┘╩╪║├гмМW(xuиж)╨g(shи┤)╦о╞╜╕▀╩╟╥╗╖N╟щ╨╬гм▓┘╩╪║├гмМW(xuиж)╨g(shи┤)╦о╞╜╞╜╞╜╩╟╥╗╖N╟щ╨╬гм▓┘╩╪▓югмМW(xuиж)╨g(shи┤)╦о╞╜╕▀╩╟╥╗╖N╟щ╨╬гмГ╔╒▀╢╝▓юДt╩╟╙╓╥╗╖N╟щ╨╬бг▀@╦─юР(lииi)МW(xuиж)╒▀╓╨гмыpГЮ(yинu)╨у╩╟╩└╚╦┘Э├└╡─г╗ыpР║┴╙╩╟╩└╚╦═┘ЧЙ╡─г╗▓┘╩╪ыm║├╦о╞╜╞╜╙╣╒▀Яo(wи▓)║ж╥рЯo(wи▓)╥цбг╖┤╡╣▓┘╩╪▓югм╦о╞╜╕▀╡─╜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Ы(jийng)Э·(jим)╔чХ■(huим)╓╨╥¤░l(fиб)┴╦▓╗╨б╡─╒Ё╩Обг бббб│І╔·╙┌╠K╕ё╠m╡─╝s║▓бд┴_┐╔╖Q(chиеng)╓оЮщҐ_╫╙╜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цгм╡л┼c╥╘║ґ╡─╝ГҐ_╫╙╧р▒╚гм╦√Еs╧роФ(dибng)╙╨МW(xuиж)ЖЦ(wииn)бг╦√╥╗╩╓▓▀ДЭ┴╦▓вМН(shик)ыH▓┘┐╪┴╦│Є├√╒╤╓Ї╡─б░├▄╬і╬і▒╚╙Л(jим)ДЭб▒Ґ_╛╓гм╫╘╝║У╞╫у┴╦├√└√гмЕs┴ю╖иЗЇ(guио)╓│├ё╡╪├▄╬і╬і▒╚╜Ы(jийng)Э·(jим)▒└Эвбг╡л▀@▓в▓╗─▄╤┌╔w╦√1705─ъ╦їМС(xiиз)╡─б╢╪ЫО┼┼c┘Q(mидo)╥╫╤╨╛┐г║ЗЇ(guио)╝╥╪ЫО┼╣й╜o╡─╜и╫hб╖╓╨МW(xuиж)╨g(shи┤)│╔╛═бг╒¤╥Ґ?yидn)щ╚ч┤╦гмёR┐╦╦╝╖Q(chиеng)╦√б░╝╚╩╟Ґ_╫╙гм╙╓╩╟юA(yи┤)╤╘╝╥б▒бг┴_╒¤┤_юA(yи┤)╤╘┴╦╨┼╙├ґw╧╡╡─╓╪╥к╫і╙├╥╘╝░╙├╝ИО┼┤·▒э╜ЁМ┘╪ЫО┼╡─╓╪╥к╨╘гм═мХr(shик)┴_юA(yи┤)╤╘┴╦╪ЫО┼Мж(duим)╜Ы(jийng)Э·(jим)╡─┤╠╝д╫і╙├бг бббб╜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обд┼ф╡┌гм╙вЗЇ(guио)╣┼╡ф╜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ДУ(chuидng)╩╝╚╦гм╩╟╥╗╬╗МW(xuиж)ЖЦ(wииn)ШO║├╚╦╞╖ШO▓ю╡─╡ф╨═╚╦╬ябгЮщ┴╦╣ж├√гм╦√▓╗Уё╩╓╢╬╧Ґ╔╧┼└гм╘┌╦√╡╟╔╧МW(xuиж)╨g(shи┤)╕▀╖х╡─═мХr(shик)гм╨─ь`╥▓╧┬╡╜┴╦╚╦щg╡╪кzбг┼ф╡┌│╔Ющб░╜y(tипng)╙Л(jим)МW(xuиж)╓о╕╕б▒гм┼ф╡┌╡ь╢и┴╦Д┌Д╙(dи░ng)Гr(jiид)╓╡╒У╡─╗ї╡A(chи│)гмб░═┴╡╪╩╟╪Ф(cивi)╕╗╓о─╕гмД┌Д╙(dи░ng)╩╟╪Ф(cивi)╕╗╓о╕╕б▒╓┴╜ё▀АщWаq╓Ї╣т▓╩бг┐╔╩╟╦√╥╘Щр(quивn)╓\╦╜гм▒│┼╤└э╧ыгм┘u(mидi)╓і╟ґШsгм╞ф╔·╗ю╫іяL(fиеng)╥▓ШO▓╗Щz№c(diигn)бг╥╗Хr(shик)Ющ╩└╚╦═┘ЧЙбг┼ф╡┌╡─╫╙МOВГ╥╗╓▒Ы](mижi)░╤┼ф╡┌╡─╓Ї╫і╒√└э│І░цбгёR┐╦╦╝╒J(rииn)Ющгм▀@╩╟╥Ґ?yидn)щ│І░ц╓Ї╫і▒╪эЪ╙╨╫і╒▀Ві╙Ыгм╡лб░▀@ВА(gии)╦╝╧ы├ЄфJ╢Ї╙╓╠╪Дe▌p╕б╡─▄Ксt(yий)гм╝╚─▄╘┌┐╦ВР═■аЦ▒╙╫o(hи┤)╓о╧┬┬╙КZР█(идi)аЦ╠mгм╙╓─▄Ющ▀@╖N┬╙КZ╧Ґ▓щ└э╢■╩└╣Ґ╟ґ▒╪╥к╡─╛Є╩┐╖Q(chиеng)╠Ц(hидo)гм▀@Ш╙╡─╫ц╧ё╩╟▓╗▒у╣л╓T╙┌╩└╡─бгб▒ бббб╜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f(shuин)╩╖╔╧┴э╥╗╬╗┤ґ╝╥йдйдёRаЦ╦_╦╣гм╦√╡─б╢╚╦┐┌╒Уб╖┤ґ╝s╩╟▒╢╩▄┼·╘u(pикng)╡─╛▐╓Їгм╦√П─Д╙(dи░ng)╬я╩└╜ч╡─╖▒╓│╥О(guий)┬╔╧ы╡╜┴╦╚╦юР(lииi)╫╘╔эгм▓в╥╘╙вЗЇ(guио)оФ(dибng)Хr(shик)╡─╜y(tипng)╙Л(jим)┘Y┴╧╫і│І┼╨Фргм╚╦юР(lииi)╔чХ■(huим)╓╨╚╦┐┌╘ІщL(zhигng)▒╪╚╗│м▀^(guи░)╪Ф(cивi)╕╗╘ІщL(zhигng)гм╙╔┤╦▒╪╚╗ОзБэ(lивi)╔чХ■(huим)Ю─(zибi)ыyбг╦√╩╟╡┌╥╗ВА(gии)└э╨╘╡╪╠с│І▒╪эЪМж(duим)╚╦┐┌╡─╫╘╙╔╘ІщL(zhигng)▀M(jимn)╨╨╥╓╓╞╡─╦╝╧ы╝╥гмМв╞ф╖Q(chиеng)╓оЮщ╚╦юР(lииi)╙Л(jим)ДЭ╔·╙¤╡─▒╟╫цСк(yийng)оФ(dибng)╒f(shuин)╩╟╩о╖╓╟боФ(dибng)?shи┤)─бг╚╗╢Їгм╦√╡─╚╦┐┌╒У╘т╙І┴╦┤╦╞Ё▒╦╖№╡─╙С╖е╓┴╜ё▀А╙╨╚╦╘┌Мж(duим)╞ф╓╕╪Я(zиж)бг▀@╞фщgгм┼c╙╔╙┌ёRаЦ╦_╦╣╚╦┐┌╒У▒╛╔э╡─╛╓╧▐╨╘╥▓╘S╙╨ъP(guибn)гм╡л═мХr(shик)╥▓┼c╚╦ВГ╡─╒`╫x╙╨ъP(guибn)бг╠╪Дe╩╟гмоФ(dибng)╚╦ВГ╫в╥т╡╜▀@ВА(gии)╠с│л╙Л(jим)ДЭ╔·╙¤╡──┴ОЯгм╘┌▒п╠ьСС╚╦Ющ╚╦┐┌╡─╘ІщL(zhигng)Сn(yинu)╙Є╡─Хr(shик)║Ґгм╦√╫╘╝║О╫║є║┴Яo(wи▓)╣Э(jiиж)╓╞╡╪│╔Ющ╥╗ВА(gии)╢р╫╙┼о╡─╕╕╙Hбг бббб╜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Ющя@МW(xuиж)гм╩╣П─╩┬▀@ВА(gии)╨╨ШI(yии)╡─МW(xuиж)╒▀╣тнh(huивn)▒╢╘Ібг╚╗╢Їгм╥╗оФ(dибng)╔чХ■(huим)╡─ъP(guибn)╫в╢╚▀^(guи░)╙┌ГA╨▒Хr(shик)гмХ■(huим)┴ю╩┬СB(tидi)╝▒Дб─ц▐D(zhuигn)бг─┐╟░╓╨ЗЇ(guио)╜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ъа(duим)╬щ╒¤╘┌╘т╙І▀@╖N╔чХ■(huим)╦╝│▒Ы_УЄбг╔чХ■(huим)МН(shик)╘┌Ск(yийng)оФ(dибng)МТ╚▌╡╪Мж(duим)┤¤╜Ы(jийng)Э·(jим)МW(xuиж)╝╥ВГгм╥Ґ?yидn)щ╦√ВГ┼c╚╬║╬┬ЪШI(yии)╥╗Ш╙гм┐╔╥╘╕▀╔╨┐╔╥╘▒░╬вгм┐╔╥╘╫╖├√╓Ё└√┐╔╥╘╡н▓┤├√└√гм┐╔╥╘┼cП─╩┬╚╬║╬╨╨оФ(dибng)╓╨╚╦ВГ░l(fиб)╔·╥╗╟╨╨╨Ющ╥╗Ш╙бг
б╛╘u(pикng)╒Уб┐б╛╒Д╣╔╒У╜Ёб┐б╛╩╒▓╪┤╦эУ(yии)б┐б╛╣╔╞▒Хr(shик)Хr(shик)┐┤б┐б╛┤ґ ╓╨ ╨бб┐
б╛╢р╖N╖╜╩╜┐┤╨┬┬Дб┐б╛┤Ґ╙бб┐б╛ъP(guибn)щ]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