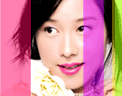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關純(北京)
在“討伐”中國經濟學家的聲浪中,我驀然想起了顧準先生——“用鮮血作墨水”寫作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我剛剛讀完新近出版的《顧準畫傳》,書頁上留下斑斑淚痕。我不是性情中柔弱的人,可是顧準先生的人格魅力,讓你無法自已。顧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更是一位令人景仰的“道德的實踐者”。許紀霖教授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
》一書中說,“顧準本人很少有道德的話語,我們翻遍《顧準文集》,沒有發現任何的道德高調,只有對傳統理想主義的冷靜反省。他個人的道德高尚不是通過高調實現的,而是以悲壯的身體力行實現的。”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稱譽顧準先生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今日之中國,“市場經濟”已為人們耳熟能詳,然而在50年前,敢提出如此超前的見解,那是需要具有追求真理的大無畏精神、科學的思想方法和豐厚的學識底蘊的。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正是在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啟發下,對“斯大林經濟模式”的深刻反思。顧準的文章有的放矢,針對當時國家計委一位“高官”的某些不正確觀點予以批評。人們還記憶猶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學泰斗孫冶方首倡“尊重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出杰出貢獻。被顧準視為“知己”的孫冶方,在謝世前一再囑咐他的兩位學生吳敬璉和張卓元,要把顧準的《試論》一文附在自己的文集中。并在《后記》里講,“是年初夏,顧準同志就提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問題,來同我研究……”顧準、孫冶方兩位互為“知己”的偉大經濟學家,留給后人一曲津津樂道的“學林佳話”。
說顧準是“中國的脊梁”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他當之無愧。顧準的超前思維令人驚嘆。早在1971年,顧準就在《十年來的蘇聯經濟》文稿中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癥了。”顧準還更加犀利地指出,蘇聯的經濟體制“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制度”。……“人間正道是滄桑”,20年后的蘇聯解體,證實了顧準的預言;也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敲響了振聾發聵的警鐘。
顧準敏銳的思想洞察力緣于他對歷史的研究和思考。1974年他在《希臘城邦制度》一書中,“以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也就是我們古代的專制主義政體與希臘民主制度的截然區別。”這樣的結論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但是“感情當然不能代替事實”。顧準命途多舛,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他戴著沉重的精神枷鎖,走進書齋,攻讀《資本論》,“長夜難明赤縣天”,警世華章留后人。1957年中蘇聯合考察黑龍江,他看不慣蘇聯專家大國沙文主義的蠻橫態度,采取了據理力爭、針鋒相對的立場。結果被考察組的人員記錄在案,以破壞中蘇關系的“罪名”劃為“右派”。1964年,因為直言批評毛主席的個人迷信,再次加冕“右派”。然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顧準始終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寧鳴而生,不默而死”,埋頭讀書,獨立思考,在精神世界里,天馬行空,創造思維,成為中國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
顧準“悲壯的道德實踐”,對我們今天的某些“公共知識分子”倒是一面鏡子。許紀霖教授為某些“知識明星”畫像——“為了迎合傳媒,吸引公眾,成為很可笑的‘文化思想明星’。他們不在學理上像顧準那樣下功夫,而是在修辭上努力,起勁地煽情、作秀、唱高調。雖然他們的‘思想’在追遂時髦的人看來很尖銳、很獨特,但是在真正有思想的人看來,會發現那些華麗的辭藻和機智的修辭背后,實際上是一個空蕩的靈魂,一個蒼白的手勢,縱然能夠泛起一時的摩登泡沫,但很快成為過眼云煙,像大浪淘沙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顧準“本來有一個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錦。但是他‘糟蹋’了這一前程,走上了一條料無始終的不歸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給抽屜寫作,給后人寫作,而不是給自己的學術前程寫作”。顧準臨終時,在床榻旁一直陪伴他的吳敬璉握著先生的手,看著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魂魄歸西,離我們而去。“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顧準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聳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天賦的聰明才智方面,還是道德文章方面,我們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達到的境界。”
顧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時代更需要像顧準這樣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