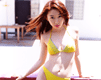耐克“包身工”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6月13日 16:20 《商務周刊》雜志 | ||||||||
|
為耐克、阿迪達斯等世界名牌代工,原本是件好事。然而在跨國公司、合約工廠乃至當地政府對各自利益的“合理追求”下,工廠主成了壓榨專家,高效率的流水線成了捆在工人身上高速運轉并不斷縮緊的緊箍咒。雖然與舊上海的包身工不同,但現代的契約不斷降低著合約工廠的議價能力,再由合約工廠傳導到工人身上,同樣擠壓著他們的血汗和忍受空間。 這是產業鏈自身逐步成熟的必然,還是產業外部的制度性壓榨?在政府、跨國公司、 □記者 王強 胥曉鶯 耐克公司受到了贊揚。因為它主動揭露了自己的代工工廠侵犯工人權益的現象。 4月13日,耐克公司向外界公布了一份名為《2004財年耐克合作責任報告》,公開了其700多家海外合同制造廠的名稱和所在地。在報告中,耐克公司承認,與其合作的海外合約工廠確有強制工人延時工作等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其中,耐克在2003年和2004年審查了569家海外廠家,發現南亞地區的工廠問題比較嚴重。有一半的當地工廠要求工人每周工作超過60個小時,其中超過10%的工廠對拒絕超時上班的工人做出過處罰;另外,報告還指出,很多亞洲工廠還限制工人在工作時間上廁所和喝水。 耐克這次主動公布供應鏈詳細信息,外界反映積極。國際紡織服裝皮革工人聯盟(ITGLWF)秘書長Neil Kearney稱,耐克的行動具有改革意義,“這樣大家就能知道,耐克是否貫徹了對外宣布的公司政策”。 然而一直以來,對像耐克這樣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合約工廠的情況,中國本土少有披露。根據報告,在中國內地,有124家生產商與耐克公司簽訂合約,為其進行代工生產,它們主要分布在廣東、山東、上海等地,其中東莞一地就有近20家工廠。 與中國純粹本土企業問題不同,類似耐克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合約工廠所暴露出來的利益和勞工等問題,表現出更加紛繁復雜的亂像。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和轉型國家,其現實特質和復雜性很難讓我們簡單梳理出一幅清晰的圖景和做出簡單的判斷。近日,本刊記者專赴廣東省,輾轉廣州、東莞、深圳等地深入采訪,我們發現的是跨國公司、合約工廠、地方政府和工人四方糾纏在一起的利益麻團。 工廠的暫時平靜 5月16日,東莞市長安鎮霄邊村的興昂鞋廠門口,前來招工的人群坐在樹下,相互打聽著工廠的情況。平靜的午后,很難想像一年前這里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工人騷亂。 去年3月到4月,擁有3萬多名工人的興昂國際有限公司旗下的5家鞋廠中,有4家工廠由于工人不滿自己的處境發生騷動,數千名工人卷入其中。 1991年由臺灣遷至東莞的興昂國際有限公司,最初只有千余工人,到2004年,它雇傭的工人已經達到3.5萬名,每年為耐克、銳步等國際品牌生產近3000萬雙鞋,價值超過30億元人民幣。 為興昂鞋廠工人提供過無償法律援助的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主任武紹智告訴《商務周刊》,去年的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超時勞動、伙食質量差、減少甚至拖欠工資、雇傭未成年員工,所以很難不把這些為跨國公司做訂單生產的工廠與“血汗工廠”聯系到一起。“此事件也暴露出我國刑事立法上的漏洞。資方讓工人付出了超強、超時勞動卻又不給合理的報酬,克扣、拖欠報酬,如此影響工人生存的嚴重行為,《刑法》中缺乏相應的刑事制裁。”武紹智說,“再加上一些具體行政行為不到位,就造成故意克扣和拖欠報酬大規模發生,受害的只能是弱者或者說弱勢群體。” 興昂廠的狀況不是個別現象,據廣東省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的調查,在珠三角地區,92.04%的企業存在加班,近七成的企業每周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有的甚至達到28小時。而高強度加班的同時是低廉甚至拖欠工資。據調查,1992—2004年,珠三角12年來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還趕不上2004年上半年食品價格的增長幅度。在深圳市的一次企業工資發放情況大檢查中,發現欠薪企業653家,占被查企業總數的40%多,涉及員工10多萬人次。 在采訪中,一位工頭指稱,工廠里要么沒有工會,要么設立的工會“只是在工廠向勞動部門申請加班的時候,代表工人敲上一個‘同意加班’的章而已”。 與興昂廠工人的激憤行為不同,“沉默的大多數”選擇了一走了之。2004年,珠三角喧囂了20多年的“民工潮”第一次被“民工荒”所取代。據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報告顯示,2004年珠三角缺口民工200萬,缺工比例為10%,其中深圳缺工40萬,東莞27萬。 大量工人的“用腳投票”,改善了留守珠三角的工人的生存狀況。為了留住工人,工廠普遍降低了招工條件,改善生產和生活待遇;政府則提高最低工資規定,并幫助工人追還拖欠工資;加工工廠的上游企業,那些跨國品牌公司,也加大了查廠力度,要求工廠改善勞工狀況。 公平勞工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FLA)東亞地區協調人葛友俐說:“無論是騷亂還是民工荒,都說明沒有絕對的弱者,工人們用破壞顯示了他們的力量,盡管這種破壞的力量是被動的。” 在東莞市長安鎮,一位帶著孩子的母親告訴記者,這兩年招工容易多了,工資福利也有所提高。幾乎每個受訪的工人都能準確地說出,今年3月份剛剛調整的東莞市最低工資提高了多少。還有一些工人會告訴你,興昂廠好,緯球廠好,因為它們是做品牌的,不像做雜牌的廠,品牌廠有“人權”。 晚8點多,東莞市高鎮路上的行人稀少,林立的工廠家家燈火通明,工廠對門的工人宿舍則黑漆漆一片。21歲的女工歐陽和她的伙伴們從街上漫步回來,她們都是裕元三廠的針車女工,今天是一位同事的18歲生日。工廠給她發了一張有總經理簽名的生日卡,還有生日券,月底的時候可以和其他當月過生日的員工一起去領一份禮物。 臺資的裕元集團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工廠,在高鎮有幾家分廠,給阿迪達斯、耐克等20多個國際知名品牌加工運動鞋,工人總數6萬多人。 歐陽來裕元半年了,對現在的工作相當滿意。她告訴記者,平時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雙休,趕貨的時候會加班,但加班時間不會超過2小時,加班的時候每周也能保證一天的休息。 工廠的伙食也不錯,早餐有包子、饅頭、面包、粉和豆漿。歐陽說,工廠里面“可好了”。有的地方“像花園一樣”,她們的宿舍“像洋房一樣”,8人一間,有電話,每個人有個帶鎖的柜子,一年四季有熱水沖涼。“比家里還好。”她說。 周末的時候,歐陽會睡個懶覺,然后在廠里看看電視看看碟,愛運動的工人可以打打球,還有熱心的工人參加義工團隊,給大家免費理發、修手表。 扣掉200來塊錢的食宿,歐陽每個月能領到八九百塊錢的工資。比起以前在小廠做工,雖然每月能拿一千多,歐陽還是覺得裕元更好。“小廠每天加班到12點鐘還算早的,哪里有周末,一個月就放一天假,發工資那天歡喜得不得了!”她手舞足蹈地說。 在工廠附近的大排檔,歐陽吃著“像雞蛋一樣”的日本豆腐,知足而快樂。目前在東莞,許多為跨國品牌公司代工的工廠看上去是平靜的。 耐克的責任感 工人與工廠主今天在東莞形成的平衡,不管是否是短暫的,至少說明耐克公司的努力起到了部分作用。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大量設廠,其中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工人的惡劣工作環境越來越引起國際的關注和批評,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以“耐克觀察運動”為先導的反血汗工廠運動。 這些抵制運動給跨國企業戴上了道德責任的巨大壓力。為改善外部形象,跨國企業大多選擇以訂立公司行為準則為第一步。耐克在1991年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慣例和人權的基本原則,起草了公司行為準則,禁止18歲以下人員參與制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參與生產衣服,“除非有國家法規條例的授權”;超時工作要先通知員工,并須依照當地法規給予補償;嚴格規定每工作6天必須有1天休假,每星期工作不得超過60小時。 1992年,耐克將這份公司行為準則分發到各合約工廠,此后對此準則定期進行評估和修改,它成為耐克公司對合約商在勞動與環境、安全與健康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耐克專門成立“環境、安全及衛生管理部門”,訂立安全標準,在每家工廠成立安全委員會,并為在危險環境中工作的員工配備勞動保護用具。 1997年耐克開始采用的“SHAPE”,是其最早的監察手段,它為評價合約廠商在執行有關環境、安全和衛生等準則方面的表現提供了基本的標準。它通常由耐克各產品基地的員工在一天之內完成,可以描畫出生產基地的總體狀況。 2002年,公司以行為準則為基礎,出臺了領導標準條例(Code Leadership Standards),其中包括13條人事管理標準、9條環境影響管理標準、23條安全管理標準、9條健康管理標準,這總共51條標準對行為準則作了更為詳細的補充和說明。 2003年,耐克開始采用名為“M-Audit”(管理審察)的監管活動,與“SHAPE”不同,它主要是對工作管理實務做更為深入的評估以發現問題,具體包括現場視察、文件核查以及對單個工人、管理人員和經理的密訪。耐克公司為此專門聘用了21位新員工,并對他們進行了監察工作方面的培訓。耐克認為,現在這一手段不但是公司監管活動的基礎,而且還成為公司認識與工作條件有關的問題及其影響的主要工具。 從2002年起,耐克公司還允許公平勞工協會(FLA)對自己的工廠進行不定期的獨立抽查。FLA的獨立調查是以外部視角來考察耐克供應鏈中各廠家的工作條件。每年,“公平勞工協會”平均要對耐克5%左右的供應商進行突然的獨立調查。 耐克對勞工工作條件的關注與系統的規范措施,自然也影響到了中國,但它并未充分體現在工人身上。作為耐克的合約工廠,興昂集團能感受到來自上游合作者的壓力,但隨著工時的縮短和工人休息時間的增加,廠方并不打算為工時減少支付代價。它承諾工資不減,前提是工人必須生產出同樣多的東西。 事實上,工人拿到的工資平均少了100元。廠方將此歸咎于工人效率并未提高,而工人們認為,工廠的出貨量并未減少。一位東莞的業內人士也告訴《商務周刊》,工人工時雖然被要求縮短,但耐克等公司交給合約工廠的訂單并未減少,而交貨時間的期限卻一再縮短。事實上,100元,正好相當于減少的兩個周末加班日的報酬。 2001年,阿迪達斯在裕元啟動一個提高效率的方案。工人們認為,工作時間確實縮短了,但更加辛苦,因為任務都精確地分配下來,幾乎沒有停工的時候。現在這些客戶要求工廠30天交貨,三年前同樣的貨交貨期為60天,而10年前是90天。 合約工廠面臨來自跨國公司的催貨壓力越來越大,而又不得不執行這些公司規定的企業社會責任,在保證利潤的惟一動機下,最后受傷害的只能是最弱勢的工人。 去年的東莞事件發生后,像耐克、銳步這樣的品牌不希望自己的鞋與勞資糾紛聯系在一起,他們集體向興昂施加了壓力,要求注重工人“人權”,但卻并沒有撤銷或減少訂單,也沒有放寬訂單的生產期限。 “我們的壓力非常大。”剛剛從興昂鞋廠離開的四川女工董芳,在臺威鞋廠門口等候招工。她在興昂鞋廠做鞋面,屬于流水線操作,不能壓貨,一壓就會挨班長的罵甚或罰款。“但有時候織機壞了難免會壓貨。”流水線的工作讓她覺得身心疲憊,“上廁所都必須找人替,一分鐘都不能停的。一天如果工廠定了一千件工作量,就必須完成。” 董的丈夫在臺威廠,她知道臺威廠經常要加班,有時候能到晚上一兩點鐘,但比起每時每刻高強度的工作,她更接受臺威工廠的管理方式,雖然上班時間長一點,但并不見得更累,關鍵是收入卻會更高。她自動放棄了那些大洋彼岸的跨國公司們津津樂道的“工人權益保護”。 工廠主的兩張報表 沒有更多選擇的工人們是容易滿足的。在采訪中,抱怨最多的是那些為跨國公司做代工的工廠主們。“來自耐克們的壓力,來自政府的壓力,來自工人們的壓力,來自同行的激烈競爭,我們才是在夾縫中生存啊。”在東莞打拼了十幾年的孫顯明向記者訴苦。 孫顯明是東莞常平鎮一家港資毛織廠的經理。他最頭疼的事就是客戶(品牌公司)的查廠。這家企業通過香港的幾家洋行給海外服裝品牌做來料加工。要得到那些品牌公司的訂單,就得先通過他們的審查,他們往往會委托香港的一些“公正行”來查廠。孫顯明給記者拿出厚厚一疊資料,工商登記,社會保險購買的保單,12個月的考勤記錄,安全生產、環保和消防證書……這些都是查廠時要看的內容。 在孫顯明看來,硬件的要求不難達到,最讓他犯難的還是工時、工資這些“軟要求”。客戶要求工廠生產必須符合《勞動法》,而《勞動法》規定每月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超過部分必須向當地勞動部門申請。有了申請記錄,加班時間一目了然,就必須按照《勞動法》給工人支付加班工資,平時加班需要支付1.5倍工資,周末2倍,國家法定假日則需要支付平時3倍的工錢。 在孫的工廠,工人加班和平時拿的工資是一樣的,大概每小時3元人民幣。工廠有兩份工資表,給查廠人員看的必須經過換算,做成符合《勞動法》的加班工資。 這樣的現象耐克在合約工廠里已有發現。《2004財年耐克合作責任報告》披露,一家中國供應商曾一再違反有關禁止超時工作和偽造記錄的規定,調查組制定了整改計劃,并且有耐克公司的三個業務部門協助工廠來執行這個計劃。但經過6個月的努力,工廠的狀況并無改觀,因此該廠就被耐克除名。 客戶查廠時還要求必須給工人購買保險。如果按照東莞的標準,給工人購齊養老、失業、工傷、醫療四個險種,工廠每月要為一個工人支付180元。孫有700多員工的工廠不算大,但每月交齊“四險”就是十幾萬,一年要100多萬。而工人的高流動率,更讓孫顯明覺得這筆支出太不值。 但沒有工人福利保障的資料,就拿不到品牌公司的訂單。孫顯明承認,現在只給五成的工人買了保險,大多是工作一年以上的,還讓工人自己交1/3,工廠支付120元。 相比客戶的“照章辦事”,政府對工廠還是比較“寬容”的。孫顯明介紹,如果不是客戶查廠,工廠不會主動去政府部門申請加班、購買保險。“政府也知道企業的難處,不會嚴格審查。”他說,“即使現在購買了保險,政府也知道企業流動率大,并不要求全部參保。” 招工難和查廠的要求,提高了工廠的工資成本,而這兩年毛織行業的利潤越來越薄。“你不做別人可以做啊,常平鎮、大朗鎮的大大小小毛織廠不下幾千家。現在報價都很低,低得你都不想做,但工廠開門總要維持。”孫顯明介紹說,1990年代,一件20塊錢的衣服能有六七塊錢利潤,后來只有三元,“現在也就才一塊錢的微利了”。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的工廠一年即使開足工,大概能做成衣150萬到180萬件,按照現在的市場價格,一件成衣毛利大概兩元錢,就是大概毛利300萬一年。另外,現在工廠有兩層廠房出租,一年大概有六七十萬收入。后勤、行政人員的工資每月10萬元,一年大概120萬元。水電氣、機器折舊、配件等皮費,一年起碼幾十萬。這樣,工廠一年的凈利也就是100多萬,差不多一件成衣一元錢利潤。但是為了維持工廠正常開工,孫顯明說有時候他們硬著頭皮接明知虧本的單子,“而且去年有一單,因為交貨來不及,走了空運,一次就花了80萬。”他說,自己的廠子去年實際是虧了300多萬。低薄的生產利潤讓孫顯明終日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虧損。去年他就親眼看到原來大朗鎮最大的毛織廠,四五千人的卓榮,“說倒閉就倒閉了”。 實際上,即使這么微薄的利潤,本身來路也有些不合法。在孫顯明的工廠,現在工人平均每小時3塊錢,每月平均工作300小時,收入900元。如果要補足加班工資,每個工人收入有3塊: 1)平時工資:每小時3塊,每天9小時,每月20天,即有540元; 2)平時加班工資:每小時4.5元,每天3小時,每月20天,這是270元; 3)周末加班工資:每小時6元,每天12小時,每月4天,為288元。 3塊相加,每個工人每月應得工資1098元,即每月應多得200元左右。 如果按《勞動法》規定補足工人的加班工資,孫顯明需要每月給每個工人多支付200元工錢,一年下來就是168萬元。如果再足額繳納700名工人的保險,每人180元,一年又是151萬元。孫顯明說:“這兩塊成本相加,就足以讓東莞許多代工廠虧本。” 利潤率連年下降和對低投資回報率的高度容忍,在制鞋業同樣存在。同業競爭的加劇等原因,使耐克的合約供應鏈是不斷變化的。2004財年,耐克新增了122家合約供應商,同時終止了與34家工廠的合同。耐克在報告中稱,合約工廠的變化,部分是根據消費需求與傾向的變化而做出的,還有一些則跟工廠在產品質量、交貨、價格以及合作責任方面的表現有關。東莞市當地的工廠主們普遍認為,價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要么是耐克的代工價格比那些企業的成本還高,企業沒法做,要么是企業壓人員工資成本壓得太厲害,工人都跑了,或者被耐克和政府查了。企業總是在這河邊走。” 政府的支柱產業變化論 和代工廠的未來 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加工企業審查勞工狀況,當地政府的勞動部門往往采取袖手的態度。對此,公平勞工協會(FLA)東亞地區協調員葛友俐認為,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是缺位的,政府應該發揮更強的勞動監管作用。 但從采訪看,也很難說地方政府無所作為,當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的時候,政府也感到委屈。 廣州市勞動保障局張杰明局長告訴《商務周刊》,廣州去年調整了最低工資,從510元人民幣調高到684元,目前為止是全國最低工資最高的地區。張杰明表示,最低工資提高當然會導致企業成本提高,更為重要的是一個企業甚至一個生產模式的產品和生命周期是否適合政府對當地的發展需求,這直接影響了政府對它的態度。 “廣州的經濟已經不是依靠那些對最低工資政策敏感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張杰明說,“現在這里的經濟不是靠洗發水和牙膏來支撐的,石化、鋼鐵、汽車、港口碼頭這些年發展迅猛。” 深圳龍安區龍華街道勞動管理辦公室的謝秉波主任也表示,勞動密集型行業已不再是當地經濟的支柱。1990年代初期,“三來一補”企業占到龍華經濟比重的90%,1996年以后,龍華引進了富士康等幾家高新技術企業,現在一個富士康就占到龍華地方經濟的大半。產業升級給當地帶來了明顯的收益,據謝秉波介紹,1990年代初期,龍華每年稅收才幾個億,到去年底已經達到20多個億。 相對于廣州、深圳,東莞的壓力要大很多。據廣東省人力資源協會甘文傳主任介紹,東莞市登記注冊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有13000多家,占當地企業總數的1/4。東莞市的外來工數量也是珠三角地區最多的,據勞動部門統計有200多萬,但甘文傳稱,據他們私下估計,實際人數應該在500萬以上,而東莞當地居住人口為150萬。 與珠三角其他地區一樣,東莞市政府也開始考慮產業升級的出路。甘文傳認為,東莞市目前的土地、生產生活成本、工資標準社保政策,已經到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為繼的階段。 地區的產業升級就意味著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拋棄。張杰明的說法代表著地方政府態度的轉變:“熬不住的是那些附加值低的,轉移能促進地方的產業升級,很正常,而且也是好事。”孫顯明很清楚的認識這一點——政府不會再扶持他們,也不再會有早期那些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了。 客戶能否考慮到工廠成本提升的壓力,給工廠一些生存的空間?孫顯明對此也不抱幻想,“毛織行業不是什么技術難度高的行業,你不做,東莞那么多家廠會做,東莞的企業做不了了,內地的甚至越南、菲律賓的廠會做。” 耐克的代加工廠豐泰企業證實,由于越南的工資水平更低,今年耐克運動鞋在越南的下單量將會加大。耐克計劃到明年年底,在越南每月生產鞋的數量達到302萬雙,而目前中國的生產規模大概為每月182萬雙,越南將成為耐克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 在國內,產業向低勞動成本地區的轉移也正在發生,有些耐克的合約工廠開始把自己的工廠從東莞和江蘇搬到江西,或者更加偏遠的大別山區。 和幾千家東莞的毛織廠一樣,孫顯明的工廠只做來料來樣加工,自己不做研發,除了生產線工人,只有行政、財務等管理人員,沒有技術和銷售部門,香港老板也沒有想過要建立這樣的部門。 孫顯明不想談企業未來的發展,雖然他不是沒有想過。“能怎么辦呢?只有想辦法多搶一些單子,把成本攤薄一點。”但是他也知道,其他廠也在這么苦苦維持,大家搶單的結果只能使利潤更低。 去別的熱土尋求更低廉的成本,也成為孫顯明所在企業的選擇。前年公司在江西贛州開了兩個分廠,相對于東莞來說,江西的工資水平更低一些,目前一個工人在東莞900元一個月,而在江西700元就夠了,稅收和地價也更優惠一些。但是孫顯明也表示擔心,內地的局限性比較大,從勞動力來說,不像廣東有那么多流動人口。招工可能會困難一些,只能從生手慢慢培養。他還擔心內地也會有企業越來越多那一天,今天在東莞發生的一切,明天還會在那里重演。他攤開手,反問道:“到時候,我們又能遷移到哪里呢?” 作家吳思在《潛規則》一書中曾闡述了一個“崇禎死彎”的概念:“我們可以想像一個U形山谷,從側面看,崇禎率領著官府的大隊人馬一路壓將下去,擠壓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各地的叛亂,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越往后越費勁,最后他撞到了谷底。這時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賦稅壓垮了更多的農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亂的規模和強度反而開始上升了,全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崇禎便走投無路了。而有了李自成之類的強大反對勢力,人們利害計算的結果頓時改變,崇禎死彎的谷底被進一步抬高。” 耐克等跨國公司手執合同向它的代工廠一路壓將下來,不斷以生產訂單轉移模式從“無差別充分供給”的代工廠身上榨出利潤,由于面臨大量的可替代者,工廠主只要還能通過壓低成本獲得利潤,他們都會選擇忍受。然后,代工廠以同樣模式,再不斷從“無差別充分供給”的工人身上榨出利潤,由于來自廣大農村的工人缺少談判能力,只要收入又高于在鄉務農,他們都會選擇忍受。這個時候,來自外界的批評和致力于保護工人福利的所謂社會責任準則,只是改變了坐在金字塔尖的品牌公司壓榨的方式方法,并進一步將責任和成本轉嫁給代工廠。雖然品牌公司的責任轉嫁和勞動法規或有或無的壓力,使工廠主的利潤谷底因此而抬高,但更為弱勢的工人身上表現出的驚人的壓縮彈性,仍使工廠主尚未接近最后的臨界點。自2004年以來,隨著中國政府致力于減輕農民負擔,遞減和取消農業稅,提高農業產品價格,在鄉務農收入的提高大幅度抬高了工人“谷底”——工人谷底臨界點的提高,對于夾在中間的工廠主可能是災難性的。 誰來終結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 耐克錯了嗎? “隨著東莞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來自上游的訂單是否會減少?當耐克們沒有了更多低廉勞動力地區選擇的時候,這些跨國集團還能生存下去嗎?”在東莞采訪時,許多合約工廠廠主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對于耐克來說,這些或許并不是一個值得疑惑的問題。因為40年來,耐克的全球經營模式,主線就是合約工廠的不斷遷徙。正是依靠這一點,耐克創造了令人炫目的業績神話,而且這種神話還將繼續在全球上演。畢竟在這個星球上,比東莞窮的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多很多。 耐克公司的巨大成功源于其創始人費爾·耐特(Phil Knight)在斯坦福商學院上學時逐漸形成的一種預見性策略,即在工資標準低的國家生產,把公司的錢都用到產品的營銷上。耐克公司的一位副總裁也曾說過:“我們對生產一竅不通,我們只是營銷人員和設計人員。” 這種模式也注定了公司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對低工資標準的刻意要求和地區選擇。1964年耐克公司成立,也就是從這一年起,耐克開始了它直到今天仍在繼續的全球生產訂單的轉移路線。 1964年成立初期,耐克是跟日本的承包商簽約生產運動鞋。但隨著日本當地的工資上漲,耐克把生產工序搬遷到韓國和中國臺灣,1982年,超過八成的耐克運動鞋在以上兩個地區生產。等到當地的工資也逐漸上漲,耐克開始瞄準東南亞國家。至1990年,大多數耐克的生產工序均搬到印度尼西亞、越南和中國內地。在東莞,像裕元和興昂這樣的大型代工企業,都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從臺灣轉移過來的。 一直低廉的勞動力和優惠政策保證了耐克的迅速膨脹,今天,這家總部位于美國俄勒岡州的企業,已經成為全球運動鞋的執牛耳者。 在早期,甚至就在幾年前,耐克很少考慮其全球合約工廠里工人的工資待遇和條件的改善。隨著全球反血汗工廠運動的開始,耐克成為攻擊和批評的目標。最初,當耐克公司碰到剝削勞工的指責時,它通常的反應只是憤怒與惶恐。公司的高級經理對一切指責均予以否認,并猛烈抨擊來自各方的批評意見。 但隨著外界對耐克經營模式的批評越來越多,耐克的創辦人兼CEO費爾·奈特在1998年5月一次講話中不得不承認:“耐克產品已經成為微薄工資、被迫超時工作、甚至任意虧待工人的同義詞。” “沒有一個CEO愿意把自己的公司與血汗工廠聯系在一起。”一位接近耐克的人士告訴記者,耐克的高姿態更多的是出于企業的經營戰略和公關策略考慮。“重要的不是自己有道德,而是讓別人認為自己有道德。” 對此判斷,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托馬斯·巴梅斯(Thomas Balmès)曾執導過一部名為《中國制造》的紀錄片,這部由英國廣播公司和芬蘭、法國的電視臺贊助拍攝的片子開頭,引用了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句話:“企業的惟一社會責任就是賺取利潤。” 他認為,對于全球市場引領他們去何方,它們不該有負疚感。 這一斷言引來的是主張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的批評,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耐克的全球經營模式帶來的必然是生產地的勞資矛盾緊張和沖突加劇,在合約工廠沒有集體談判能力與耐克討價還價的不對等形勢下,大部分利潤被跨國公司拿走,而成本壓力最終只能轉嫁到處于更沒有談判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的工人身上。 流傳業內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國家領導人曾見到一位耐克鞋的臺灣代理商,問他在中國的企業辦得怎么樣,該代理商說,耐克鞋的70%都是在中國生產的。領導人問,一雙鞋在美國能賣到多少價錢,代理商說大約是160美元一雙。領導人又問,那么我們中國能從每雙鞋中賺多少錢呢?代理商說,大約只有3—4美元吧。臺灣代理商的話讓這位向以鐵腕著稱的領導人氣得連飯都沒有吃。可能他并不知道的是,中國的工人為耐克每生產一雙鞋,拿到的卻只有0.5美元的勞動報酬——這一數字在2004年之前更低。 “在不平等貿易關系和合約壓力下,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個悖論,工廠在巨大的壓力下,對于來自跨國公司們的工時和責任的要求,只能采取欺騙和弱者最后承擔成本的辦法。”葛友俐曾多次參加耐克的社會責任調查活動,在采訪中她向記者強調,“跨國公司在把訂單發包給合約工廠的時候,同時也把自己應負的責任向下推卸了,這是不公平的。” “現實有非常讓人絕望的方方面面,但要改變目前商業邏輯和市場邏輯,還需要時間。” 葛友俐說。 勞動力還能低多久?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夏小林還注意到,在耐克的生產模式下,制造工廠和地方政府都面臨一個困境:工廠要隨時面對工人不堪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后的“用腳投票”,而地方政府也要面對工廠由于日益提升的各種成本壓力后的“用腳投票”,在這一點上,工人和工廠主的選擇權利是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在于,“雇主在用腳投票的同時,還可以用手投票,他們與政府有一定的議價能力,在加班時間、勞動保險等方面的違法違規得到政府一定的默許”。 這對于像東莞這樣靠訂單產業發展起來的新興制造城市來說,資本轉移這種風險正在成為現實。而更現實的危險在于,“招商引資”至今仍是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產業升級雖然也時常出現在地方政府的文件里和會議發言,但對傳統模式的路徑依賴,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延續舊有的思路。“這只能會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處于最低端。”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常凱教授說。 在今年年初的首屆青年華商峰會上,有高層人士仍在特別強調中國具有質優價廉的勞動力優勢:“在美國每小時工資約是16美元,在墨西哥約是4美元,在中國約是0.5美元。” 表面上看,勞動力價格超低對吸引外國投資者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實際上這樣的吸引只能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勞動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和再教育的機會,生活保障度低,技術人力缺乏,進而導致產品的技術落后,國際競爭力滑坡,勞動力價格的差異最終會與技術等級的差異接近,并成為絕對落后的勞動力價格的真實反映。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中國的低工資策略只能不斷把淘汰工廠吸引進來。使“垃圾產業”在中國逐步形成規模性集中,導致產業工人生活的長期貧困化。 中國的貿易已經因此受到負面的影響。與發達國家貿易方式偏重一般貿易不同,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2004年1至10月,中國進出口加工貿易累計4371.5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47%。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條中處于利潤率最低的低端位置。加工貿易有零關稅的優勢,但由于缺乏品牌價值和創新內涵,加工貿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貿易占據中國貿易方式半壁江山的境況影響了整體利潤水平,降低了中國貿易競爭力。 去年發生在珠三角地區的“民工荒”,也為中國仰仗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的增長道路敲響警鐘,去年以來,國內的路風等學者一直在強調反思FDI和“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片面強調比較優勢理論,在國際分工中長期偏重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依舊能獲得些許利益,但在長期中卻會面臨貿易結構不穩定,總是落后于人的“比較優勢陷阱”。 邁克·波特在《國家競爭戰略》一書中曾指出:“競爭力與廉價勞動力之間并無必然聯系。產業競爭中,生產要素非但不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其價值也在快速消退中。以生產成本或政府補貼作為比較優勢的弱點在于,更低成本的生產環境會不斷出現。” 今天以廉價勞動力被看好的地區,明天可能就會被新的廉價勞動力地區取代。在東莞和其他沿海發達地區,波特所說的現象正在發生。而更令人憂慮的還不在此,而是這些地區的產業升級并不理想,甚至還遠未開始。 “比較優勢”的神話必須打破。在中國這個巨大而復雜的新興市場,假如勞動力低成本的經濟憂患繼續被扭曲性的解釋為經濟優勢的話,那么,不合理和悖論仍將繼續下去。 | ||||||||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產經觀察 > 正文 |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票:今日黑馬 |
| 怎樣迅速挖掘網絡財富 |
| 短線最大黑馬股票預報 |
| 海順咨詢 安全獲利 |
| 風情小布藝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時裝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創業賺大錢? |
| 品牌服裝 一折供貨 |
| 火爆粥鋪 四季穩賺 |
| 開冰淇淋店賺得瘋狂 |
| 美味--抵擋不住的誘惑 |
| 新行業 新技術 狂賺! |
| 投資3萬年利高的驚人 |
| 05年開什么店好賺錢? |
| 05年投資賺錢好項目!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