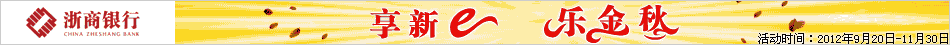秦暉:從感恩型福利觀走向問責型福利觀
現在講的福利國家都是民主國家,搞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搞了老百姓不感謝,不搞老百姓要問責,這和統治者喜歡不喜歡搞福利無關,不喜歡也得干。
秦暉
最近,歐洲福利國家鬧危機。希臘福利開支太大,老百姓也沒感謝政府,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政府借債太多,支撐不了,老百姓就抗議。但是,很多人由此說“可見福利國家搞不得,搞福利就造成大問題”,卻值得辨析。這事到底怎么造成的?
福利國家vs“強權國家”
在現在的西方語境中,“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是對立兩極: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但最早的“福利國家”,反義詞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強權國家。
1920年代,福利國家作為德語名詞出現,Wohlfahrstaat,是貶義詞。當時德國極右翼分子,后來成為納粹基礎的一些人,用這個詞來罵魏瑪共和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你們只懂討好老百姓,搞虛偽的婦人之仁。不懂讓老百姓為偉大的德國而奉獻,你們搞的是福利國家,我們要的是偉大的德國。這些批評福利國家的人,并不主張自由放任,而是搞納粹那一套。
1930年代,“福利國家”概念傳到英語國家,成了褒義詞。1930—1937年,在政治學、經濟學領域都有人用這個概念形容民主國家,“福利國家”的反面是什么?這時也沒說是“自由放任”,而是“強權國家”。
這概念能在二戰中廣泛普及,1940年代的英國宗教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年輕時是工黨成員,信奉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搞社會福利。二戰期間,他寫了《教徒與公民》一書,影響很大。其中提到兩個概念:Welfare state與Warfare state,這在英語中是一個語言游戲,Welfare與Warfare發音相近,但按他的說法,意思完全相反。Welfare state是福利國家,他解釋是“民主國家要為老百姓提供福利”。Warfare state是戰爭的意思,指的是軍國主義,1940年代正是二戰時期,指的是意大利、德國、納粹法西斯專制獨裁的國家。他說福利國家和軍國主義國家是對立的,沒提到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的對立。
走向“問責型福利觀”
盡管這位大主教說Welfare state是搞福利的,Warfare state是搞軍國主義,讓老百姓當戰爭炮灰的,可當時的納粹和意大利都有相當高的社會福利水平,也不是光打仗。同時,當時英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在二戰特殊時代也在全力以赴地打仗。這兩者的區別到底在哪里?坦普爾沒說得很清楚。在我看,有三個區別非常明顯。
第一,現在講的福利國家都是民主國家,搞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搞了老百姓不感謝,不搞老百姓要問責,這和統治者喜歡不喜歡搞福利無關,不喜歡也得干。在憲政制度下,福利是一種責任。瑞典主要是社會民主黨執政,但政黨輪替,也有很多次是自由黨或右翼政黨執政,它們不喜歡福利國家,但也得做,因為這是由老百姓決定的。
斯大林搞福利是皇恩浩蕩,搞一點老百姓就高呼萬歲,不搞也不能要求他。福利不是責任,而是恩情。這種觀念,當然主要是由專制主義造成的,但有時一些“卸責右派”也幫了忙,他們再三講國家不必盡這種責任,老百姓應該“不找市長找市場”,什么教育呀醫療呀都不能麻煩政府。既然他沒這個責任,他還給了你這不就是額外恩賜了嗎?所以你要感恩。
第二,公共福利是一種二次分配手段,在民主國家由多數決定。一般都是正向分配,指向平等。區別只在于,一些國家比較傾向于(注意是選民傾向于,并非統治者喜歡)自由放任,實行低福利制度。另一些國家的選民選擇了高福利制度,平等的功能就很強。所謂低福利,一是覆蓋率低,只照顧那些最窮的。比如美國有福利房,但通常只給失業者,一般人沒申請資格。而高福利國家的福利覆蓋率很高,義務教育、全民醫保全民共享,在有些國家任何人都可申請住房福利,但在有些國家條件很苛刻。然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只給官員分房,窮人反倒沒份,這不可想象。二是同樣受照顧的窮人,低福利國家照顧得少一點,高福利國家照顧得多一點。北歐高福利國家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數往往會下降一半。美國這樣的低福利國家下降得很少。但沒有一個國家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數是上升的。
可另外一些國家福利和特權掛鉤,具有非常強烈的等級性。在這些國家,福利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待遇。包括用車、住房、醫療。這種福利的最大特點是,強勢者初始分配占了一次便宜,二次分配再占一次便宜,弱勢者初始分配受損失,二次分配再受損失。這是福利反向調節,這種國家面臨的不是高福利與低福利的問題,而是“負福利”的問題。
假如福利有平等的功能,在最差的情況下平等功能等于0,是“零福利”,即自由放任。但負福利國家是擴大不平等,豈止零福利而已。自古以來,我國的強勢者就主要不是靠初始分配,而是靠特權“待遇”來顯示地位的。歷史上,誰知道皇帝領多少工資?皇帝往往根本無所謂工資,在“初始分配”上他與乞丐幾乎是“平等”的。但乞丐餓死沒人管,而皇上“從搖籃到墳墓”都狂吃國家的,還包三宮六院,享受“供給制”下的奢侈生活。皇上還發福利,當然是論功行賞,先發給一定級別的權貴。
奧巴馬上臺后就要搞醫改,很多人批評美國醫療,這么富的國家還是有人看不起病。但在美國誰看不起病?是窮人嗎?不是。美國是低福利國家,覆蓋面很窄,按現在看到的數字(各州情況不一樣),美國聯邦財政提供的福利性醫療保險覆蓋面只有18%,有些州還有州提供的。這18%主要包括兩個項目:一個醫療保險,這個項目標準是對65歲以上的老人全部負責;另外一個是醫療補貼,專門針對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其他人國家基本不管。
歐洲國家不一樣。比如英國不僅國民全覆蓋,學生在英國待半年以上就可享有。而美國沒有,所以多數人只能買商業性醫療保險,但比較貴。如果有些人仗著身體好不買醫療保險,一旦有病去看醫生,的確是奇貴,以致有人看不起病。但這些人不是美國最弱勢的群體,而是中下階層。這些人沒窮到可以享受國家醫療福利的地步,又不愿買商業保險。
奧巴馬推行醫改,要贏得多數人支持不是很容易。富人不愿,因為從他們口袋里掏錢,富人也沒有看不起病的問題。美國窮人也不愿意,因為那18%的人已經有了保障,他們也不需要什么醫改。只有中下階層是奧巴馬醫改的支持者。
第三,既然民主國家的福利是國民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務,這種福利就顯然是公民的權利、政府的責任,而不能反過來變成是政府的權力、公民的責任。似乎類似的事,如果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那就是福利,假如是政府強加于百姓,那就不是了——當然,不是說政府不能要求于百姓,只是這種事不能叫福利而已。
例如同樣是老百姓干活兒,如果是老百姓要求政府保障就業、搞培訓、增加崗位等等,當然帶有福利含義。但官家抓老百姓去干活,就像秦始皇把孟姜女老公抓去修長城,那就不是福利了。窮人要求政府以廉租房與福利公屋來改造“貧民窟”,那是福利,而政府用鐵腕“城管”拆掉窮人的“違章建筑”并趕走窮人來“消滅貧民窟”就不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是福利,強制性抓捕流浪漢的“收容遣送法”就不是。國家承擔責任提供養老保險是福利,國家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令其自耕終老而不許留在城里“給政府添麻煩”就不是。
以上三條歸根結底,福利國家首先必須是民主國家。而反過來講,爭取福利問責就是通向憲政民主的一條重要道路。改變我們的福利觀念,從“感恩型福利觀”走向“問責型福利觀”,這對我們走向憲政民主非常重要。
買多少菜給多少錢
有人把福利國家和專制主義混為一談,或者說搞福利會導致專制,或者說不專制就會失去福利。兩者似乎一“右”一“左”,其實作用卻是一樣的。
而我們知道所謂憲政機制,實際上就是通過限權問責而實現權責對應的機制。
在權大責小的舊體制下,“為福利而問責”與“為自由而限權”實際上是從兩個方面在向憲政走近,其意義決不下于擴大直接選舉等等。在權力不受制約、責任不可追問的情況下,走向憲政得通過制度上的改變,但首先要有觀念上的改變,要在每件事情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
憲政制度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于權力和責任的契約,在憲政條件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就像我和保姆之間的契約,我希望他買多少菜就給他多少錢。
當然,我家兩口子對此會有分歧:太太要求保姆多買點菜,因此要多交給他錢。而先生不愿讓他處置這么多錢,也就不能要求他買太多的菜。那么保姆怎么辦?等你們吵出個結果來,給多少錢我買多少菜就是了。
國家也是一樣,有人愿要大政府,要求它多服務,就愿意多授它一點權力;有些人愿意要更多自由,不愿給它太大權力,也不能要它承擔太多責任。高稅收高福利或低稅收低福利。到底怎么辦?競選出個結果,誰贏就照誰的辦就是。這是一種制度安排。與之相對的非憲政制度,或者說是專制制度則相反,權力不受限,統治者想橫征暴斂就可橫征暴斂,責任不可問,皇上給你點福利你就得感謝,不給你不能問他要。
問題在于怎么才能走出這種狀態呢?
很多人說,憲政制度是一種財政體制,財政公開、預算透明,這是漸進民主。可政府憑什么愿意搞預算公開?動力從何而來?從憲政制度的歷史看,從最早英國、法國出現憲政一直到后來的波蘭、匈牙利率先走出鐵幕,有個共同點:這些國家都是被赤字逼出憲政的。政府在什么條件下愿意向公眾晾賬本?如果想收多少錢就收多少,想不給你就不給你,錢都留下我自己花,他愿意晾賬本嗎?不可能。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他會主動晾:他向你收錢,你大聲埋怨,使他收不到多少錢,你又逼他花很多錢,必須從搖籃到墳墓都負責。這樣兩頭逼,總有一天他受不了就會晾出賬本。
有人說高福利國家不好,老百姓對政府的要求太高等等。他們的確是有這個問題。但是限制責任的前提是限制權力,權力無限責任就該無限。一個經濟自由主義者,在憲政體制下,不應提出從搖籃到墳墓都要國家負責,但在非憲政國家就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同樣,一個社會主義者在憲政國家可以為了搞福利支持高稅收,但在非憲政國家他能支持皇上橫征暴斂嗎?笑話!你去看看19世紀歐洲非憲政國家與向憲政過渡中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抗議高稅收比自由主義還積極!自由主義者最核心的觀念是權責對應:不要求你負那么大的責任,前提是不希望你有那么大的權力。社會主義者對這個核心觀念并無不同,只是推出的訴求相反:給你多授點權,前提是我要更嚴厲地向你問責。
很多國家在走向民主化過程中,啟蒙的作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英國、法國最早出現憲政,不是因為啟蒙思想家寫了很多文章,而是皇上需要很多錢,財政虧空一塌糊涂,實在沒辦法讓老百姓納稅,不得不開國會跟納稅人商量,在時而暴烈時而溫和的討價還價中,憲政就出來了。東歐也一樣,波蘭、匈牙利率先走向憲政,共同的特點是這兩國的赤字在東歐最高,非常重要的杠桿是老百姓對政府實行福利問責,政府必須提供這、提供那,提供了不感謝,不提供就抗議。
福利要求的力量
現在有人常把憲政民主和自由主義相聯系,如果這里說的是政治自由主義,那么問題不大,因為所謂政治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主張憲政民主,民主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也屬于政治自由主義者。但是,“經濟自由主義”也就是市場自由競爭、國家不干預的思想,卻并非憲政民主體制在經濟上的等值對應物。盡管這種思想因其在邏輯上的限權取向,應該屬于推動憲政的一翼,但卻因缺乏問責取向而需要另一翼的互補,這另一翼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或稱社會民主主義。
事實上,幾乎所有典型的憲政國家都是這兩翼共同的舞臺,當然也是兩者博弈和互滲的場所,卻沒有一個憲政國家是只有“自由放任”論者唱獨角戲的。已有的憲政平臺是如此,這一平臺的建立同樣是兩者共同之功。過去的論者探討東歐轉軌的成就,政治上多強調政治自由主義對民主化的作用,經濟上多強調“經濟自由主義”對市場化的作用。而對于社會民主主義只是肯定其政治自由主義傾向對憲政的作用,對其經濟上的福利問責主張推動憲政進程的重要性,則很少提及。這是很大的缺陷。
甚至可以說,至少在東歐民主化的幾個先行國家(現已加入歐盟的波、捷、匈和前東德),福利問責的社會民主思想對于憲政民主的推動力甚至大于經濟自由主義。歐洲國家在二戰前有過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時代,比如捷克、東德、波蘭這樣的國家都有過社會黨執政,那個時候老百姓就有了一種社會主義觀念:政府是為我們服務的,提供福利理所當然,給了不用謝,不給可以要。
現在很多人講福利國家是左派思想,不應該有,老百姓就該不找市長找市場,就應自生自滅。如果這樣,東歐國家不可能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就是問責問出來的。
在東歐,民眾的限權問責在經濟上表現為,向我橫征暴斂我抗議,向你要公共服務理直氣壯,而且公共服務越要越厲害。那時的波蘭人既沒有主張私有化,也沒有主張市場經濟,而是不斷向政府進行福利問責,市場上沒肉,就抗議為什么沒有了,肉的價格高了抗議價格為什么高了。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后,波蘭民眾一直對政府進行福利問責。政府不斷講,老百姓應該知道政府的苦衷,應該懂得不找市長找市場。
不斷問責造成一個現象:赤字越來越高。高到波蘭不可能有余錢供養貪官污吏,因此那些人就覺得當官太沒意思,整天被老百姓追在后面找麻煩,自己撈不到任何好處。
波蘭從1980年雅羅謝維奇總理在問責聲中辭職后,就沒有一個穩定的內閣,9年間換了7個總理,從雅羅謝維奇、巴比烏赫、平科夫斯基、雅魯澤爾斯基、梅斯內爾、拉科夫斯基到基什查克。人人無心戀棧,“圓桌會議”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談判是被逼出來的,這時財政公開、預算透明不要求也有了,因為統治者比你更著急財政公開,急不可待地給你晾賬本:“只有這么一點錢,你的要求滿足不了,要么你給我多一點,要么不要向我要那么多。”那時候不但有了財政公開、預算透明,而且我敢說那時的財政公開、預算透明是真的。
漫天要價,就地還錢
話說回來,如果老百姓問責慣了,民主化以后怎么辦?民主化以后老百姓仍然要求福利無窮大,就變成希臘那樣,就會出現財政不可持續的福利病。
但這些國家都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憲政前老百姓的福利訴求沒有邊際,可以從搖籃問責到墳墓。一旦實行了憲政,老百姓就變得很自覺,開圓桌會議,政府跟你討論,你給多少權力替你承擔多少責任,這時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有人說“我愿當奴才,只要有低價的肉吃”,有人說“我上臺物價肯定要漲,肯定不能保你那么多,但條件是可以給你自由。”在多種權力、責任的契約組合中,老百姓既然作出了某種選擇,當然就會遵守契約。
于是,正如當年英法國王征稅,國民以“無代表不納稅”相抗拒,但憲政后民選國會征稅更多,國民卻樂于繳納一樣,東歐的憲政也使國民痛快地撤銷了福利上的漫天要價。波蘭圓桌會議后,國民的“過度福利”病一下就消除了,以前肉價上漲30%就上街,1990年后上漲500%也是理所當然,原因就是有了一個權責對應的契約,政府和百姓只能簽訂一個權責對應的契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做不到的,但相反的現象經常發生,即馬兒既要吃山珍海味但又不肯跑。這種情況怎么辦?兩種訴求都可以提,而且應該提:第一抗議你吃那么多山珍海味,第二逼得你不能不跑。而兩種訴求的“契約前”形式,恰恰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促使雙方走向契約的談判過程,通常都會是一個“漫天要價施加壓力、就地還錢達成妥協”的過程。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實際上做不到,可以做到的是迫使這匹馬要跟你談它吃多少草,就跑多少路。但在達成妥協之前當然是可以漫天要價的。這與契約達成后的過分需索是兩回事。
今天的希臘人糟就糟在,他們在憲政完成38年后真的追求起“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個不可能的結果,而昨天的波蘭人高就高在憲政之前他們進行了“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漫天要價。沒有一個合理的要價策略,不提出這個要價,就沒有還價的空間。這完全是漸進的、和平的改革,和任何暴力沒有關系。如果最后就吃多少草跑多少路的問題達成契約,那就是憲政成型的一天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