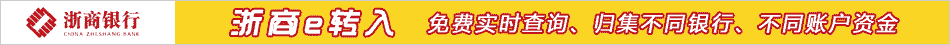評(píng)論:三一的“委屈”與中聯(lián)的“國(guó)企”身份
中新網(wǎng)12月24日電雖然當(dāng)事各方的聲音逐漸轉(zhuǎn)弱,但鬧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三一重工[微博]出走長(zhǎng)沙”一事尚未平息。縱觀這段時(shí)間來(lái)“離家出走”的三一重工[微博]對(duì)中聯(lián)重科的指責(zé),給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無(wú)比哀怨”,像個(gè)受了家庭怨氣“養(yǎng)子”一樣,對(duì)著左右隔壁鄰居抱怨家長(zhǎng)處事不公、放縱大哥欺負(fù)他這個(gè)老二。中聯(lián)重科呢?確實(shí)也像個(gè)老大,百口莫辯,說(shuō)什么都不好。
如果“圍觀群眾”要看大家族的家庭鬧劇,前有曹雪芹先生《紅樓夢(mèng)》,后有巴金先生的《家》《春》《秋》三部曲,大可無(wú)視三一重工喋喋不休地控訴中聯(lián)重科。可惜這不是一部家庭鬧劇,而是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下兩家公司間的競(jìng)爭(zhēng)。當(dāng)事方將一個(gè)完全可以依托法律和市場(chǎng)規(guī)則而行的紛爭(zhēng),粗暴地拖進(jìn)借“傾訴”而博取輿論同情的深淵,實(shí)在值得各方深思。
在引發(fā)輿論爆點(diǎn)的新聞報(bào)道《三一恨別長(zhǎng)沙 梁穩(wěn)根的內(nèi)心獨(dú)白》中,當(dāng)事人含蓄地說(shuō)了許多疑團(tuán),比如,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不僅限制三一重工獲得公平競(jìng)爭(zhēng)的權(quán)利,甚至讓企業(yè)負(fù)責(zé)人連正常日子都沒(méi)法過(guò)下去了。給人的感覺(jué)是,中聯(lián)重科為了自己利益,控制了政府各個(gè)職權(quán)部門,聯(lián)合起來(lái)打擊、排擠三一。
從正常邏輯來(lái)講,中聯(lián)重科只是一個(gè)企業(yè),憑什么左右政府部門的決策?更別說(shuō)控制政府各實(shí)權(quán)部門了。顯然,三一重工在“獨(dú)白”中含蓄點(diǎn)出來(lái)的眾多疑團(tuán),并不像說(shuō)起來(lái)那么簡(jiǎn)單的“控訴中聯(lián)重科”。正如本文開(kāi)頭所言,三一重工與中聯(lián)重科之間的恩怨,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企業(yè)間的自由競(jìng)爭(zhēng),而非大家族里上演的家庭鬧劇,自然不存在老大給老娘吹風(fēng)打壓老二,以圖多分點(diǎn)家產(chǎn)、多要點(diǎn)月錢的可能。
那么,為什么三一重工硬是要曲曲折折、含含蓄蓄地將這個(gè)問(wèn)題傾訴成“中聯(lián)重科成了影子政府”、“中聯(lián)重科操控政府公權(quán)打壓三一重工”呢?而又是因?yàn)槭裁矗屳浾摵蜕鐣?huì)各界一聽(tīng)見(jiàn)三一這種哀怨的傾訴,立刻就深有感觸地給三一投以同情的目光呢?
答案其實(shí)很簡(jiǎn)單:政府的越界管理與中聯(lián)的國(guó)企身份。
大家也正是深刻領(lǐng)會(huì)了這兩點(diǎn),才能輕而易舉就理解其中的問(wèn)題所在。說(shuō)白了,無(wú)論是政府的補(bǔ)貼多給中聯(lián)少給三一,還是政策上偏袒中聯(lián)重科打壓三一重工,皆因政府這個(gè)“當(dāng)家的老娘”,總覺(jué)得國(guó)企中聯(lián)重科是親生的,而民企三一重工是領(lǐng)養(yǎng)的,所以處處偏袒中聯(lián)這個(gè)“親生兒子”。
這種思維模式一旦定型、周圍隔壁鄰居都心知肚明了之后,就算“當(dāng)家的老娘”沒(méi)有偏袒親生兒子,只要那個(gè)領(lǐng)養(yǎng)的兒子哭幾下、鬧幾下、控訴幾下,大家不用思考也自然而然就領(lǐng)會(huì)了。這時(shí)候,偏袒不偏袒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親生的”和“領(lǐng)養(yǎng)的”這兩種身份:如果你是親生的兒子,縱然老娘沒(méi)多給你飯吃,領(lǐng)養(yǎng)的孩子哭鬧起來(lái),周圍鄰居也會(huì)拿白眼瞧你,背后還會(huì)謠諑你欺負(fù)了你弟弟。所以說(shuō),“后媽”不好當(dāng),“后媽”的親生兒子日子也不好過(guò)。
一場(chǎng)本該依據(jù)法律、遵守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則的企業(yè)競(jìng)爭(zhēng),就這么變成了中國(guó)歷史上大家族里屢見(jiàn)不鮮的“家庭鬧劇”!甚至是結(jié)局,也幾乎一模一樣:三一重工的突然出走和出走后含蓄的控訴,以及輿論和社會(huì)各界對(duì)三一重工的同情、對(duì)中聯(lián)重科的指責(zé),多像巴金《家》里的情節(jié)啊,一瞬間,三一重工幾乎就成了那個(gè)離家出走的“覺(jué)慧”!
可惜的是,“覺(jué)慧”出走之后,歸結(jié)起來(lái)的問(wèn)題,并不在于大哥覺(jué)新、二哥覺(jué)民以及家族內(nèi)其他人對(duì)他的壓迫,而是將控訴矛頭直指整個(gè)大家族制度。三一重工卻沒(méi)有這種膽量,而是很巧妙、很含蓄地將責(zé)任歸結(jié)到了中聯(lián)重科身上,由此一來(lái),當(dāng)前輿論、各界的討論也是如此。
這是刻意而為之嗎?如果是,那就更該令業(yè)界悲哀了。
作為一家民營(yíng)企業(yè),三一重工不想與政府正面起沖突,固然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從側(cè)面反映出當(dāng)前很多地方的市場(chǎng)環(huán)境惡劣到了什么地步:政府就像大家庭的祖母、大家族的族長(zhǎng),對(duì)區(qū)域里的企業(yè)所采用的管理方法,就像是族長(zhǎng)以一大堆家規(guī)管制大家族內(nèi)的青年后輩一樣,稍有問(wèn)題,不是以市場(chǎng)規(guī)則、法律原則來(lái)解決,而是在法理之外,借公權(quán)維系一條特殊通道,不管企業(yè)愿不愿意,都得服從這條家規(guī),還不能有怨言,更不能外傳,因?yàn)椤凹页蟛荒芡鈸P(yáng)”也是其中一條重要的家規(guī)。
這甚至超過(guò)了之前學(xué)界探討的“政府成了保姆”的概念,在這里,政府不僅間接插手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事務(wù),還以各種行政方式直接參與到企業(yè)間的競(jìng)爭(zhēng)、經(jīng)營(yíng)中去,尤其是政府的干預(yù)已經(jīng)超出了法律的底線,其結(jié)果就是讓轄區(qū)內(nèi)的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者手足無(wú)措、無(wú)所適從,不敢多言,更不敢怨言,只能一走了之!
正如之前張瑞敏的名言,在中國(guó)轉(zhuǎn)型期經(jīng)營(yíng)企業(yè)需要“三只眼”,一只眼看外部市場(chǎng),二只眼看內(nèi)部經(jīng)營(yíng),第三只眼看政府。由于政府左右著企業(yè)的生死,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者每天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眼巴巴地盯著政府,有問(wèn)題了,不找法律、不找市場(chǎng),而是找市長(zhǎng)。由此,看政府、看市長(zhǎng)臉色行事也就成了企業(yè)家必須承受的壓力。
這才是三一重工曲折申訴的東西,也是中聯(lián)重科默默承受的東西!
問(wèn)題是,就算是張瑞敏自己,也在他的“三只眼”理論之外加了兩句話,一句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只需要一只眼盯著政府就行”,另一句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需要兩只眼,一只眼睛盯著外部市場(chǎng),一只眼睛盯著內(nèi)部經(jīng)營(yíng)”。
也就是說(shuō),只有在“中國(guó)轉(zhuǎn)型期”,企業(yè)才需要“三只眼”。然而,從改革開(kāi)放、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三十多年了,剛剛召開(kāi)的黨中央十八大也提出要“加快完善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這種背景下,一向號(hào)稱中部“經(jīng)濟(jì)重鎮(zhèn)”的長(zhǎng)沙還在上演這出“三只眼”的鬧劇,甚至愈演愈烈,不得不讓人驚呼:“轉(zhuǎn)型期”何日才是個(gè)頭?政府何日才能真正擺正自己的角色?何日才能讓真正做到讓市長(zhǎng)的歸市長(zhǎng)、市場(chǎng)的歸市場(chǎng)?(張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