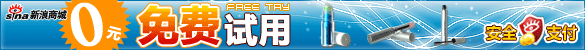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大興安嶺的艱難時光(2)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7日 11:48 經(jīng)濟觀察報
在搶運的三年間,該地區(qū)每年采伐的木材總量達到800多萬立方米,相當(dāng)于日常年份的兩倍多。因為供應(yīng)量急劇放大,此后,全國木材價格一路走低。 因為是搶運,承包者們希望爭取好資源,這給當(dāng)?shù)氐牟糠至謽I(yè)干部提供了權(quán)力尋租的空間;因為木材的積壓,放倒的木材不能及時變現(xiàn),這反過來讓林場給職工發(fā)不出工資。“林子砍的越來越多,我們的日子卻越來越壞。”前哨林場的一位職工說,“一場大火把當(dāng)官的燒發(fā)了,卻把職工燒慘了。” 更糟的情況接踵而至。在1990年以后的7年間,因為供過于求,木材市場逐年滑坡,木材價格大幅下降,林區(qū)工人的欠薪情況日趨嚴重;與此同時,大興安嶺好的林木資源越來越少,有些林木即使采下來,也賣不上價。 “天保”十年 1997年,大興安嶺的林木可采蓄積量由開發(fā)時的5.7億立方米下降到1.7億立方米;林業(yè)集團虧損1.2億元,欠工人工資4億元,外欠債務(wù)20多億元。大興安嶺風(fēng)光不再,陷入了資源危機和企業(yè)危困的“雙危”境地。 在林木資源漸近枯竭的情況下,習(xí)慣于砍樹吃飯的林區(qū)人并沒有找到其他出路。大興安嶺沒有大工業(yè),也沒有大企業(yè),即便是一個林場有膠合板廠、筷子廠或者家具廠,也是小打小鬧,靠林吃飯。在市場經(jīng)濟的沖擊下,這些一直附著在大國企身上的集體企業(yè),此時早已瀕臨破產(chǎn);在“雙危”的夾擊下,林區(qū)的大批職工開始下崗。 “當(dāng)時,54萬大興安嶺人面臨如何活下去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人們首先想到的還是砍樹。”左方副主任回憶說,“林區(qū)資源的保護變得更加艱難。” 1998年,按照國家林業(yè)局的部署,大興安嶺開始試點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兩年以后,覆蓋全國主要林區(qū)的天保工程(2000—2010)正式啟動。從2000年開始,國家財政每年撥付給大興安嶺地區(qū)的天保工程資金有5億—7億元,除了支付林區(qū)7萬名在職職工的工資外,這些資金還包括林區(qū)在管護、防火、建設(shè)等方面所需費用。 天保工程資金的另一個重要用途,就是彌補歷史欠賬。林區(qū)多年來拖欠的工資逐步清償,下崗職工的安置問題也借此得以解決。林區(qū)多年來在城市建設(shè)和社會事業(yè)上形成的歷史欠賬,也得到部分補充;這其中,加格達奇到漠河的高標(biāo)準(zhǔn)公路,加格達奇的城市建設(shè),就被當(dāng)?shù)馗刹恳暈樘毂9こ藤Y金投入的典范。 從90年代初開始,就有大批的大興安嶺人離開林區(qū),到外邊自謀生路。“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到處都可以看到大興安嶺人。”離休干部張福江說,“尤其是海邊城市,是大興安嶺人的最愛。” 1993至1997年,是大興安嶺最為艱難的階段,第二次居民外遷潮隨之到來。此后,因為天保資金的投入,大興安嶺的外遷人數(shù)趨于平穩(wěn)。 大興安嶺到底外遷了多少人,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具體的數(shù)據(jù)。“反正這些年,考上學(xué)的,有能力的,有親屬的,有關(guān)系的,有錢的,都走了。”在林區(qū)的各個場站,記者都能看到廢棄不用的職工住房,有些密林深處的場站,成排的住房被遺棄。在地區(qū)首府加格達奇鎮(zhèn),每平方米新蓋樓房的價格不到1200元。因為遠離內(nèi)陸和氣候嚴寒,樓房造價高,以這個價格出售新樓盤,開發(fā)商根本賺不到錢。 大興安嶺或許是中國氣候最為惡劣的地方之一,這里屬高寒區(qū)域,冬天長達七八個月,夏天4個月,冬夏溫差可達80度,幾乎沒有春天和秋天。因為只有90天的生長期,加之土壤瘠薄,這里能夠生長的只有土豆和黃豆兩種農(nóng)作物。天氣冷、條件差、產(chǎn)業(yè)單一,成了那些非林人群離開家園的主要原因。 也有無法離開的,河?xùn)|林場63歲的王在坤老人就是一例。1990年,林場完成了搶運“火燒木”的會戰(zhàn),此后,這個被大火重創(chuàng)的林場將工作的重心轉(zhuǎn)向了造林。然而造林并不能養(yǎng)活林場職工,此后幾年,生活艱難的河?xùn)|林場把目光投向了150公里外的富克山。 2002年,在自己原有作業(yè)區(qū)多年無所作為的河?xùn)|林場開始整體搬遷到漠河鎮(zhèn),但退休在家的王在坤老人卻沒跟隨林場下山。在河?xùn)|林場300多戶住房的廢墟中間,王在坤老人和其他兩戶人家選擇了堅守。“如果也搬到鎮(zhèn)上,房子要自己買,我買不起。再說,我也習(xí)慣了這里的生活,不想改變。” 王在坤有三個孩子,現(xiàn)在都在外地。林場搬遷后,這里就沒了電,沒了自來水,沒了班車。除了收音機,家里再沒有其他電器,老人靠著每月900多元的退休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天保工程實施后,大興安嶺調(diào)低了木材產(chǎn)量。2002年,大興安嶺制定了接續(xù)產(chǎn)業(yè)戰(zhàn)略,提出了在保證生態(tài)效益的前提下發(fā)展地方特色經(jīng)濟。除了發(fā)展林木產(chǎn)品的精深加工、林下資源開發(fā)兩大產(chǎn)業(yè),林區(qū)還先后介入了生物制藥、生態(tài)旅游和特種養(yǎng)殖業(yè)。 2006年,大興安嶺在本地區(qū)的“十一五”規(guī)劃中,提出了發(fā)展六大接續(xù)產(chǎn)業(yè),除了上述五大,礦業(yè)開發(fā)被寄予重望。大興安嶺擁有煤、鐵、鉛、鋅、銅等多種礦產(chǎn)資源,左方副主任認為,因為該地區(qū)資源豐富,加之儲量潛力巨大,所以礦產(chǎn)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或許會成為大興安嶺下一階段經(jīng)濟增長的爆發(fā)點。 三十年的角落時光 2006年,與大興安嶺一水相連的小興安嶺開始試點國有林權(quán)改革。這一年的4月29日,34歲的伊春市烏馬河林業(yè)局職工蔣永彬,在一次性繳清62901元后,將9.3公頃國有森林正式劃到了自己的名下。他的這次競買行為,被伊春林管局稱為“林改第一槌”。 2007年10月,當(dāng)蔣永彬在自家的林地中計算再過一二十年就將獲得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投資收益的時候,大興安嶺圖強林業(yè)局中學(xué)的王老師卻在為自己的工資終于能與地方同類人員“平起平坐”而高興。 “我們這些企辦中小學(xué)教師,多少年來一直執(zhí)行林業(yè)企業(yè)職工工資標(biāo)準(zhǔn),而不是黑龍江省的教師工資標(biāo)準(zhǔn)。”王老師說,“現(xiàn)在,總算實現(xiàn)了同工同酬。” 在大興安嶺,任何一項改革似乎都比外地來得慢:公務(wù)員一直拿著企業(yè)的工資,高寒地區(qū)享受不到高寒補貼。“我們這里就是被人遺忘的角落,”漠河縣委宣傳部的一位官員抱怨說,“30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計劃經(jīng)濟的年代。” 1980年,大興安嶺地區(qū)“革命委員會”改為大興安嶺行政公署,成為黑龍江省政府的派出機構(gòu);兩年后,大興安嶺林管局企業(yè)管理體制(計劃、財務(wù))單獨運作,仍直屬林業(yè)部,與行政公署合署辦公。此后,中國開始嘗試首輪國企改革。 80年代后期,大興安嶺林管局也實施過放權(quán)讓利等改革措施,但隨著1987年大火過后的會戰(zhàn),改革停滯。 1991年,國務(wù)院確定大興安嶺林管局為全國首批55家企業(yè)集團之一。大興安嶺隨之啟動了轉(zhuǎn)換企業(yè)經(jīng)營機制的改革。1994年,林管局啟動了建立現(xiàn)代勞動、用工、分配等制度的企業(yè)改革,并開始“推行全員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工資可高可低”。與此同時,他們嘗試將政企分開。 隸屬于該地區(qū)的新林區(qū),是政企分開的模范。當(dāng)時,新林區(qū)不但實現(xiàn)了區(qū)、局各自掛牌,而且除了局長兼任區(qū)長以外,下面人員都進行了政企分開。但這種體制在艱難運行了兩年以后,隨著區(qū)長的升遷,模范區(qū)重回政企合一的老路。 漠河教育系統(tǒng)的改革也經(jīng)歷了這樣的輪回。實施政企分開后,原來隸屬于圖強林業(yè)局的教育局,劃歸漠河縣教育局主管,但漠河縣教育局是由西林吉林業(yè)局主管的,而西林吉林業(yè)局在行政級別上又與圖強林業(yè)局平級,所以最后這次改革只好不了了之。 1996年3月,國務(wù)院正式批準(zhǔn)大興安嶺林業(yè)集團成立。因為現(xiàn)實所迫,國家林業(yè)局希望通過政企分開,為林業(yè)集團的發(fā)展減輕負擔(dān),然而,黑龍江省卻因為解決不了人員分流、富余人員安置、政府支出等一系列問題,遲遲不愿接盤。 1998年天保工程實施后,大興安嶺的現(xiàn)實壓力得以緩解,持續(xù)了4年多的改革動力似乎借此消散,“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政企合一制度,也一直持續(xù)到了今天。 “政企不分,過去不利于林業(yè)的生產(chǎn),現(xiàn)在則不利于天然林資源的保護。”東北林業(yè)大學(xué)經(jīng)濟管理學(xué)院副院長耿玉德教授說。 雖然在過去的多次體制改革中,大興安嶺都曾積極參與,“但事實上,那些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很少有針對大興安嶺制定的,這導(dǎo)致它的諸多改革,大多是‘套’用某個政策。”黑龍江省社科院的一位學(xué)者認為,大興安嶺套用了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和政企分開的改革,結(jié)果沒有成效;之后,大興安嶺與“國企三年脫困”和“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優(yōu)惠政策擦肩而過;而現(xiàn)在,大興安嶺提出的“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林區(qū)”,也是套用 “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政策的結(jié)果。 “我們的改革好像把它給忘了。”在這位學(xué)者眼里,大興安嶺三十年的時光宛如一日。 2010年 按照規(guī)劃,到2010年,大興安嶺所有的原木必須經(jīng)過深加工后才能獲準(zhǔn)外運出售。這意味著,該地的林木深加工企業(yè)必須在未來的三年中成倍地提升加工能力,才能吃掉每年采伐的100多萬立方米原木。 90年代,該地林業(yè)局自辦企業(yè)頗多,但不論是造紙、板材,還是家具、活性炭,幾年下來,幾乎是開什么廠,虧什么廠。今天,大興安嶺的幾家大型林木加工企業(yè)都是民營。有些企業(yè)表示,擴大生產(chǎn)能力沒問題,但考慮到高昂的運輸成本,擴大生產(chǎn)規(guī)模面臨較大的風(fēng)險。 2010年也是天保工程結(jié)束的年份,到那時,大興安嶺會憑借六大接續(xù)產(chǎn)業(yè)贏得更好的生存機會嗎?在接受記者采訪的18個人中,有3個人相信,他們中兩個是政府官員,一個是離休干部。 至于大興安嶺最為看好的礦產(chǎn)開發(fā)產(chǎn)業(yè),在東北林業(yè)大學(xué)的耿玉德教授看來,也不樂觀。“地下礦藏首先屬于國家;再說,在大興安嶺地區(qū)開礦或者進行冶煉,首先需要面對的就是環(huán)境破壞和污染的問題。”他說,“大興安嶺是國家的重點林區(qū),其生態(tài)環(huán)境功能是國家死保的底線。” 在西林吉林業(yè)局的區(qū)域內(nèi),現(xiàn)在惟有富克山一地尚有可供采伐的林木資源。“其實也沒多少了。”老孫說,雖然上面批下這塊作業(yè)區(qū)才幾年,但實際上,從90年代開始,因為林業(yè)局的資源匱乏,就有作業(yè)隊在富克山上偷采了。 現(xiàn)在,西林吉旗下的五大林場,都在富克山作業(yè),“我估計,再有兩三年,富克山上也沒林可采了。”老孫說,整個西林吉林場有五六千人,在3000多上班的工人中,有2000人在富克山,其余1000人趁著黑龍江封凍期,跨江遠赴俄羅斯林區(qū)作業(yè)去了。 事實上,西林吉的資源枯竭狀況并非個案,在大興安嶺所屬的14個林業(yè)局中,除了被劃作自然保護區(qū)的,其余林業(yè)局的林木資源狀況也與西林吉相似。在加格達奇通往漠河、行程為9個小時的火車上,放眼望去,森林里能見到的只有手腕粗的新生樹木。 三年以后,是堅守,還是離開? 當(dāng)我們要大興安嶺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個樂觀的消息正在這片古老的林區(qū)中口口相傳—— 你還沒聽說嗎,大興安嶺的天保工程要延長7年…… 新浪財經(jīng)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jīng)授權(quán),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zhuǎn)載。
【 新浪財經(jīng)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