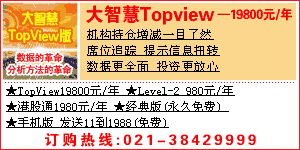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2000:一個鄉(xiāng)黨委書記的千禧年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1日 14:16 經(jīng)濟觀察報
馬國川 當千禧年的第一縷陽光投照在中國城市興奮而激動的面龐的時候,也投照在中國廣袤農(nóng)村的每一個角落,無數(shù)破敗墻體上,粗大的標語更加刺目—— 堅決打擊抗糧抗稅的壞分子! 喝藥不奪瓶,上吊就解繩。 …… 但是李昌平既沒有感受到 “迎接新世紀”的歡樂氣氛,也沒有注意到身邊的這些標語。他正開著一輛“桑塔納”到處游蕩。他是在“郁悶”中進入2000年第一個黎明的。 這是他出任湖北省監(jiān)利縣棋盤鄉(xiāng)黨委書記的第二十四天,再過一個月就是農(nóng)歷春節(jié),可是他手里竟然沒有一分錢,只有一個黑黑的大窟窿:鄉(xiāng)政府債臺高筑,不是欠銀行的——銀行已經(jīng)不敢借給他們了,而是從私人手里借來的高利貸。好多人圍著他討債,他只能說好話、陪笑臉。然而,面對鄉(xiāng)里的三百六十一個工作人員,空話和笑臉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他們已經(jīng)好幾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 “年關”如期而至。這位新任黨委書記終于借來一筆錢。他拿出干部名冊,不論級別高低和資歷深淺,每人發(fā)兩千元,另附一張“白條”。 然后他回過頭來,付給堵在門口的債主們利息。“本金?一定還,一定還。政府不會欺騙人民!請放心,請放心!”言之鑿鑿。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本金什么時候能夠還上。 一 過去的17年中,李昌平親身經(jīng)歷了農(nóng)村改革的全過程。 1983年,二十歲的李昌平從湖北省機電學校畢業(yè)后,回到洪湖邊的家鄉(xiāng)——周河公社工作。兩年后,李昌平被任命為監(jiān)利縣周河鄉(xiāng)黨委書記。 那還是一個物資短缺的時代,也是一個熱情勃發(fā)的時代。剛分到土地的農(nóng)民,生產(chǎn)積極性高漲,中國農(nóng)村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那時候,農(nóng)民收入持續(xù)上升,農(nóng)民收益一是靠糧食等大宗農(nóng)產(chǎn)品增產(chǎn)增收,二是靠非農(nóng)業(yè)收入,包括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外出打工。” 李昌平執(zhí)政下的周河鄉(xiāng)幾乎村村有漁場,每村每年從每個漁場提留一二十萬元。鄉(xiāng)里有農(nóng)工商總公司,下面有八九個企業(yè),從事農(nóng)產(chǎn)品的加工、營銷,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桐油、油漆、漁網(wǎng)等)的生產(chǎn),以及服裝生產(chǎn)等等,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年上繳提留達幾十萬元。 這一時期也恰恰是中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高速增長階段。1988年,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從業(yè)人員達到9495萬人,這是鄧小平也沒有預料到的收獲。“那時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為什么能蓬勃發(fā)展?因為那個時期的農(nóng)民集體有權用土地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農(nóng)民可以分享土地非農(nóng)用資本收益。”后來,離開家鄉(xiāng)的李昌平在對中國近六十年的土地政策進行研究后認為,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對農(nóng)民最有利。 但是,就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聲飄蕩全國的時候,身處田野的李昌平卻知道,事情在悄悄發(fā)生著變化。 198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鄉(xiāng)(鎮(zhèn))村企業(yè)建設用地,“必須嚴格控制”。從此,農(nóng)民要辦企業(yè),必須到城里的工業(yè)區(qū)去,農(nóng)民使用土地辦企業(yè),要經(jīng)過“國家審批”,先將土地變?yōu)閲型恋兀缓笤俑邇r買回來。這不但剝奪了農(nóng)民分享土地非農(nóng)用資本收益的權利,也限制了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和村辦企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 從第二年起,國家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采取“調(diào)整、整頓、改造、提高”的方針,減少了稅收、信貸方面的支持和優(yōu)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確規(guī)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所需的資金,應主要靠農(nóng)民集資籌措”,“進一步提倡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要立足于農(nóng)副產(chǎn)品和當?shù)卦霞庸ぁ薄`l(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村辦企業(yè)從銀行貸款變得十分困難。同時,國家給予沿海地區(qū)很多外企“超國民待遇”,這對于內(nèi)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李昌平更直接的感受是,鄉(xiāng)鎮(zhèn)部門開始增多了,工商、稅務、漁業(yè)、林業(yè)站等等建立起來,每個部門都靠創(chuàng)收存在。開始周河鄉(xiāng)政府只有八九個干部,可是到1993年李昌平擔任周河鄉(xiāng)的黨委書記時,他發(fā)現(xiàn),吃財政的干部已經(jīng)超過了百人。 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使得“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稅收,但農(nóng)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yī)療等事務逐步下放給基層政府。農(nóng)村教育、醫(yī)療、生產(chǎn)資料等成本的增加,導致農(nóng)民負擔很重。而越來越多的吃財政的干部都要工資,“我們只能找農(nóng)民要,所以干群關系十分緊張。”李昌平說。 二 “剛到鄉(xiāng)鎮(zhèn)工作的時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時候,我是有抱負的。可是到了90年代,年紀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經(jīng)驗增加了,但是事情卻辦不好了。到處得罪人,只有欺侮農(nóng)民。” 李昌平?jīng)Q心做些事。 精簡機構、清退編外人員、減輕農(nóng)民負擔、治理亂收費……今天的人們把這些都稱為改革,而且給予高度評價。作為一個農(nóng)民的兒子,深知農(nóng)民疾苦的李昌平從不否認自己的農(nóng)民情結,但是他對自己當年的改革評價并不高,“一切都是逼出來的,上面不給錢,不改不行了”。 1996年,李昌平的改革在周河鄉(xiāng)取得顯著成效。三年前,該鄉(xiāng)是監(jiān)利縣經(jīng)濟最落后的鄉(xiāng)鎮(zhèn),是年,該鄉(xiāng)成了全縣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財政收入進入全縣26個鄉(xiāng)鎮(zhèn)中的前五名。李昌平成了減輕農(nóng)民負擔的“英雄”,全省優(yōu)秀黨員。但是,他卻遭到了全縣執(zhí)法收費單位的集體發(fā)難。更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一旦他被調(diào)離,一切又立即恢復到原樣。 在痛苦和迷惘中,一起突如其來的事件差點斷送了他的仕途。 1997年春季,監(jiān)利縣政府頒布命令,要屬下農(nóng)民將全年稅費的四分之一在當年5月繳納。按照既成制度,稅費本該在收獲以后交納,監(jiān)利縣此舉顯然違背成憲,但是沒有任何人提出質(zhì)疑。 從官員的立場上來看,連續(xù)多年行此寅吃卯糧之舉,實在是掩蓋財政破產(chǎn)危機以及維系官員生存的無奈之舉。當時,所有本當由政府舉辦之事,諸如維護道路、擴建學校、修復被洪水摧毀的壩橋閘渠、建設縣城賓館和機關干部住宅、購買官員轎車等等,全都不能實現(xiàn),甚至連干部工資也不能按期足額發(fā)放。征稅期限不符合生產(chǎn)周期,適逢鄉(xiāng)村青黃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產(chǎn)資金的季節(jié),政府與民爭利已成常態(tài)。雖然前一年監(jiān)利南部十個鄉(xiāng)鎮(zhèn)遭遇水災,顆粒無收,湖北省委書記已經(jīng)明確要求給災區(qū)減免稅費,況且“災民免繳皇糧”在我們國家也是自古而來的傳統(tǒng),可是在二十世紀末的監(jiān)利實行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如今的農(nóng)民“稅費”并非“皇糧”,而是地方官員的衣食,所以監(jiān)利不僅不肯減免,反而要求農(nóng)民提前繳納。 柘木鄉(xiāng)茶卜村有個婦女朱長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她搬出省委書記“受災免稅”的承諾,要求政府先行退還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應將那一筆錢用來抵交眼前稅費。這一要求從制度和道理上來說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筆錢早被官員花完了,登門的收費干部當然不允。于是發(fā)生口角直至肢體沖突,干部在盛怒之下將她的丈夫捉起來,關到小學校里,說是“辦學習班”。朱長仙當即喝農(nóng)藥自殺,她的尸體被農(nóng)民抬到鄉(xiāng)政府。然而這還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監(jiān)利縣的另外一個村莊,一個小學教師也因不堪沉重稅賦而自盡。這兩件事情恰巧發(fā)生在7月1日香港回歸日前夕,牽涉政治大局的穩(wěn)定。所以當日就有指令傳達下來:“從重從嚴從快”懲處肇事官員。 時任柘木鄉(xiāng)黨委書記的李昌平雖然遠在數(shù)百公里的武漢學習,但是當時的縣委書記要求他“自請?zhí)幏帧薄S谑抢畈綄懴铝宿o職報告,雖然事件調(diào)查組的成員說這是監(jiān)利縣委的“丟卒保帥”之舉,但是在李昌平的報告里沒有冠冕堂皇的大話,而是充滿了“負罪感”,“和朱長仙的生命相比,給我這個黨委書記一個處分算得了什么呢?”李昌平被撤消了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 三 在辭職報告里,李昌平這樣寫道,“如果給我處分能促進中央政策的落實,能讓農(nóng)民相信黨,我愿意接受任何處分。誰叫我是共產(chǎn)黨員!”可是事隔三年,當他回到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他所擔心的局面不僅沒有絲毫改觀,反而更加嚴重。 走在正月里的農(nóng)村,他看到的不是過年的喜慶。一些農(nóng)家的大門緊鎖,悄無聲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過年也沒回來。另外有些農(nóng)家有人聲,但不是笑聲。“到處都是骨肉分離,擁抱泣別的場面。那些可憐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雙腿不放。”這位黨委書記的“桑塔納”也被攔下。農(nóng)民說想搭車,他一點頭,就擠上來五個人。他問他們?yōu)槭裁匆尘x鄉(xiāng),一個人說:“你們當官兒的心太黑,不出去沒有活路。”他有點不相信,覺得這些人也許就是城里人常說的“無賴”,或者是官員們口中的“刁民”。 然而一路上的情景卻讓他淚流滿面。“成群結隊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滾滾的洪流勢不可擋。不管是什么車,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統(tǒng)統(tǒng)攔下搭乘。如果是客車,一定要擠到裝不下最后一個人為止。如果是貨車,就放上稻草,像裝貨物一樣裝人,直到裝得不能再裝為止。” 當他走進角湖村黨支部書記李先進的家時,他發(fā)現(xiàn)這位少年時代同學的家仍然是兩間熟悉的瓦房,那還是十五年前蓋的,已經(jīng)破敗不堪,仿佛隨時就要倒塌。十五年前這位同學結婚時置下的黑白電視機,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錢的電器。李先進的母親雖然只有六十歲,看上去卻像八十歲的人了,讓他不敢相認。“過去只愁沒有糧食吃,現(xiàn)在好了,糧食不珍貴了,愁的事也多了”,這老太太說,“愁孩子讀不起書,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稅……”。不過李昌平知道這是真話,他上任這兩個月來,親眼看著他的親姑媽和親姑爺有病不治,慢慢死去,還親耳聽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漢1999年交了七百元的“人頭稅”。他的上級說,這“人頭稅”是增加財政收入的“好經(jīng)驗”!侯家老漢跑了十幾里來找李昌平,只為了問一句話:“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 憑著對家鄉(xiāng)父老的了解,他知道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漢永遠不會是那種“刁民”,可是就連他們也是怨氣沖天了。一個說:“老了,政府不僅不養(yǎng)我們,還要我們這些老人養(yǎng)政府!”另一個說:“這個政策要變一變,再不變,老百姓可是沒法子生活了。”這場面令李昌平震撼,多年以后還記憶猶新:“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農(nóng)民太苦了!太可憐了!面對他們,我總有一種負疚的感覺。”更讓他不寒而栗的是農(nóng)民對官員的敵對情緒。看來他過去聽的那些報告并非實情,下級糊弄上級,而他的上級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裝糊涂。 下轉50版 上接47版 四 1962年春天,陜西戶縣農(nóng)民楊偉名寫下《當前形勢懷感》。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nóng)民面對 “瀕于破產(chǎn)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面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如洶涌狂濤,沖擊心膛”。在文中,楊偉名概述當時國民經(jīng)濟形勢特別是農(nóng)村經(jīng)濟形勢時說:“目前我們已經(jīng)承認 ‘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nóng)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現(xiàn)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chǎn)凋零代替了五谷豐登,饑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于破產(chǎn)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他質(zhì)疑:“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來形勢是逼人的,不過困難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盡速地應用于當前形勢,諸如一類物資自由市場的開放,中小型工商業(yè)以‘節(jié)制’代替‘改造’,農(nóng)業(yè)方面采取‘集體’與‘單干’聽憑群眾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膽考慮的。” 初夏,這封近萬言字的建議信發(fā)向了公社黨委直至黨中央。因為文中有“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之語,故又名《一葉知秋》。這篇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干希望……共產(chǎn)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于衷。”各級工作組接踵而至,楊偉名被迫作了違心的檢討。“文革”中,楊偉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同妻子雙雙服毒身亡。 37歲的李昌平還不知道楊偉名這個人,更不知道他的未來命運。此時他只想選擇一個人傾訴自己的話。“最終我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傾訴對象”,他后來在一本類似自傳的書里回憶這個晚上的情形,“當我提筆寫下‘總理’兩個字時,淚水頓時溢滿了我的眼眶”。 這是2000年2月10日的午夜。 “我要對您說的是,現(xiàn)在農(nóng)民真苦,農(nóng)村真窮,農(nóng)業(yè)真危險。”在閃爍的燈光下,李昌平寫出當代中國農(nóng)村史上最觸目驚心的一段文字。他告訴共和國的第五任總理朱基,農(nóng)民不再熱愛土地,因為百分之八十的農(nóng)民種田虧本。官員本來是按照土地攤派稅賦的,現(xiàn)在只好轉而按人丁攤派,叫做“人頭費”。中央政府稅收體系中沒有這個名目,可是干部執(zhí)行此項制度卻格外認真。“喪失勞動力的八十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地交幾百元的‘人頭’費。”盡管如此,鄉(xiāng)鎮(zhèn)政府依然債臺高筑,每年從農(nóng)民那里弄來的錢,除了償還債務利息,還不夠給干部發(fā)工資的,因為依靠稅費養(yǎng)活的人在過去十年里增加了兩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貸,去農(nóng)民頭上搜刮更多的錢來還債。如此年復一年,政府的債臺愈高,百姓積怨日深。“這樣下去,黨的基層組織和政府怎么運轉啊?”李昌平感嘆:“現(xiàn)在真話無處說,做實事求是的干部太難,太難啊。” 信寫完了,心情平靜下來的李昌平在猶豫中過了三個星期。黨的制度雖然允許任何一個黨員直接上書最高領袖,但李昌平知道,這個舉動不會被他的上級原諒。他對上級仍然抱著一點希望。可是在縣委隨后召開的一次宣布當年農(nóng)民的稅費數(shù)量繼續(xù)上漲的會議上,當他直言不諱地說農(nóng)民負擔過重并引發(fā)了惡性循環(huán)后,卻無人回應,縣委書記甚至說:“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 “我沒有理由不把給總理的信發(fā)出去。”李昌平走出會場時這樣想。他對自己的直接上級已徹底絕望。 五 中央調(diào)查組來了。 那封4000多字的信發(fā)出還不到一個月,中央調(diào)查組就來到了監(jiān)利縣。調(diào)查沒有找縣領導,而是直接與李昌平接洽,走訪村民,發(fā)現(xiàn)情況比信中所反映的還嚴重。在閱讀了調(diào)查報告后,朱基總理批復說:農(nóng)民真苦、農(nóng)村真窮、農(nóng)業(yè)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于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而誤信了基層干部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也對調(diào)查報告作了批示,強調(diào)要切實減輕農(nóng)民負擔。 當年6月,湖北省決定在棋盤鄉(xiāng)、監(jiān)利縣進行改革,“取得經(jīng)驗,在全省推廣”。2000年8月《南方周末》頭版的大幅報道,使得李昌平成為一個新聞人物。《南風窗》的總編輯秦朔還專門寫了一篇短文,稱他是“一個時代的發(fā)言者”,還說“每一個時代都在尋找為它的命運而殫精竭慮的發(fā)言者”。 但化解債務、精簡機構、減輕農(nóng)民負擔,無一不是與利益集團做斗爭。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他成為了該縣“不穩(wěn)定的核心”。來自地方的龐大調(diào)查組使李昌平陷入尷尬的境地。他終于不能忍耐,辭去黨委書記職務,而且決心選擇離開家鄉(xiāng)。后來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給朱基總理寫信時是抱著希望的話,那么,辭職時是絕望的。” 離家的前夜,李昌平獨自跑到長江邊,放聲大哭。 在一些人眼里,他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是失敗者。因為李昌平被迫辭職離鄉(xiāng)、南下打工去了。 這一年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曹錦清將其在黃河沿途所看、所聽、所談、所思,結集為《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xiāng)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并出版;第二年,于建嶸的博士論文《岳村政治》出版;2002年,李昌平出版了 《我向總理說實話》。這些關系“三農(nóng)”的書籍都引起不同程度的轟動,“三農(nóng)問題”日漸成為學界和政府共同關注的話題。 在 《我向總理說實話》的前言里,李昌平寫道:“回首農(nóng)村工作的17年,對農(nóng)民好事做得太少,壞事做得不少,于農(nóng)民,我是有罪的”,“我,農(nóng)民的父母官,應該無數(shù)次下地獄”,“我現(xiàn)在懺悔我的過去,我怕懺悔晚了,上蒼不原諒我。” 新浪財經(jīng)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jīng)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