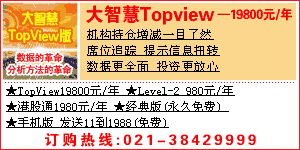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民初憲政挫敗與啟蒙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1日 14:15 經濟觀察報
袁偉時 多年來,世界各地時興反啟蒙。當前中國的國學熱,其中最極端的主張,底色也是否定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明。從根底上看,這不是理論論爭,而是史實的考查問題;摘引某些學者的推斷不足于澄清真相,問題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尋找。 辛亥革命,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固有體制;五族共和,民主,憲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頭禪。可是,好景不長,只有四年光景,民國招牌被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所取代。從思想淵源來說,這是鴉片戰爭以降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后啟蒙運動成敗的記錄,是研究啟蒙和憲政歷史命運的很有價值的個案。 民初憲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辛亥革命后第一個憲法文件也在這里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義,11日由起義領導人和諮議局推舉黎元洪為都督;17日制定了 《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組織了適應戰爭環境的中華民國軍政府;25日修訂了這個條例,頒布實行 《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實行“公推都督一人,執行軍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規定“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系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議決施行。”同時設立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檢查各軍隊和各部、各機關。從而顯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點。而在10月28日至11月13日期間制定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后第一個憲法文本,也是當時同類文件的范本。 這個約法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一要三權分立,二要保護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在規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時,規定 “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并集會結社”;“人民自由保有財產”;“人民自由營業”等八項自由。在隨后支持共和而宣布“獨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隨《鄂州約法》,堅持三權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則。例如,1911年12月29日通過的《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軍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務員,與議會法院三部構成之。”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這些憲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國元年 (1912)3月11日公布實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一樣,是同盟會的重要領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與文字,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也是一脈相承的。它規定人民享有囊括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七項自由權;建立三權分立體制:“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國務員則“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并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法官獨立審判”,并相應建立法官不得免職、轉職、減俸等制度,為司法獨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這些文本大體與現代各國的憲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臨時約法》制定以前,堅持三權分立原則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臨時參議院列入 “政府交議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當天上午“討究結果:公議由秘書長起草,咨復政府,并將原案退回。”第二天發出的咨文寫道:“憲法發案權應歸國會獨有。而國會未召集以前,本院為惟一立法機關。故臨時組織法應由本院編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擬,未免逾越權限。”堅決將這個越權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當時和后來的學者指出 《臨時約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給后來的政治生活留下禍根。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它沒有為公民的自由權利建構切實的保障。 這些文件列舉了公民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這些規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驅們力圖帶領中國攀上人類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并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沒有解決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于補救:“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ofHabeas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并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盡管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憲法草案和憲法都接納了這個批評意見,規定要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但都沒有付諸實施。 與此同時,章士釗還指出,《臨時約法》的有些規定為行政侵犯司法獨立留下了隱患。《臨時約法》第10條規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揭露,所謂平政院屬于行政裁判系統。“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貓口之鼠之自由矣。”因此,他堅決主張刪除這一條。 此外,這些文件無一例外都附上一條尾巴:“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歷史已經證明,它為專制統治者制定惡法肆意“依法”剝奪公民的自由大開方便之門。20世紀中國社會精英的認識遠遠沒有達到18世紀美國建國領袖們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準生效的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愿的權利。”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臺,美國不斷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點,演變成為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 二,它沒有建立徹底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失去制約和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和專橫。《臨時約法》設計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嚴重缺陷是參議院(國會)的權力沒有受到必要的制約。 它規定:“參議院對于國務員(總理和各部總長),認為違法或失職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彈劾之。”但是,如果行政系統嚴重不滿立法系統的作為,卻沒有救濟的手段。與多數現代國家的憲法不同,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沒有辦法把矛盾訴諸國民作最后的裁決。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行政權非常強大,而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則處心積慮冀圖推行內閣制,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兩強相遇,如何良性互動?如果制度設計合理,有可能壓制雙方過大的欲望,在沖撞中謀求妥協;即使妥協無望,也可以在既定的軌道中重組內閣或解散國會,保持政府正常運作。可是,《臨時約法》設計的制度漏洞導致雙方都走向極端:袁世凱干脆摧毀國會,成立御用的參政院,復辟帝制;國民黨控制下的那些國會議員除少數潔身自愛者外,則紛紛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壇中翻云覆雨,公開或暗中謀取私利,最后以5000大洋一票的價格出賣靈魂,賄選曹錕為大總統。兩敗俱傷,雙方都留下千古罵名。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任何國家的民主憲政都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全十美;不斷補漏、增強才會走上康莊大道。應該肯定,民初民主憲政有過良好的征兆,必然失敗論流于表面,沒有深刻揭示內在的復雜關系。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臨時參議會就有不俗的表現。除了上面談及的以外,還有幾個事例: 一,實事求是,承認現實,平穩過渡。 與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不但沒有出現駭人聽聞的對王公貴族和其他特權階層的屠殺,反而承認現實,繼續保持原有待遇。1912年2月6日參議院通過決議,規定“清帝遜位后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其宗朝(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同時規定滿蒙回藏各旗 “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先籌八旗生計,于未籌定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取”。 對清代法律則采取稍加修改,全盤繼承的方針。根據孫文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前的提議,參議院通過決議:“所有前清時規定之 《法院編制法》、《商律》、《違警律》及宣統三年頒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并先后頒布之《禁煙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余均準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并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后凡關民事案件,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 總覽當時情況,在革命外衣下,改良的氣味十分明顯。 二,否決行政系統的違法建議。 孫文號稱創國元勛,后來更被國民黨尊為 “國父”,但在民國元年(1912)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在參議院碰了兩次釘子。 除了上面已經談及的孫大總統將法制局所擬的 《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咨送參議院,被參議院退回外;另一次是急于找錢的臨時政府為取得貸款,滿足日本人覬覦已久的圖謀,強迫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懷將漢冶萍公司的部分股權轉讓給日本人。當孫文將這筆貸款案咨請參議院批準時,它通過決議:“僉以漢冶萍煤鐵公司與日人合辦,喪權違法。前由本院兩次質問,政府派員答復,毫無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交本院議決,無論股東會能否通過,本院決不承認。”孫文的算盤落空了。 盡管開局良好,民國憲政進程還是中斷了。個中原因安在? 有好些學者認為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仍然是農業經濟時代是中國民主憲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過,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憲政制度,那時離產業革命肇始之日還有50年以上;通常認為產業革命完成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后的事了。美國憲法頒布于1787年,當時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兩百多年來其憲政卻一直運行無礙,日趨完善。中國就生產力水平來說,與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別不是太大;而經過鴉片戰爭以來60年創巨痛深的折騰,從1901年開始,朝野上下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已經基本一致;作為有悠久商業傳統的國家,經濟領域也不乏契約精神。毋庸諱言,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幅員遼闊的大國,地區差別是十分懸殊的,但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帶和長江兩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間社會組織 (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種商會)的發源地和政治家的搖籃。 當時的迫切任務是為人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尋求政治保障,經濟發展的障礙不在經濟本身;民主憲政受挫的答案必須在經濟領域以外去尋求。 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公民權利訴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會留下一些震古鑠今的文件。從1215年英格蘭的 《大憲章》到《權利法案》、美國《獨立宣言》、《人權法案》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標志著文明的進展。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謂不多,但作為歷史文件去審讀,傳遞給后人的是什么信息呢? 武昌起義后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義,向海內外發布了《布告全國電》等十個電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體”、實行“國民主義”,“查舊日滿清流毒之由,在于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自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為共和政體”等字句,但這些字眼寥寥可數,一閃而過,不是文告的主體。連篇累牘的是光復漢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 “愿我族協力同心,復黃帝衣冠之舊,執戈起義,啟中華禮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復大漢之山河。”“中國亡于滿洲已二百六十余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 “深恨胡虜,非我族類”。 “……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恥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于衽席。”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 起義各省的文告,內容驚人的一致,基調都是民族主義,而且貫穿其中的是為漢族報仇雪恥的滿漢對立或者華夷有別的觀念。請以思想觀念最為開放的江蘇(包括它管轄下的上海)為例: 上海 《軍政府布告》:“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國”。 江蘇都督府的大旗上寫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興漢安民”。 而在全國性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有關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狹隘民族主義烙印。孫文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的文告中,“滿人竊位”、“逆胡猾夏,盜據神州”、“異族專制”、不要“為異族效命”、“重睹漢儀”等字句比比皆是。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臘月28),南京臨時政府諸公得悉清帝頒布《退位詔》的第三天,在軍務、外交、財政等難題堆積如山的狀況下,居然不惜辛勞,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馬屁:“蓋中夏見制于邊境小夷者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勛,未有能及太祖之偉邵【碩】者也。”并且不倫不類地把辛亥革命與朱皇帝捆綁起來: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后人,成茲鴻業。”“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把接續漢族統治的傳統視為一件大事,根本沒有想到朱元璋殘忍的專制統治與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不少學者已經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國為職志的革命派,指導思想頗為龐雜,最為統一和突出的則是推翻異族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同盟會把“驅除韃虜”作為綱領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肯定,辛亥革命過程中,對民族關系的處理是比較穩妥的,除了個別省份(如浙江)有些小沖突外,滿、漢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實現了政權交替。就以浙江來說,雙方在兩個條件下停止了沖突:一是旗兵繳出槍械、彈藥;二是“旗兵向以兵餉為生,現已改編民籍,一是斷不能使之失所,暫仍照舊發給餉項”,可謂合情合理。 廣東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由漢滿兩族代表共同主持會議,選出新政府負責官員和決定當前的重大措施,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在全國范圍內,“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號也傳遍四方。 行動與語言呈現巨大反差。這既體現了各地紳商的穩健,也反映了漢族華夷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視域太窄,沒有把推進民主憲政作為行動的主要推動力。 以孫文來說,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滿漢之不容”,康梁是“漢奸”,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義”,把華夷之辨作為“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 《民報》的基調和同梁啟超的《新民從報》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滿族人視為外國人。用朱執信的話來說是:“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而這一論點的始作俑者是孫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開聲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是外國人占據著的。” 民族主義情緒彌漫的直接后果是這次革命沒有把公民自由權利擺到應有的位置;而啟蒙運動的根本訴求恰恰是人的覺醒和公民權利保障。在各國民主革命的文獻中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1912年1月1日,孫文宣誓就職,當天發表了兩個宣言:《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通告海陸軍將士文》;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盡掃專制之遺毒,確定共和”的名義下,宣布“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和“財政之統一”等五個統一“為政務之方針”,卻只字不談公民的自由權利。后者則稱:“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而吾皇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衍于無極”。直到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才想到用對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認同去解釋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賦自由,縈想已夙”;“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圣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壓倒了民主、自由的訴求。民族主義是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階梯。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辛亥革命后,社會精英審時度勢,把漢族的民族主義訴求迅速轉化為“五族共和”的國家主義。對一個被侵略的衰弱國家說來,這是受到廣泛歡迎的轉變。可是,這個轉變帶來新的隱憂: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還是在共和外衣掩蓋下的專制國家?有沒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夠的智慧集結力量,在實踐中糾正文本的缺陷,引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自由憲政? 一代啟蒙大師梁啟超也被國家主義引入歧途 在當時的政治家當中,梁啟超是對憲政理論領會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實際政治運作,他立即陷入冀圖建構威權體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樣和袁世凱溝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啟超給身為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寫信,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基本傾向是力圖在中國建構兩黨制的政治架構,體現了清醒的現代政治意識。他說:“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為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于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民國初年,三大政治勢力在博弈: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派;梁啟超為首的原立憲派;以袁世凱為中心的北洋派軍政大員。 實權掌握在袁世凱和他的追隨者手中,這些人不是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這些人追求的是富國強兵,是發展經濟以及作為經濟發展必要條件的辦新式教育,改革舊的司法體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實行憲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領導人一樣,他們大體把民主、憲政理解為決策程序,不但不了解憲政的核心是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專制統治習慣隨時流露。其上焉者以為民做主心態君臨天下,往往在辦一些富國利民的好事的同時,說不定什么時候重大決策失誤,造成難以彌補的大災難。下焉者則口誦民主共和,實則為一己私利橫行無忌。怎樣把這些良莠不齊的實權派逼入民主共和軌道?這是關系共和國命運的關鍵。 梁啟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預備立憲之際,已經察覺必須和可能與袁世凱合作推進新政,顯示了不計前嫌的政治家胸懷。辛亥革命后,雙方都表達了合作的愿望。作為與革命派有別的政治力量,他們的聯合無可厚非;恰當運作,有助于推動最有利于民主發展的兩黨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啟超看到了化解激進思潮的迫切,卻忽視了牽制和監督袁世凱及其追隨者。梁啟超后來組成的進步黨成了依附袁世凱的參政黨,甚至在袁世凱摧毀國會后仍亦步亦趨,參加了取代國會的御用機構 “政治會議”和 “參政院”。這樣的參政黨成了專制統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國被推翻帶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的環境,梁啟超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環境,既無力阻擋激進思潮的蔓延,更沒有密切監督袁世凱的施政。直到復辟帝制的丑劇鬧得不可開交,他才挺身而出與袁世凱決裂。就個人而言,他仍然不失為反復辟運動的旗手;而就整個國家來說,未能阻擋這幕丑劇上演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這些行動體現了梁啟超政治思想的弱點。清末新政期間,已經顯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奇怪的組合:既把憲政視為中國發展的惟一選擇,又力倡開明專制,認為它是走向憲政必經的過渡階段。他和袁世凱等開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線上。這不僅是梁啟超個人的失誤,而且是20世紀中國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征。 梁啟超以善變著稱,其思想又是駁雜的,但在一個時段中,脈絡還是清晰的。 從1905年開始,他把提倡憲政放在突出位置。與清廷把憲政擺上議事日程相呼應,他組織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為職志的政治團體——政聞社。他起草的《社約》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確定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盡管它成立不到一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關注的四條綱領: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這個綱領擺脫了當時流行的富國強兵論者就事論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變革作為中國救亡圖存的康莊大道,特別是把人權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 它明確規定:“國家之目的,一方面謀自身之發達,一方面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為國家發達之源泉,故首最當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為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這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由政黨發布的人權保障宣言,后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都證明,這些論斷一語中的,揭示了20世紀中國盛衰的關鍵。 他還直接與當朝大員合作,配合和幫助清政府的預備立憲。1905年“秋冬間先生為若輩 (端方等清帝國大臣)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并赦免黨人,請定國是一類的奏折,逾二十余萬言。”2006年8月清廷派出到國外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遞交的 《考察各國憲政報告》等文件,就是梁啟超起草的。保皇會及其出版物也相應作了調整。 但是,與此同時,梁啟超也不遺余力鼓吹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憲政與開明專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極端,梁啟超為什么會將兩者同時端出來呢?在他看來,“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更不用說民主立憲了。理由有兩條:“(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機關未整備”。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實行,法律不完備,司法不健全等等。可是,1904至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打敗老大的俄羅斯帝國,震撼了海內外輿論。久久未能擺脫貧弱困境的中國,士紳和城市居民對憲政的向往,更難于遏止。在內外形勢脅迫下,梁啟超及其追隨者不能不調整策略,參與立憲運動,但是,他們認為實現憲政需要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過渡期。在梁啟超看來,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開明專制階段都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指出,開明專制論不僅是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認識,激進如陳天華,也持此說。他在留給湖南留學生的絕命書中寫道:“當今之弊,在于廢弛,不在于專制。欲救中國,惟有開明專制。”這封信寫于1905年12月7日,比梁啟超發表《開明專制論》(1906年1月25-3月25日)還要早一些。也許有人以為,這是個別人士的極端觀點。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為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革命派領導人誠然沒有忘記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掛在嘴邊。但是,他們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逐步形成以軍政、訓政、憲政命名的革命三階段論,所謂訓政就是開明專制的別名。 為什么互相對立的兩個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會在這里交集?竊以為雙方有共同的認識誤區: 首先是對自由的誤解。對于自由,梁啟超在1900年前后曾有非常精辟的論述。他在反駁其師康有為否定自由的觀點時指出:“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他接著駁斥所謂民智未開不能實行民主和自由會導致混亂的糊涂思想說:“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又自由與服從兩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這些話在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是常識,在發展滯后的中國卻至今仍被目為啟蒙者的語言,不時還被一些人視為異端邪說,成為思想圍剿的目標。翻檢20世紀中國思想史,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先驅,不得不為宣揚這些常識殫精竭慮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 不幸的是,梁啟超沒有將這些正確觀點堅持到底。轉折發生在1903年。他斷言:“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與此同時,他認為,19世紀末開始,“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國主義大起……乃至于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范圍,以競于外,而他國更何論焉!”20世紀初葉開始,同盟會和保皇黨人異口同聲說:國家利益和國民素質低下決定中國人必須放棄個人自由。而離開個人自由的所謂國家、民族的自由不過是獨裁專制的別名。國家主義蒙住了啟蒙先驅的眼睛,兩個流派的領袖們的思想在這里匯合了。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層面,在國家、民族、集體這座迷宮面前,都忙著頂禮膜拜,而忘記離開人的解放,離開公民權利的保障,不但國家失去根基,人們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的目標也會化為鏡花水月。要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必須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較深切的了解。不幸,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很少人能達到這個高度。這是20世紀中國兵連禍結的重要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是以西方經驗作為開明專制論的根據的。他認為法國“革命之后,殆如無政府然。故再經拿破侖之十年開明專制,裁抑而鍛煉之,而憲法乃漸確立也。”普魯士“行開明專制最久”,到德國統一后,“鐵血宰相之政治,名為立憲,實變相之開明專制耳。”而東方后起的強國“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二年,皆開明專制時代也。”從歷史經驗看,梁啟超推崇的這些東西方國家的所謂“開明專制”都沒有成為過渡到憲政的橋梁。他們走上憲政軌道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 (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真正實行憲政)。 但是,梁啟超的這些論斷卻體現了他的政治思想的變遷:從盧梭轉向伯倫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國家主義壓倒了自由、民主的訴求。 民初憲政挫敗說明什么? 民初憲政歷程表明,用中西文化沖突的簡單模式,已經無法解釋復雜的社會現象。 19世紀中國啟蒙的主角是西方傳教士,包括康梁在內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是他們的學生。進入20世紀,隨著國門大開,留學生涌入東瀛,本土知識精英主宰了思想文化陣地。他們分裂為不同的流派,但無論哪一派大體上對東西文化都有所了解。于是,即使是開明專制論乃至復辟帝制、實行赤裸裸的專制統治,有關人士不但從本國傳統尋找資源,也力求從西方流行理論中尋找根據。 上述情況表明,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焦點不是國別或地區文化,而主要是維護專制的觀點與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之間的沖突。換句話說,面對公民權利的覺醒,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籠罩下的專制文化突顯,成為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思想障礙。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專制、等級和服從。因此,濫觴于鴉片戰爭前后的中國新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反對傳統核心價值的姿態 (但不是全盤反傳統),這是情境使然。與此同時,西方的專制或偏激文化,也先后涌入中國,與傳統專制思想匯合,成為中國人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從而為國家繁榮奠立堅實基礎的主要障礙。 中國人所以無能阻擋這些思想文化逆流,說到底是對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了解和普及。一百多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累撲累起,無非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受挫的側影。目前反啟蒙的聲音甚囂塵上,實質是對歷史進程的誤解。加深對現代文明普適性的核心價值的認識,堅持不懈用各種方式做好普及工作,仍然是中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任務。 (本文有刪節,并略作者原注釋若干) 新浪財經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