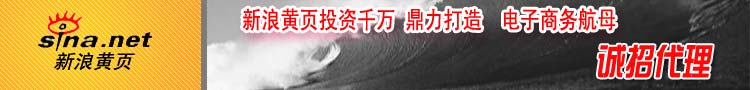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數字化生存的信任危機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6日 11:15 南方都市報
劉陽 多年前初讀黃仁宇,覺得他把歷史梳理得別開生面。隨后不斷看到有人引用他的“大歷史觀”: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就是從非數目字管理向數目字管理過渡的過程,中國近百年來的曲折莫不與此相關。 掌握“用數目字管理國家”的能力,似乎成為歷史發展的目的。有了“目的論”的終極承諾,肯綮一通百通,就連國共兩黨的歷史角色也擺平了:大家原是一場接力賽里的兄弟,政權更替的暴力過程,在“大歷史”的觀照,其實只是兩個隊友在交接棒。 相對而言,“數目字管理”是一個偏重技術性的概念。它不重視“數目字”背后的文化差異,不強調“管理”背后的價值關懷,似乎現代文明的產生很可能是一個“技術活”,只要中國人下決心不再做“糙哥”,就能完美復制一個現代文明。大陸讀者從回避價值判斷、實用主義至上的當下語境出發,在諸多對現代化的描述、分析與想象中,顯然對這一樂觀立場產生了熱烈的共鳴。 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變固然不易,但事實證明,“權力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變更為艱難。中國的進步顯而易見,盡管每年在GDP增幅之類統計數據上,地方還熱衷于和中央玩擰毛巾的游戲,但畢竟在行政手段之外,近年來,央行已開始學習動用利率杠桿調控經濟。 不僅如此,我們的生活已經呈現出一幅“數字化”的景觀。人們對不能用數字表達的觀念似乎已提不起興致,例如,效率是實打實的一組數字,而公平只是一個供講述的觀念。“綠色GDP”考核指標,至今無法順利納入官員考核體系,筆者認為,指標數字背后的內涵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新理念,其中蘊涵著強烈的人本關懷,以至于傳統的權力分配結構和政府運作模式一時間竟無法消化。癥結于內,外顯為中央政令不暢,行政法規、部門立法與憲法原則的齟齬。 可見,由技術官僚主導的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在技術層面上已臨極限。或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有識之士不斷論及中國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必須依靠全面推進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改革來清除,改革必將是波及執政者利益的一場“自我革命”。 沒有合理的制度,不僅不會有正確的數字,更不會有對正確數字的合理解讀。例如,基尼系數本是顯示一國貧富差距的實打實的數字,但究竟如何解釋,技發于心,則又生出許多“技巧”。而所謂“科學的統計數據”,統計學里有一個最具反思精神的概念叫做“統計撒謊”,提醒人們對數字別有用心的使用。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在中國被宣傳到幾乎家喻戶曉的國際慣例,大多都是關于收費的。 “數字化生存”與“信息時代”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盡管中國依然艱難地走在通往“數目字管理”的變革之路上,但在登堂入室之后,政府迅速掌握了信息技術,并發展出一套“哲學”,以確立其信息管理方式的合理性。數目字管理的能力越強,對資源的支配就越有效率,信息的控制成本也就越低。當對權力的制約僅僅來自上級的時候,其危險就在于它將誘使管理者不再關注問題本身,而是用心于對有關問題的信息的控制。 在數字化時代,占有并提供信息、利用與開發信息,都可能收入不菲,網絡在這方面示范作用明顯,納斯達克把最健康的財富夢想空投到中國。而控制好信息,同樣也能暴斂橫財,最新的例子是湖南郴州腐敗窩案中的市委宣傳部長樊甲生,被稱為“礦難新聞滅火隊”。當礦難發生后,樊甲生監督新聞監督,在第一時間對消息進行封鎖,事后從黑礦主那里獲得礦山干股或現金回報。而最近的案情進展是郴州“首貪”紀委書記曾錦春被糾,樊甲生不過是負責“信息控制”的專職馬仔。 這一個案凸顯出當世界已經步入信息時代后,中國式的“數字化生存”的一體兩面:數目字管理能力與信息控制的結合。沒有價值觀的數字管理,模糊了管理與控制的差別。 根據美國學者新近以印尼為樣本進行的研究,由于政府官員有多種辦法隱藏腐敗信息,公眾獲知的渠道非常有限,當公眾感覺腐敗程度惡化0.8%時,真實腐敗程度其實已然飆升了10%。信息的不對稱,加大了監督的難度,持續損害著社會成員間的信任,在經濟領域則體現為信用匱乏、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小到幾個人的公司,大到幾億人的國家,信任的崩潰先于組織的崩潰;依靠“數目字”維持的利益茍合,只求短期回報,難做長久預期,遑論“可持續發展”。波蘭社會學家深入考察本國的社會變遷,以統計數據為依據,得出民主與市場化改革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重建信任的結論。 要改變危險的臨界狀態,只有依賴信任的重建,賦予數目字以價值觀。事固任重道遠,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沒有信任,何談和諧?執政黨及時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無疑頗具遠見,深懷理想。 (作者任職于《南風窗》)
【發表評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