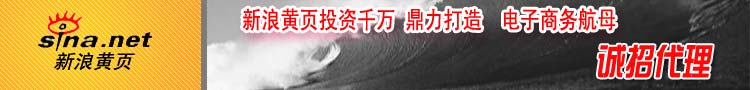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我試圖勾勒的是某種集體人格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1日 22:32 經濟觀察報
唐曉渡/文 1985年2月號《詩刊》頭條刊載了由公木、嚴辰、屠岸、辛笛、魯黎、艾青等18位老詩人聯署的、題為《為詩一呼》的文章。這是他們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為促進新詩走向繁榮而采取的聯合行動。在這篇文章中,老詩人們同時向“各級文藝領導同志”、評論界、出版社和文學刊物發出了吁請,吁請他們注意“胡啟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大會所致的賀詞中”對“包括新詩在內”的“我國社會主義文學有了空前的發展”的肯定,吁請他們(“重要的是各級文藝領導同志”)“應該重視新詩,要給予真正的關懷和實際的支持,要通過各種途徑和采取各種方法,推動新詩的發展。”吁請的背后是不滿,不滿的背后是擔憂,擔憂的背后是正在悄悄興起的商業化大潮,是各種勢必導致詩歌的社會文化地位急劇下降的無意識力量的合流。老詩人們關愛新詩事業的拳拳之心確實令人動容,問題在于,這種“為民請命”式的呼吁將如何落到實處?它所訴諸的良知或悲懷是否能反過來成為其有效性的保證? 饒有興味的是,于此前后一批更年輕的詩人也在紛紛采取“聯合行動”。這種“聯合行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吁請,吁請詩歌社會更多關注他們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卻是一種回應,回應新詩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率先采取這一行動的是一批四川的校園詩人。他們以寫所謂“莽漢”詩相號召,并自印詩集《怒漢》,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詩歌群落,其主要成員有李亞偉、萬夏、胡冬等。1985年1月,由柏樺、周忠陵主持的民間詩刊《日日新》在成都創刊,同時創刊的民間詩刊還有署名四川省東方研究學會、整體主義研究會主辦的《現代詩內部參考資料》。3月,由《他們》文學社主辦的民間詩刊《他們》在南京創刊,主要成員有韓東、于堅、丁當等。4月,民間詩刊《海上》、《大陸》在上海創刊,主要撰稿人有孟浪、默默、陳東東、郁郁、王寅、陸憶敏、劉漫流等。6月,由燕曉東,尚仲敏主編的《大學生詩報》開辟“大學生詩會”欄,并撰文倡導“大學生詩派”。7月,署名四川省中國當代實驗詩歌研究室主辦的民間詩刊《中國當代實驗詩歌》創刊;同時北京的一批青年詩人成立“圓明園詩社”,并自辦民間詩刊《圓明園》,主要成員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 這種組社團、辦民刊的熱情在其后的兩、三年內有增無減,形成了一定影響的包括:1986年3月,由四川省大學生詩人聯合會主辦的《中國當代詩歌》推出所謂繼“朦朧詩”之后的“第二次浪潮”;5月,署名四川省青年詩人協會現代文學信息室主辦的民間詩刊《非非》創刊,主要成員有周倫佑、藍馬、楊黎等;稍后,《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在四川創刊,主要成員為石光華、宋渠、宋煒等;又稍后,黃翔等在貴州發起“中國詩歌天體星團”,并印行同名詩報;1987年3月,由廖亦武執編的民間詩歌出版物《巴蜀現代詩群》印行;5月,由孫文波等主持的民間詩刊《紅旗》在四川成都創刊,由嚴力主持的《一行》詩刊同時在美國創刊;1988年7月,由芒克、楊煉、唐曉渡發起,北京一批青年詩人成立“幸存者詩歌俱樂部”,并自印民間詩刊《幸存者》;9月,首倡“知識分子精神”的民間詩刊《傾向》創刊,主要成員有西川、歐陽江河、陳東東等;11月,民間詩刊《北回歸線》在杭州創刊,主要成員有梁曉明、耿占春、劉翔等。 回首那一時期的民間詩壇,真可謂風起云涌,眾聲喧嘩。這既是在壓抑機制下長期積累的詩歌應力的一次大爆發,也是當代詩歌的自身活力和能量的一次大開放,一場不折不扣的巴赫金所說的“語言狂歡”。如果說其規模、聲勢、話語和行為方式都很像是對“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滑稽摹仿的話,那么不應忘記,其無可爭議的自發和多樣性也構成了與前者的根本區別。或許,說這是一場中國式的達達主義運動更加合適。它在歷史的上下文中恰好與前不久那場“清污”運動形成了反諷,并使“指導者”們控制局面、收復“失地”的愿望完全落空。形勢變得越來越像W·葉芝在《基督重臨》一詩中曾寫到的那樣: 在向外擴張的旋體上旋轉啊旋轉, 獵鷹同再聽不見主人的呼喚,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處彌漫著一片混亂…… 運動的高潮是1986年10月由《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主辦的“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據統計,共有84個民間詩歌群體(人數最少的只有一個——詩歌中真正的極大值)參加了先后分兩期刊載的展出。當然數量不足以說明任何問題,就像嘗試借用商業方式運作(包括運動中提出來的那些針對“朦朧詩”的策略性口號)以推廣詩歌盡管稱得上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意,但并沒有給這場運動額外增添什么光彩一樣。這場運動的最大成果,在于使“朦朧詩”之后一直醞釀著的二次變構表面化了。新一代詩人自我確認式的介入表明,多元化已不可逆轉地成為當代詩歌的基本價值取向,尋求自律的詩正越來越成為它自己的意識形態,而這同時意味著其可能性在生命/語言界面上更廣闊、更深入的探索和拓展。由于運動,“第三代詩人”或“第三代詩”成了風行一時、臧否激烈的談資,進而成為批評家和教授們的研究課題。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集體命名或批評術語的最初版權,竟應歸屬于毛澤東和當年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我所目睹的有關這場運動最令人感動,也最戲劇化的一幕發生在《詩刊》辦公室。當時我正在看稿。一勁男一靚女滿面風塵,合拎著一個大旅行袋,像冒出來似地突然出現在身后。未等我開口詢問,他們已從旅行袋中取出一面卷著的旗幟,“呼”地一下展開。旗幟大約有近兩米長,半米寬,紫平絨作底,鑲著金黃的流蘇,上面赫然一行亦魏亦楷、遒勁沉雄的大字也是金黃的,寫的是“中國詩歌天體星團”。我一時驚詫,口中訥訥, 卻又見他們收起旗幟,復從旅行袋中取出沉沉的一卷紙,在地上“啪”地打開。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疊鉛印的詩報,刊頭處亦題著“中國詩歌天體星團”,與旗幟上的顯是出于一人之手。此時但聽那勁男開口道:“我們是貴州的黑豹子,到北京咬人來啦!”這話聽來像是在背事先準備好的臺詞,我不覺“哈”地一下笑出了聲。我說寫詩就寫詩吧,怎么還要咬人啊。這兩人卻不笑,仍是一臉莊重,也許是緊張。交談之下,勁男說他姓王,本來身患重病,在醫院躺著,差不多已被醫生判了死刑。但一聽說要來北京,陡地渾身是勁,瞞著醫生爬窗戶,從醫院直接上了火車。“我太熱愛詩了”,他攥了攥拳頭:“只要是為詩做事,豁出命來我也干。”我無法不相信他的故事,無法不為之嘆息。最后他指著地下的詩報說:“這是我們自己籌款印的,想送給詩刊社的老師每人一份。如果愿意,就給一塊錢的工本費,不給也不要緊。”我還能說什么?趕緊掏錢買了五份。我記得那是1986年初冬。 隔著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濾網,當然不能指望《詩刊》會對那些正在民間的廣闊原野上馳騁嘶鳴的詩歌黑馬作出直接回應;但既是生活在同一片時代的天空下,它自也會有自己的機遇和崢嶸。在這里工作的,畢竟大多是第一流且經驗豐富的編輯。他們的敏感,他們為詩歌服務的熱情,他們忘我的工作精神,使《詩刊》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失去過重心。 吳家瑾,頭腦無比清醒、心思極為縝密、永不知疲倦為何物的編輯部主任。任何時候你去她的辦公室,都會看到她在埋頭伏案。教會學校出身,拉過小提琴,少時即投身革命。在一次話題廣泛的交談中她突然從唯物論的角度說到信仰。她說早年在教會學校時曾請教過一位牧師,怎樣證明上帝的存在?牧師回答:想想電。電看不見,摸不著,但它能使燈炮發光。由此我知道勤勉地工作之于她意味著什么,而她的歷練又為何毫不影響她心態的年輕。她總是謙稱她不懂詩,但正是由于她的慧眼和堅持,金絲燕的《詩的禁欲與奴性的放蕩》一文才得以在《詩刊》1986年12月號發表。在我看來,該文或許是整個80年代見載于《詩刊》的最精采、最有沖擊力的詩學文章。 王燕生,詩歌界公認的“大朋友”,一只地地道道的詩歌駱駝。他的古道熱腸使他們的家門敞向四面八方,使他的桃李遍及江南塞北,也使他曾經英俊的容顏早衰,使他年不及五十便兩鬢飛雪。他一年的發稿量,往往比三個人加起來還要多。但他對《詩刊》的最大貢獻,恐怕還得算從1981年起,連續組織、主持了十余期原則上每年一屆的“青春詩會”,后者在許多年輕人的心目中,無異當代的“詩歌黃埔”。把他和朋友們聯系在一起的不但是詩,還有酒;而推杯換盞中和酒香一起彌漫的,不但是友情,是逸興,還有難得一抒的憂思和不平之氣。我不會忘記1987年冬某日,為了王若水、吳祖光、劉賓雁等被開除出黨,他下班后將我這個群眾拽至家中飲談。那次我們差不多喝掉了整整三瓶白酒,其結果是第二天起床后不得不花十分鐘找他的鞋。 雷霆,自稱“快樂的大頭兵”。我從未問過他這么說時心中是否想著帥克,但假如我真這么問,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確實,在經受了太多的欺瞞和挫敗之后,還有什么能比保有帥克式的自嘲、帥克式的機警、帥克式的幽默更值得成為一個當代知識分子的快樂之源?問題在于真要修煉到帥克式的境界決非易事,因此我寧愿認為他的快樂更多地來自他的淡泊和自我安妥。他堅持按自己的時間表和節奏安排工作,毫不在意這樣的我行我素對管理體制意味著什么。如果湊巧聽到了批評,他會伴以無辜的表情一笑了之。“你不能照著某種固定的程序寫詩,因此也沒有必要當一個小公務員式的詩歌編輯”,私下里他曾對我傳授道:“他們總是盯著我上班遲到,卻看不到我差不多天天都最晚回家,更甭說業余投入的大量時間了。我不會和誰計較,關鍵在于”,他按了按胸口:“咱對得起良心。” 熱烈而自持,放達而勤懇,胸有丘壑而又恪盡職守——如此的評價并非適用于其時《詩刊》的每一個編輯,我試圖勾勒的是某種集體人格(當然是它的“正面”)。正是依靠這樣的集體人格,《詩刊》同仁們群策群力。于1984年下半年,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辦起了“詩刊社全國青年詩歌刊授學院”及院刊《未名詩人》,以一方面吸引更多的青年讀者,應對相繼創建的眾多兄弟詩歌報刊的競爭局面,一方面適應逐漸增強的商業大潮的沖擊,改善日見窘迫的財政收支狀況(與此同時還創辦了一份內部發行的《〈詩刊〉通訊》,那是我到《詩刊》后獨當一面負責的第一個項目);也正是依靠這樣的集體人格,在隨后鄒荻帆先生因病住院、邵燕祥先生堅決請辭,事實上無人主持視事的一段時間里,《詩刊》的日常工作照舊有條不紊地進行,基本未受影響。就我個人而言,我很樂意分享這種集體人格,猶如朋友們的詩所帶來的震撼,總是被我視為不斷擺脫詩歌蒙昧狀態的自身努力的一部分。寫到這里我能感到一股微溫從心頭直傳到指尖,但我知道這和時間的魔術或中年的感傷無關。確實,80年代《詩刊》的工作和人際關系之于我遠較90年代值得憶念;它還沒有,或者說還來不及變得像后來那樣冷漠,那樣勢利,那樣雇傭化,那樣在兩眼向上的政客和文牘主義的官僚作風的窒息下麻木不仁,散發著某種令人感到屈辱的腐敗和慢性中毒的氣味。 隨著“大氣候”經歷了周期性的震蕩后又一次擺向寬松,《詩刊》也開始再度舒展它的腰肢。“詩歌政協”式的“拼盤”風格仍然是免不了的,但變化也甚為明顯,這就是以前瞻的目光進一步敞向青年。1984年第8期《詩刊》非同尋常地以頭條發表了邵燕祥的長詩《中國,怎樣面對挑戰》。在這首以深重的憂患意識(“危險,/不在天外的烏云,/而在蕭墻之內”)為背景的詩中,“五十年代的青春”和“八十年代的青春”形成了一種錯綜的對話,從而共同凸現出“新鮮的歲月快來吧”這一未來向度上的呼喚。應該說,邵燕祥的呼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詩刊》大多同仁的心聲(就像他傳達“重慶詩會精神”時陰云密布的表情匯聚著同一的“痛徹肝腸的戰栗”一樣)。隨后《詩刊》的一系列舉措顯然都和更多地面向青年讀者,致力于拓展自己的“新鮮歲月”有關,包括第10期的“無名詩人作品專號”,1985年第4、7兩期的“八十年代外國詩特輯”、第5期的“青年詩頁”、第8期的“朗誦詩特輯”、第9期的“外國愛情詩特輯”等。尤其是新辟的“無名詩人專號”,作為每年第10期的特色欄目,在此后數年內備受歡迎和關注,事實上和年度的“青春詩會”及刊授學院改稿會一起,構成《詩刊》不同梯次作者的“戰略后備”。 同樣,密切與詩歌現實關系的舉措也體現于批評方面。1985年6月號發表了謝冕評《詩刊》歷屆“青春詩會”的詩人新作,兼論現階段青年詩的長文《中國的青春》,可以被視為一個明確的信號。緊接著,7月2-4日,編輯部邀請部分在京的詩歌學者、評論家舉行座談會,就當代新詩發展的現狀和可能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會議尖銳觸及了新詩批評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若干問題:以“葉公好龍”的態度對待“雙百”方針,不能形成正常的批評風氣;部分論者知識老化,方法陳舊,對新的創作現象缺乏基本的敏感和了解;對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詩人,尤其是青年詩人缺乏重視;青年一代從事詩歌批評和研究的不多,有后繼乏人之虞等等。隨之,11、12月號《詩刊》又連續推出“詩歌研究方法筆談”特輯,以期從方法論的角度,把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引向深入。1986年1月號更前所未有——此后迄今也再沒有過——地推出了“青春詩論”特輯,使一段時間以來業已初具規模的不同詩歌觀念的交響,突然奏出了一個E弦上的華彩樂段。 有足夠的理由把這一時期稱為《詩刊》的自我變革期。這種自我變革同時涉及其互為表里、不可分割而又有極大彈性和張力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作協機關刊物,它更堅定、更熱烈地維護其與黨內外堅持改革開放的進步力量相一致的原則立場;另一方面,作為為詩歌服務的刊物,它試圖更多地立足詩歌自身的要求而成為文化和意識形態變革的一部分。和同一時期某些風格上較為激進的兄弟刊物,例如《中國》相比,它的美學趣味仍未能擺脫“廟堂”的局限(《中國》因相繼刊發一系列“新生代”的先鋒詩歌作品,尤其是1986年10月號推出“巴蜀現代詩群”而被勒令改刊。同年12月號《中國》印行“終刊號”以示抗議);然而,和它歷來的面貌和心志相比,它卻從未顯得如此年輕,如此放松,如此主動,如此煥發著內在的生機。這里,“更多地敞向青年”決不僅僅是一個姿態調整的問題,它同時意味著更多地敞向詩的活力源頭,敞向詩的自由和多元本質,敞向其不是受制于某些人的偏狹意志,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無限廣闊性的、不可預設的前景。 這種勢頭并未因為1986年春社領導班子的變更而稍有阻滯,而是為其接續并得到了進一步強化。關于這一點,在聽了新任主編張志民先生至為簡樸的“就任演說”后大家心里就有了譜。正如后來為實踐所證明的那樣,他的方略是“無為而治”,換作當時流行的管理術語就是:最大程度地發揮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他把自己的就職會定名為“談心會”,是在以一種最沒有個性的方式來表達個性,最見不出智慧的方式來呈現智慧。他說:“《詩刊》是大家的刊物。大家的刊物大家來辦。‘大家’不是抽象的,具體講,可叫作兩個‘大家’。一是全國詩歌界及廣大讀者的‘大家’,一是《詩刊》編輯部的‘大家’。”另一位新任主編楊子敏先生接茬兒發揮:“兩個‘大家’的提法很親切。兩個‘大家’融洽、和諧,息息相通,就會為雙百方針的進一步貫徹實行創造更加適宜的環境,我們的刊物也就會更加生機勃勃,多彩多姿。”有關會議的側記熱情洋溢地寫道:“談心會開得十分活躍!人人爭相發言,爭相插話,有回顧,有展望,有對刊物工作的具體設計,有對未來的暢想,會議進行了整整一天,充滿了民主、開放、生動、活潑的氣氛。”作為與會者之一我認為這并沒有夸張。那時我們——包括兩位主編在內——全然沒有想到,數年后寬慈仁厚的張志民先生會一方面被指為“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軟弱無力”,另一方面被指為與副主編劉湛秋一起,合力“架空”了楊子敏。 由劉湛秋接任副主編據說頗費了一番考量功夫,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這位黝黑精瘦的小個子頭腦靈活,精力充沛,盡管遇事喜歡一驚一乍,但確實干勁十足。接手主持《詩刊》日常工作后,他很快就顯示出了他的策劃才能:從版式到人事,從卷首語到新欄目。作為詩人,他倡行并耽溺于所謂“軟詩歌”(從前蘇聯的“悄聲細語派”化出);然而作為刊物主管,他的工作作風并不軟,充其量有點心不在焉。他最大的長處是使權力欲和工作熱情混而不分。他上任后的“亮相”文字題為《詩歌界要進一步創造寬松氣氛》,而他也確實真心誠意地喜歡寬松;只有在感到難以應對的情況下,他才把挑戰視為一種威脅,這時他會表現得神經質,在感傷和激憤之間跳來跳去。不管怎么說,他主事后沒有多長時間,《詩刊》就呈現出某種新的氣象,其最大膽也最出色的舉措包括在1986年7、9月號分別刊出了兩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詩,在9月號選發了翟永明的組詩《女人》,以及通過當年“青春詩會”人選的遴定,在相當程度上引進了先鋒詩界的活力。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發表評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