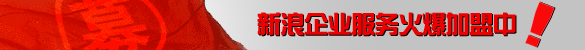崔衛平:我意圖理解這個難以理解的世界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6月25日 17:06 經濟觀察報 | |||||||||
|
本報特約記者 王小魯/文 公共發言的能力和道德 采訪崔衛平教授,并沒有太大難度,因為平時與她也多有交流。但是她前段時間身體不適,到密云青山綠水間的家里休養了。近年來她似乎越來越注重生活的品質。關注學者學
上半年,中國文化界發生了思想界與文學界互相“炮轟”,崔也置身其中。但報紙報道的關于崔的觀點,與她平時素來堅持的相反,而有的作家也據此批評崔,于是又展開了一次缺乏建設性的爭吵。經過了這么多年的發言訓練,為什么精英們的交流仍然如此劣質? 交流與公共空間的良性建設,一直是崔努力的目標。在當下,人們或多或少都有交流的障礙。在采訪她的過程中,筆者的表達出了問題,她說:“我發現你的表達不如寫作流暢,不過,我有時候也這樣。”她說在北京電影學院上課時,學生都不喜歡發言。“我對他們說,你們發言不是對我負責,而是對整個空間負責。” 不愿發言乃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現象,小時候老師鼓勵你發言,其實只是鼓勵某種特定發言,因為普遍輿論與公眾精神的真正激發,常讓部分老師難以控制。到后來,即使學生們有發言的熱情,也沒了發言能力。學生帶著缺陷走入社會,給予社會以先天的不足。在國家壓力下的社會空間尚未發展起來的時候,加強公共空間的建設是此時代的重要命題,也因此,社會需要一種發言的訓練,需要有表率力量的個體出現。 崔衛平正在努力起著表率的作用。她近年來在公共媒體頻繁發表文章,以至有朋友說“崔衛平簡直是在母儀天下”。我問她最近這些年的發言,是不是受到了哈貝馬斯和漢娜·阿倫特公共空間理論的激勵?她說,肯定有這個因素在,但我面對的是具體情境中的具體問題。 公共交流和公共空間是近來使用率頗高的詞。在二戰與納粹之后,哈貝馬斯和漢娜·阿倫特等學者更加注意探討公共交流的重要性。他們倡導人與人的交往和互動,包括不同學科間的交流,比如說藝術意志需要與社會意志相溝通,這一現象的出現乃是基于這樣的理解:世界性的或者國家內的災難是由于交流不充分,公共空間缺乏建設。他們甚至認為,不會交流的孤獨個體乃是極權的基礎性力量。這個觀點,也是崔在不同的場合不停地強調的。崔衛平喜歡阿倫特,她這幾年的學術工作也受益于阿倫特,比如她引進的東歐的一些資源,正是順著阿倫特這個藤蔓摸過去,尋找到的。 “私人生活的起點,就是維持一個人的基本生存,當人僅僅屈服于身體的需要、當他的生活僅僅是圍繞物質必需品、圍繞某種‘必然性’開展時,這個人是不自由的。阿倫特指出,在古代希臘,‘private life’本身就包含了一種被剝奪的性質,它被剝奪了參與世界事務權利。而如果把與他人共同的世界看做意義的來源,那么,沉陷于私人性中的存在則是荒蕪空洞的。” 尤其是1980年代后,我們曾有稱頌孤獨的潮流,而崔的這個說法,卻將人置于一種需要社會合作的壓力下,僅此一點,她就區別于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自由主義作家。崔渴望優質的交流,她的榜樣是山姆佐德,《一千零一夜》里那個以講故事阻止國王暴力的小女孩: “我覺得世界需要表述,表述就是理解,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是無法忍受的,我們不知道這個地方跟那個地方有什么關系。整個世界不能理解,那就是完全荒蕪的。山姆佐德在講故事,敘事就是意味著意義,她的故事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哪些說得長一點,要敘述哪些場景,放棄哪些場景,這些就是她的立場。所以意義就是通過講述來實現的,這里是尋求一種對于世界的理解。” 經驗主義的,女性的,貼身的 崔衛平以前是搞美學的,但她超越了專家身份,幾乎針對社會整體進行發言。這就有難度,我認為她克服這個難度的主要辦法,就是從經驗出發,不停地回到生命原點,以此為據點考察一切。有生命細節做支撐,發言就不空洞。“學術的非學術的起點”、“政治的非政治學的起點”,這都是她大力提倡的。 崔衛平在北京電影學院講課,許多學生似懂非懂,但還是不停地被吸引,許多外系甚至外校的學生前來蹭課。她的課有特殊的力量,她往往從某件發生于我們身邊的小事講起,一步步向上引領,最后到達一個理論平臺,日常的生活細節經過一番分析,忽然得到升華,獲得了意義,這是奇妙的體驗。“風起于青蘋之末”,這樣的講課方式是經驗主義的、反概念先行的。她的寫作風格也是平易的,文章里沒有意識形態或各種主義的對抗,所以這樣的學者無法以“左”或“右”來定性命名。 “顧準有一本書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他的終點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其實走到經驗主義是一個漫長過程,因為我們最早接受的教育都是從概念出發,我現在盡量要求自己每說一句話,都有經驗的成分。其實概念是容易的,我每次上課都幫學生分析作業,發現他們喜歡用大概念,后來我就說,這樣吧,你們寫理論文章都帶稈小秤,每個概念看看你能不能拎動,拎不動就別拎,這些概念要和你的身高體重有個合適的比例。” 這就是她的說話風格,她經常在課堂上做一些生活化的比喻。比如她很喜歡講“現代性”、“現代主義”,她說,現代以后,一切都不再是根深蒂固的了,“就好像一種小白菜,你種在地里長不大,必須在它生長到一定階段后給它挪個地方,它才能長大。”現代之后,世界已經沒有什么堅固的、無須懷疑的東西,一切都必須接受再檢驗。 生活化、經驗、感性直觀,這些詞似乎與女性更有親和力。西美爾認為女性更傾向于獻身于日常要求,更關注個人生活的感性品質,而這也許恰好可以解釋崔衛平為什么會稟有那樣獨特的思考方式,比如她提倡“政治應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如此說來,女性身份在崔的寫作中是有意義的,但她承認這一點嗎?女性主義運動如今已經發展出了繁復的層次,有的女性主義者認為不要過分強調女性性別身份,而有的則認為必須強調。崔衛平早期的文章中也曾經涉及類似問題,但她認為這個時代不僅僅女性權利有缺失,男性權利也有缺失,雖然她似乎也承認女性有自己獨特的權利狀況。從這里來看,也許可以冒昧說一句,崔衛平是有母性光輝的。也許崔不喜歡這樣的話,因為把“母親作為女性惟一有價值的身份”是很有男權色彩的。 崔向我坦言自己的寫作與女性身份的關系,“比如我對于歷史上的大人物不感興趣,那是少數族類,他們把大部分人包括普通人和婦女都排除在外,大人物的經驗不是我們的經驗。我最近寫文章批評張藝謀拍《秦始皇》,里面說秦始皇為開創偉業喪失了一些人性的東西。我認為,你不能在殺我頭的時候,我還在替他著想。政治的話題,在中國很可能是變成一個大人物們的話題,談到政治,就是治理國家了,就民族前途了,然后自己一下子成為重要人物了,這樣的政治根本沒把普通人放進去,當然政治是需要設計制度的,但是作為一個幾千年被排除在歷史外的女性的立場,我就會想到政治的起點,不管怎么設計,都起碼不能與人類生活為敵。我們生活中有的東西,政治中才能有,經驗中有的東西,制度中才能有。假如脫離生活經驗來設計一套東西,就不太靠譜。” 崔衛平雖然反對精英嘴臉,但她并沒有沉浸在自己的私生活中,而是做了更多承擔。只是她不說大話,在兢兢業業地為時代裁縫一件貼身的理論衣服。她說:“可以稱之為思想家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考慮的是思維活動如何與這個世界相匹配。”“要談論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二手的理論上,完全忽視自己周圍有名有姓的鄰居們的存在和他們對于生活的實際感受。” 為什么要關注文化與道德 崔一直致力于引進東歐思想資源,從最早翻譯《布拉格精神》,到后來翻譯哈維爾和米奇尼克。其實崔在很久以前關注問題的向度,與哈維爾的寫作是相像的。她本身是搞文學評論的,后來涉及到政治哲學,而進入問題的角度也多是道德的和文化的。哈維爾以前則是戲劇家,在成為政治家之后仍然有藝術家思維,而且他否認自己是政治家。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文化批評在中國受歧視,道德性呼吁更讓制度學者反感,這當然有中國獨特的語境。這個獨特語境的特點是,許多詞語都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扭曲,不復是本意,而反對者其實也不一定反對那個詞本身的所指,而是反對詞義在特定氛圍中的扭曲,這個反對也都是策略性的,因此目前的交流困難重重,因為發生了語言的混亂。文化與道德,就曾受到曲解,其實我們不能因為一些詞語的歷史性污染,而忽略了那個詞所指的問題本身。“文化太重要了!”崔衛平說。崔后來翻譯哈維爾等人,我想一定是有所揀選,有良苦用心的。 崔衛平說知識分子要盡情享樂,這話聽來刺耳,但我們該從善意的角度理解,她說,知識分子往往企望社會大事件,而不愿意過平常生活,這使他們無法理解過平常生活的普通人,也就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要求,而只顧自己的道德感和對豪壯場面的需要。“一個人如果不生活,沒有自己的生活他就不知道別人有生活的要求,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別人的生活。苦出身的人總愛將一些東西稱之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情調’,再三看不慣,一有可能就要加以扼殺。這不能不說是真誠的。因為他們沒有體驗過不知道它們對于造成人的美好的精神狀態所產生的作用。這就像一個有自己個性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個性,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自由思想。他自己經驗中沒有的東西往往也不習慣別人有。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知識分子思想要更解放一點,腳步要更快一些,盡量發展自己的生活,盡情享受一切美妙的東西。” 崔將日常生活的建立看得很重要,而文化批評是可以幫助我們建立這種生活的。日常生活中,道德判斷和文化品位無處不在,她打擊了某些知識分子的妄想,其實并不排斥每個個體精神性的建立。哈維爾為他所在的捷克社會所開的處方是道德性的:不講假話,活在真實中。這不是宏大的制度建設,而是一個細微的道德要求,為什么要這樣做?譬如一個工廠出了問題,我們知道問題何在,也知道解決此問題的科學方案,但把方案拿過去,卻并不一定得到實行。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并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了其他東西,比如缺道德。而在這個方案未實行之前,人們往往變成犬儒主義者,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這個方案的不實行上去。而在哈維爾那里,他看到了這個僵化的空間中尚有可作為的地方,那地方就在于日常生活的點滴中,但它需要個人的道德做配合,這樣的熱情使每個人都有了價值,每個日常行為都有了意義。 最后,讀崔的文章后我有個疑問:“讀你的文章惟一不滿足的地方,在于對于超驗的維度缺乏探討”。在制度建設和社會層面上,也許需要經驗主義,但對于文學或者個人精神生活,超驗維度不能說是完全虛妄的。與那場“炮轟”中對崔的報道恰好相反,崔一直反對文學之社會功能的過分夸張,而其實她對于文學之個人精神性的撫慰和宗教性的價值也很少探討,英美新批評把文學主要看作技術。而崔在《論道德》一文中則說:“道德問題存在于這樣一個前提上——我們意愿呵護自己。”沒有一個更可靠的絕對的根基,似乎道德很難走得更遠,而哈維爾似乎是認可超驗的存在的。崔衛平是這樣回答我的上述疑問的:“我很理解哈維爾在最絕望的時候,說什么東西都會被記下來,什么東西都不會被遺忘。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可能會有這樣的信念,我其實能夠領略那個東西的美,但是,我還是不使用這個維度,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是很東方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評論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務器幫你賺錢 |
| 21世紀狂賺錢--絕招 |
| 韓國親子裝,新生財富 |
| 1000元小店狂賺錢 |
| 39健康網=健康金礦 |
| 一萬元投入 月賺十萬 |
| 18歲少女開店狂賺! |
| 99個精品項目(賺)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緩 |
| 夏治哮喘氣管炎好時機 |
| 痛風治療新突破(圖)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療法 |
| 高血壓!有了新發現!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