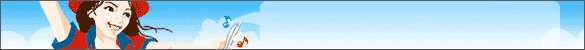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趙武平
一個間接有過交往的老者故去當(dāng)夜,眼看就要十二點的時候,在廣州編畫報而久疏聯(lián)絡(luò)的朋友忽然來電,詢問可否涂抹幾筆以作紀(jì)念,——早先在光明日報大樓五層鄰著圖書館的編輯部濫充編戶之民那幾年,對面而坐的同事與老先生常有往還,故而他慨然惠賜的散文篇什,以及自題簽名的新書毛邊本,我也有幸得以先睹,甚至收藏。出于世道嫌他文風(fēng)散
漫的訾議雖偶有聲聞,卻不能稍減我平素所懷好感和好奇,況且還有熟識他的友人說過,老人不僅曾經(jīng)受業(yè)“死于臺灣的錢穆先生”,而且也與其舊北大師輩知堂先生私人交誼深厚;他寓中盡歷劫難而仍庋藏多多的周氏雜著,“凡是刊印過的,由早年的《俠女奴》《玉蟲緣》等,到最近的《知堂雜詩抄》和《知堂集外文》止,我差不多都有”,更是我輩周迷心動彌久的至寶。
有一年古吳軒藏書家王君自姑蘇抵京,相約分頭前趨往訪老先生于其城外新居。待我從櫻花西街出發(fā),緊趕慢趕沖到說好碰頭的地方,性急而先行的來客已從老人寓所辭別而出。彼時他已逾八五之壽,貿(mào)然登門再加叨擾總嫌不妥,索性過門不入。因緣不到對面不識,大約就是說的這個意思。以后,也在熱鬧場合望他袖手無言端坐,還曾托人求他為一部付印前的文稿題簽,但始終無緣與他當(dāng)面晤談。
流年似水,一轉(zhuǎn)眼人作古了,不到的因緣永遠(yuǎn)不會到了。但因其逝而起的諸般耳食之言,卻難免牽人想起他縷述前塵影事,坦蕩不避自己和革命女作家的情怨糾纏。他淡然談往憶舊的姿態(tài),遠(yuǎn)遠(yuǎn)超出旁人揣度:小說歸屬子部,情節(jié)大小皆可編可造,無須當(dāng)真而言。浪漫主義的紅色經(jīng)典,在他眼中似乎若有若無;直面物是人非,他無怨無悔,更無憎。當(dāng)然誰也無法證明,看客的強行附會,給他帶有愁郁乃至煩擾究竟有多少,——晚年才與之結(jié)識的某公嘗言,開始接觸的時候,“我一直有顧忌,因為他是余永澤,他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對余永澤,我是瞧不起的,對他我也保持著距離,我怕跟他接觸會被人說什么壞話,那時我還是《讀書》的負(fù)責(zé)人。”更有著名話劇院主事者透露,同名電影中余永澤的飾演人選,投拍前非取身材相貌都似人物原型的于是之不可。如此而為目的何在,以及能否以之旁證小說家言是否屬實,自然可以推而想之。
并非虛構(gòu)的小說丑角,和他本人干系究竟多大,徒然空想并無所得;盡管兩人當(dāng)有重疊身影,實乃不爭事實。前年偶然徘徊舊書店,意外檢出小說家在“做老祖母的年齡”那年所公開的日記,方才看見她似乎還是心存惻隱的。她說:“當(dāng)年我的愛人玄,本來他非常愛我。當(dāng)我向往革命,當(dāng)他不能和我一同走上革命道路時,我終于毅然離開了他。當(dāng)我們分開后,又一次我去看他,他變得骨瘦如柴,坐在一張佛像下,流著眼淚,拉著我的手說:‘默,回來吧!我們還在一起吧!……我不能——不能沒有你呵!……’他那絕望的面容,他那悲傷的眼淚,使我心如刀割,使我?guī)缀鮿訐u了……他畢竟是我一生中初戀的愛人啊!我們已經(jīng)共同生活了幾年,他在文學(xué)上有修養(yǎng),我們完全可以在一起過著安逸、平靜、充滿愛情的生活;我們可以‘紅袖添香夜讀書’;可以毫無風(fēng)險地共同翱翔在浩瀚的、各種各樣引人入勝的圖書中……然而,我要參加共產(chǎn)黨,我要革命的信念,戰(zhàn)勝了纏綿的個人情感。終于,我還是忍心離開了他。他后來對人說過,他幾乎為我死去。但當(dāng)時我又何嘗不痛苦呢?當(dāng)我看到他這樣一個大學(xué)生,竟像老僧般趺坐在佛像下,‘這全是因為我呀!’我忍不住哭了。”然而先他而往泉下的她未必知道,看去心似止水的他,其實也有衷曲欲與人言:“本諸古訓(xùn)‘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今訓(xùn)‘苦悶的象征’,我也想寫小說。因為這種情懷,一是形體恍惚,二是分量太重,都宜于用小說的形式表達(dá),而且要長篇。并已擬定標(biāo)題,先是《中年》,寫定命下的愁苦;后是《皈》,寫終于尋得歸宿。事實是沒有寫。不是沒有能力寫;我自信,有了主旨,正如其他所謂作家,我也會編造。而終于不寫,是因為時移世異,這世有要求,表現(xiàn)手法可以殊途,所表現(xiàn)則必須同歸,山呼萬歲。我的《中年》的愁苦,《皈》的設(shè)想,都與萬歲無關(guān),行祖?zhèn)髅髡鼙I碇溃缓貌荒霉P。”顯然并非不欲抱怨,只是文網(wǎng)密時不能怨;而到了可以暢言的年歲,怨的念想已從心底消逝。詩自他手出,但已無怨。
“天下惟一種刻薄人,善作文字”,仿佛于他卻是例外;所謂以德報怨,更似可以其言行兼作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