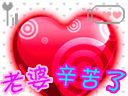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蔣明倬
最近,報(bào)社的同事在人手一本的看《〈華爾街日?qǐng)?bào)〉是如何講故事的》(《華》),我翻了沒幾頁,那種對(duì)于寫作本身剖析的抽絲剝繭的勁頭,讓我想起了作家馬原的一本書——《虛構(gòu)之刀》。
于是又想把馬原的書翻出來重新看,偏偏又找不到了,于是一家一家地打電話到各個(gè)書店去問,只有萬圣書園芳草地店還有這個(gè)書,立刻打車奔這個(gè)書店。
讓人錯(cuò)愕的事情,就在這個(gè)時(shí)候發(fā)生了。萬圣書園為人熟知的是藍(lán)旗營(yíng)的那個(gè)店,我不曾去過芳草地店,據(jù)說是在藍(lán)島附近,司機(jī)找了一陣子找不到。我只好下了車,春節(jié)剛過,天氣仍然冷,在周圍幾條街上來來回回地走了若干次,還是找不到。但忽然發(fā)現(xiàn)旁邊的一個(gè)商店的名字居然是我在遠(yuǎn)方的一個(gè)朋友的名字,而商店旁邊是個(gè)小酒吧,酒吧的名字剛好又是那個(gè)朋友出生的年份。我忽然就覺得這個(gè)氣氛就詭異起來了,如同夢(mèng)魘。找不到出路的焦灼和朋友的溫暖在那一刻是一起涌進(jìn)心里來的,一段時(shí)間以來工作上的無所進(jìn)展和困頓、情感上的愛恨冷暖也一下子就翻涌出來,漾滿了整條街。佇立街頭,整個(gè)人都是虛幻的。
最后只好又電話書店花了很大周折才在一個(gè)偏僻的地方找到了店,拿到那本《虛構(gòu)之刀》。在還沒來得及看的時(shí)候,我被派往山西出差。那是我第一次去山西晉城,長(zhǎng)途車一路顛簸,到處是滾滾煙塵,轟鳴來去的運(yùn)煤車,忽然覺得自己回到了上世紀(jì)七八十年代。我沒有任何小城鎮(zhèn)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在我的想象里,只有上世紀(jì)七八十年代的城市才是那個(gè)樣子,身著暗啞服裝的人們來去在灰土土的街上,小販們?cè)诼短斓牟耸袌?chǎng)叫賣,打蔫的白菜葉胡亂地被丟在大街上……我穿著雪白的羽絨服行色匆匆闖入這個(gè)城市的時(shí)候,如同穿越時(shí)光而來,持續(xù)的仍是那種虛幻的感覺。
夜里,躺在旅店看《虛構(gòu)之刀》“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一章忽然就心有所動(dòng)。有那么一段是講作家的“白日夢(mèng)”,馬原講,當(dāng)一個(gè)人獨(dú)處,尤其是發(fā)現(xiàn)廣大無邊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一個(gè)人的時(shí)候,就容易出現(xiàn)幻覺,即使當(dāng)時(shí)陽光非常的好,視野也非常的清晰。而作家寫作的時(shí)候經(jīng)常是一個(gè)人,就很容易產(chǎn)生很多莫名其妙的念頭或者幻覺來。
而從這點(diǎn)來看,我覺得記者甚至是比作家更容易產(chǎn)生虛幻感的職業(yè),經(jīng)常是一個(gè)人出差到一個(gè)完全陌生的地方,基本瞬間就完成了時(shí)空的棄置;經(jīng)常是在很短的一段時(shí)間里見毫不相干的采訪對(duì)象,他們彼此的身份、氣質(zhì)相差得甚至極為懸殊。一個(gè)記者很可能第一天坐著三輪車去一個(gè)偏遠(yuǎn)農(nóng)村里采訪禽流感,第二天就在國際化的大都市的五星酒店里采訪跨國企業(yè)的老總。這種持續(xù)的孤獨(dú)狀態(tài)和不斷急劇轉(zhuǎn)變的時(shí)空都作用在一個(gè)人身上,結(jié)果可能是,同時(shí)承認(rèn)每一種場(chǎng)景的真實(shí)性,但閃回的時(shí)刻里心里的感覺還是那么的不真切,真實(shí)地經(jīng)歷一些事情,在過后看是歷史,當(dāng)時(shí)看,又似乎是在做夢(mèng)。
在接觸事實(shí)片斷出現(xiàn)的時(shí)候,似乎眼睛和耳朵已經(jīng)做了確定,但內(nèi)心里往往又好像永遠(yuǎn)都對(duì)這種“真實(shí)”保持一種警覺,往往是前一刻還以為是真實(shí)的東西,在下一個(gè)時(shí)刻立刻就成為幻影。所有的“事實(shí)”都需要不斷的懷疑和然后再一次的確認(rèn)。在最后的真相背后是無數(shù)幻影的尸骸。接下去在山西的采訪就是這樣的過程。去那是為了調(diào)查一個(gè)環(huán)評(píng)不合格的企業(yè),國家環(huán)保總局提供了企業(yè)的名單,但開始調(diào)查的時(shí)候,卻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馗緵]有叫名單上那個(gè)名字的企業(yè),相似名稱的企業(yè)倒有幾家。這是已經(jīng)通報(bào)全國的違規(guī)事件,當(dāng)我向當(dāng)?shù)厥协h(huán)保局和省環(huán)保局詢問此事,他們聲稱并不知情,當(dāng)我找到這個(gè)企業(yè)的投資方,他們也聲稱并不知情。兩天里,我來往于縣城和化工企業(yè)成堆的小鎮(zhèn),依然如墜夢(mèng)里,所有的事情既是眼見耳聞,又覺得都不那么真實(shí)。
當(dāng)截稿那天的上午,一切才清晰起來,項(xiàng)目本身是國家環(huán)保總局直管,所以當(dāng)?shù)丨h(huán)保部門并不知情,由于企業(yè)本身的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復(fù)雜,集團(tuán)就不知道下面企業(yè)發(fā)生的事情,最后見到企業(yè)老總的時(shí)候,他們整改都已經(jīng)開始。如果說最初我迷惑的是不清晰的事件本身,而當(dāng)一切清晰起來的時(shí)候,我迷惑的是能造成這些困擾的可以繼續(xù)存在的原因。
我用了整個(gè)下午來寫稿子,直到晚上編輯要交版的時(shí)候,都沒有辦法寫出來個(gè)讓自己滿意的東西,根本就覺得無力表達(dá)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沮喪得如同被扔到廢紙簍里的那些皺巴巴的資料,實(shí)際上這種沮喪已經(jīng)困擾我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這也就是我根本不會(huì)放過《〈華爾街日?qǐng)?bào)〉是如何講故事的》、《虛構(gòu)之刀》這樣的寫作技巧之書的原因,對(duì)于布隆代爾或者馬原,我都抱有著很大的好奇心,作為構(gòu)建文字的高手,無論真實(shí)也罷、虛構(gòu)也罷,最終我希望從他們身上獲得的,不過是從心所欲的表達(dá)。如何通過技巧,讓觀感、記憶、內(nèi)心、文字統(tǒng)一起來,可以最終翻云覆雨。
在《華》里布隆代爾提供的是非虛構(gòu)文體里講故事的技巧,而《虛構(gòu)之刀》,馬原一直講述的都是小說的敘事技巧,在相互比照的閱讀中,文體差異帶來的處理技巧的不同是赫然的,但也會(huì)發(fā)現(xiàn)它們可以互相借鑒之處。新聞里,有引語的處理方式,在小說中,有對(duì)白的處理技巧;新聞里,是告訴你吸引人閱讀的因素,小說里告訴你如何設(shè)置懸念。這些技巧實(shí)際上彼此都是有關(guān)聯(lián)性的。
在《華》里,記者說幾乎在所有偉大的故事創(chuàng)意中,都有一種人性的展示。而對(duì)于人性的展示做得最好的部分不是小說么?在小說里,也有《白鯨》這樣的作品,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枯燥的對(duì)于鯨魚的各種資料,然后小說本身的吸引力卻可以支撐讀者讀完它,它所采用的技巧,不值得財(cái)經(jīng)記者們借鑒么?
而最終所有人希望的不過是,寫吧!無論用哪一種技巧,只要能吸引人讀下去,只要文字最終能震撼讀者,如果可以借鑒的技巧為什么不借鑒呢?管他是屬于新聞的還是小說的。
記者或者作家,本質(zhì)不都是觀察者、書寫者么。在作家那里,最終達(dá)到的是虛構(gòu)的真實(shí),盡管憑空想象,但一切又似乎皆可觸摸。在記者這里,也可能最終的結(jié)果是,真相往往夸張、怪誕得都如同虛構(gò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