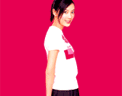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
趙武平
黎明來臨時,寂寞摸到近前,幻聽在耳邊跟著生出,仿佛響起了久違的既脆且雜的鳥鳴;俯望不遠處的浦江云霧,我不禁失神浮想北京的早晨,想起往昔筆耕通宵,起身推窗遠望晨曦的那一瞬,檐下高高的槐樹枝椏間,猛然沖出來的麻雀啁啾——歡快,熱鬧,密集。五年來時有傳聞,說熟稔的老城拆后又建,在變得新異,好似壓根兒未曾謀面。不過惦念
中槐花和鳥雀依然,淡的清香還彌散在半空。但幻想的樂觀,終因一紙飛鴻的抵達而告消逝——梁從誡先生寄來的話語,捎來的有他自己的憂慮,更有我對遠方的失望。他說:“卡森將自己的這本著作起名為《寂靜的春天》,對于普通的美國人來說,在自家的后院里聽不到鳥鳴,是件會使人猛然吃驚的大事。可是請大家回憶一下,我們中國城市居民,看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聽到過鳥鳴呢?對于中國人來說,環境問題已遠遠不止是什么聽不聽見鳥叫,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問題了。”
半年多來,瞥見墨綠封皮的《寂靜的春天》,我就想到梁從誡先生,和他起初猶疑著不肯作序的情形。拉切爾·卡森的書早成中文,也已有綠色政治家阿爾·戈爾長篇導言在先,梁先生覺得自己好像已無贅言必要——誰還不知道這部喚醒人類環保良知的杰作呢?正如戈爾所言,《寂靜的春天》如同《湯姆叔叔的小屋》,都是改變歷史的名著。斯陀夫人給美國南方蓄奴制度畫上句號,卡森開啟了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屈辱時代已與黑人無關,可環保之路仍舊遙遠,并且沒有止境。如果沒有卡森的調查和呼吁,貽害無窮的“滴滴涕“(DDT)也許永遠不會從農田退出,保衛生態的熱心人大概還沒走到一起。可是環境意識普及之后,意想不到的尷尬仍難避免。戈爾說:“我們在國內禁絕了某些殺蟲劑,但我們仍在生產并將其出口到其他國家。”在他看來,現存的社會發展制系,更類似“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以長遠的悲劇的代價,換取眼前的利益”。任何一個地方的食物鏈受害,其實也就是地球上每個地方的食物鏈都遭到破壞。可惜婦孺皆知之理,惟權貴馬頭是瞻的政客,還有貪欲無度的惟利是圖者,大都裝作懵然無知。也許這就是從誡先生雖然惶恐,但還是沒有回絕我,最終出來說話的因由。
從誡先生的序言雖說直率簡當,但讀來卻使人坐臥不寧。他感慨道:“本來,按一般常識來說,后發展國家理應避免走別人已付出過代價的彎路,但是,中國卻重復了,并仍在重復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還是個問題……人類第一次專門為環境問題而舉行的國際大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是《寂靜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1972年召開的。那時中國剛剛恢復聯合國席位,收到了這次會議的邀請。而當時國內的宣傳口徑是:環境問題是資本主義典型的社會弊病,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夠承認也有環境污染問題呢?以致當時中國政府甚至考慮過是否派團出席。”他的同齡者自然會有印象,當年夢想之一曾是:從天安門城樓望下去,要處處都是煙囪。
在濕冷的季節,不大能看得到鬧騰的雀兒;可日前一個老翻譯家的談話,卻勾我記起那不朽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會遠嗎?我期望還會有春鳥歌唱,雖然不知道寒冬何時有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