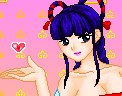|
本報首席評論員 孟雷
歷來的冬天,往往都是英雄歇馬、壯士還鄉的時候。眼見著報業同仁們的來來去去,反而越來越覺得淡然,有的人徹底離開這個行當,更多人來年春天又加入進來,懷抱著“當代史官”憧憬的青年從來都像一茬茬的韭菜。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這樣,因為他們心中有一個“修當代史”的沖動和“道統”。當然,這也是因為現代政治的逐漸昌明,使青年們的憧
憬有了更多實現的可能,三千年“道統”因之續如長河。
在中國,史分官史(正史)與私史。當同一段歷史因“述其正朔”的需要而被“宣付史館”的同時,它往往也會在別處以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闡釋方式呈現出來,這是因為有私史的存在——私史就是當代史。
以我們似乎已熟知的中國史為例,努力記錄著它的變遷的,看來遠不止煌煌一架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雖然當歷史已經消散,承載它的只剩下這些紙頁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置疑這些“官史”或曰“正史”的巨大價值。但是,對于歷史而言,它是否已足夠了呢?朝代的更替,最終使“后朝修前朝之史”成為現實通例,本朝和本朝史官對此往往無能為力。無論他們多想“書祖宗之功業,垂后世以追范”,他們關于“當代史”的記述——譬如皇帝起居注、本朝實錄等等——都只能為“覆我國者修我史”提供參考。歷史之像,總得要假手于人,但它就此已然被“史”這個鏡鑒折射了兩次,光與色的散失偏移自是不待我言。懸案之多多、翻案之涌涌,誰能說可以撇清這個原由呢。
既然當代職業史官修不成當代史,那么就會有別的知識分子來作,作出來的就是——私史,私史的價值就在于它往往直接記錄著當代甚至當時。治私史,這個道統之發軔,起始于充滿著最旺盛入世情懷的第一代公共知識分子——孔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部已被普遍認定是孔子惟一親著作品的史書,成為中國第一部私修的史書。其后這隱然成為一個傳統,雖然歷代政府對知識分子們的這一行為普遍不快,因為以“筆則筆、削則削”的春秋筆法記錄些官史所不載的當代“陰暗面”等等,從孔子就開了頭。比如,南宋政府頒布的政令就指出——“言私史害正道”,就此開了明令嚴禁私人作史的先河;到據后來的史書稱“文字獄最酷烈”的清代,將私刻《明書輯略》的莊廷瓏掘墳戮尸、誅其親族;王緗綺作《湘軍志》,而曾門將帥怒曰可殺,終迫其毀版……
雖然千百年下來,以私自記錄、傳播當代歷史的罪名觸諱取禍者不乏其人。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從來是不缺乏對自身的“公器”期許的,而在以往的傳統社會里,他的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的體現,往往其大莫過于“記史”。把真實的當代歷史記錄下來、傳播開去,正是薪火相傳的“道統”之一。而且,社會越是處在變革與動蕩之際,這種欲望就越強烈。
正是這些非工具(史官)的知識分子出于春秋道統的自發記錄,讓我們的歷史不再“從一而終”,使后世人對它有了多角度參詳、觀察的可能。
政治的逐漸昌明、訊息的發達,催生了新聞報館和以專門記錄當代史為職業的記者這一行當。私史與公器、知識分子道統與社會大眾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有機統一的可能。我們可以看到,就方法論而言,私史著者所柄持的“我之目見耳聞、大眾之親歷身受”,仍是以真實和公心為基本出發點的記者所遵循的職業指歸。而在實踐論的范疇,報館制度和記者行當,為有志于記錄當代史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另一條路徑,在官修與私修之間多少尋求到一種平衡的可能。
雖然這個行當的特性,使他們往往無法潛心一念、有條不紊地記錄所有想記錄的變遷,但就像歷來私史限于條件無法都像《春秋》、《三國志》、《國榷》一樣擁有完善的體例,這并不影響他們因力圖準確地記錄了當代史的種種事件而帶來的價值。那些價值,既是記者的職業要求,又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道統”所系,三千年未斷,今后也會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