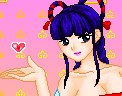食指與林莽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1月07日 18:13 經濟觀察報 | |||||||||
|
張清華/文 食指:“請聽我心中陣陣解凍的心潮” 1998年干冷的初冬,年屆五十的食指回到他闊別多年的老家山東濟寧,在那里度過了他“天命之年”的生日。那場面想必是熱鬧而幸福的;但他必定沒有料到,之后的濟南之行
食指穿著他那身洗得發了白的“學生藍”的滌卡中山裝,登上了一所大學的講臺。掌聲像暴風雨一樣響起來。他立定了之后,人們才看得清楚,他的下身穿的是一條上個年代留下來的卡其布的黃軍褲——一樣是洗褪了顏色的,領子、袖口和褲腳都起了毛邊。特別是那褲子的膝蓋上,大約還有一個“食指”般大小的破洞。沒有人會想象到他的朗誦水準是這樣的高——勝過了所有專業和非專業的人們。因為沒有人能夠像他自己那樣沉著而準確地理解著那些用生命凝成的句子,并準確地表達著那其中的哀痛與憂憤,信念與沉淪。仿佛昔日重來,他再一次地身歷并品味了那漸已遠逝的年華和黯去的韶光。這是完全統一的節奏:出自心靈的語調和速度,同那充滿了屈辱和奮爭的生命的節律完全一致,猶如春蠶吐絲,杜鵑啼血。 食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跨越了歷史裂谷的“在場”,讓世紀末歡樂的孩子們透過時間的遮障,知道了什么是一個歌手的命運,什么是悲劇、生命和詩的真諦,什么是無可回避的抗爭和擔承,什么是深淵上的毀滅和再生,什么是“一次性的生存和寫作”(雅斯貝斯語),不可模仿的天才和無可挽回的代價……至少,他有使我——一個也置身于“現場”的人重新認識詩之意義、重新尋找詩之真諦的無與倫比的分量。 與別的朦朧詩人不同的是,食指在當代詩歌的格局中并不是馬上就顯示出其價值和意義的。盡管早在1979年問世的《今天》第二期上就發表了他的《相信未來》、《命運》和《瘋狗》,在第三期上又發表了他的《魚群三部曲》等代表性的作品,但在很長的時間里,他卻被忽略和漠視了。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但細想來也符合規律,更貼近當代的情形。他是在歷史出現了更大的彎曲和彌合跡象的時候,在一個時代真正行將消逝的時候,才顯出了其特殊性。很明顯,一個迅即被時代認可的詩人總是有可疑之處的,更可能在最終被歷史所忽略和淘汰。誰更能夠切近歷史的真實?誰更能夠完整地記錄下一代人的心路歷程?甚至,誰更能形象地載錄下那種記憶的方式?或者更直接地說,誰會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或者象征?時間將會反過來凸顯這個人獨一無二的價值。人們對于他的忽略,在我看來并不是由于所謂的有否“難度”和是否“現代”,不是因為他的詩中包含了更少所謂“變革”的因素,而是因為人們的精神中必然出現的盲區,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對歷史的失憶”。 一個小詩人的臨場會被世俗誤解為精神病,而一個大詩人的在場則會讓世界感到自己的渺小,讓世俗感到自己的粗鄙和被提升。他現在擁有了這種力量。 “世界是一所牢獄”,丹麥的王子在他身遭不幸的時候曾這樣說,那時他近乎于一個詩人。而我們似乎也可以這樣說,世界就是一座福利院,它正是為我們的詩人所準備。我們的本意是合伙的謀殺,但因為詩人那過于刺眼的光明和我們自己身上的卑瑣,這圖謀最終轉化為迂腐的善意和奴仆的掌聲。所以,我更愿意從哲學的意義上來理解“福利院”和“精神病”這樣的詞語。 詩人注定要穿行其中:世界也許就是這樣“世界化了”(海德格爾語),福利院也因此獲得了意義。因此我們也許注定要“從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看到了這樣一個巨大的背景,在現代以來的哲學史、藝術史和文學史上許多卓越的名字都與精神分裂連在一起,荷爾德林、尼采、愛倫·坡、斯特林堡、凡高、葉賽寧、普拉斯……這本身就構成了偉大的啟示,人類在走向自己的未來的過程中,精神越來越陷入自我的矛盾和分裂之中。顯然,這里有太多的歷史、哲學和審美詩學方面的含義。正是食指的瘋狂反過來映照了他作品中崇高而背債的理想精神,使之具有了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由此變成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死結和聚焦點,和他同時代的人們從那個時代逃脫出來得以幸存,而他卻義無返顧地與這個世界同歸于盡,一起沉淪。他是一個真正面對和生存于自己時代的人,他唱著自己時代的歌,宛若泰坦尼克號上的樂師,臨危不懼,勇敢地投向毀滅的淵藪。 在活著的詩人中,還有誰能夠像食指那樣,可以構成如此復雜豐富的精神現象? 然而詩人終究還是走出了那座福利院。2003年的初夏,我看到了第六期《詩刊·下半月刊》上登出的他的四首新作,同時我還知道了另一個消息:獨居多年的他,已經在2002年3月回到了新安在北京百萬莊的家,在那里他與一位叫做翟寒樂的女士,共同筑起了一座生命之巢。這讓人感到欣慰和慶幸,這飽經磨難的人,終于分享到了可貴的“冬日的陽光”。從他的詩里不難看出,他對自己重回“世俗生活”充滿了欣悅和歸宿感,他甚至有點小心翼翼的依戀了——“可得好好珍惜這暖暖的冬陽/外出走走,享受下這難得的時光/讓陽光曬出的好心情隨鴿群放飛/鴿鈴聲牽帶出心中的笑聲朗朗”(《冬日的陽光——給寒樂》)。不知道這日常生活是否可以醫治詩人心靈的舊傷?他一生所尋求的平衡,也許總算在這暮秋或初冬的日子里,現出了一縷夕照的霞光。 但詩人的使命并未就此終結,“他一生中從未停止過追求……”,我們又看到了一個以尼采自比的食指。他期待著思想的暴風雪,期待著他自己和人世再度的精神撞擊——“沒人能理解他性情的孤僻和高傲/也沒人回答他對世俗的嘲諷”(《啊,尼采》)。他的一半安睡著,另一般卻在黑夜里醒來,睜大了炯炯的目光。 老友林莽訪問了食指。在這篇訪談中,清晰地展現著他的孜孜不倦的思想。關于詩歌和詩學,他提出了自己看法,這幾乎是最原始、最常識的看法,但卻是根本:“理過其辭不是好作品”,這個評價可以說是直擊當代詩歌的命門。他強調“中國氣派”,“中國詩的根不能斷”,這在6年前我就近距離地聽到過,但現在他說的更清楚,“就是要從中國博大深沉的社會創造出一種新的詩歌體。但詩歌要有一種形式,必須研究外國詩和中國結合起來的形式。這很重要,古典加民歌走不通……”他還談到古典詩歌的變革,中外詩學的差異,詩歌翻譯的奧秘,“理學”與“心學”的不同,“天人合一”的境界,等等,可以看出,他是在不間斷的讀和思中來體味的。這狀態甚至使他充滿了激動,仿佛他的藝術生命將要再度重臨一個勃發的春天。 這正是食指生命中根源性的東西,完全的“二元性”:執著與失敗,翱翔與深淵,希望與絕望,悲傷與歡欣……這一切又投射為“寒冬”與“春天”的對立統一,相生相依的形象隱喻,并且最終又化為了詩。這是他既往詩歌寫作的原動力,也是他今天繼續用詩歌來進行他生命探求的精神源泉。因此我們就同時看見了一個徘徊于冬日暴風雪中的瘋狂的尼采,和一個期盼著春之旋律的洶涌著“解凍的心潮”的食指,他們其實是詩人自己同在的兩個影子。 他是不安的,這是詩人的靈魂—— 多少不眠之夜中忍受著疾病的折磨 孤獨冷漠中懷著詩意的憧憬 思想的嬰兒經受了分娩的苦痛 終于喊出了驚天動地的哭聲 尼采,當改變世界的太陽到來之前 滿天迸發閃爍著你思想的火花 快熄滅的燭火燃燒著你最后的激情 尼采啊尼采,讓我們一路同行 他又是堅定的,這是詩人的意志—— 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春風醉醺醺地在原野上奔馳 陽光下純潔的白雪公主 已融日黃土地焦渴的懷抱 隨著藝術家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躍 春光在嘩嘩作響的水面上喧囂 讀著五線譜上神妙的音符 請聽我心中陣陣解凍的心潮…… 林莽: “我渴望在人們心中拋下一片火焰” 風雨吹打著青春的向往 歲月是多么的凄涼 在遺忘過水手的荒島上 我描繪著生命的船 寄托在波濤上傳遞,滾向遙遠的地方…… 好像是白洋淀的風吹出了那張臉,他一點也不像是一個來自北京的人,因為在那張臉上,沒有流溢出這城市獨有的傲慢和自負,有的卻是柔和、質樸,對命運和挫折的默默承擔。所以,我相信是這水泊、這淀子,賦予了他一生對詩歌的熱愛,也注定了他蘆葦般堅韌的性格。一點也不奇怪,幾十年過去了,如今他仍然會時常地放下手里忙著的一切,和老芒克一起想念那里的老鄉們,趕數百里的路程,去和他們一起喝酒敘舊。那不是一時半會兒的沖動,而是一種默契和認同,因為他的心,合著他的青年時代的記憶與夢幻,有一半已留在了那里。 2001年秋,我讀到了他的這首叫做《記憶》的長詩。生命的秋天似乎帶來了過多的敏感訊息,歲月留下的一切,在某個時刻會變的突兀和尖厲起來。這是一首屬于過去、屬于白洋淀的歲月、更屬于此時此刻的詩篇,什么東西在深深地刺激著詩人的心。我總是相信,長詩是一個寫作者不會輕易動用的文體,如果動用,必是有相應分量的東西需要表達。對林莽來說,這應是一個度過了五十歲生命歷程的人,對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一次清理。這一年,芒克五十歲,當年和他一起、而今遠漂海外的根子和多多也都五十歲了,而林莽比他們都還要長上兩歲,一個時代——不,是許多個時代都已結束了,時間迅速地使曾有的一切染上了滄桑的容顏。這正是長詩誕生的時刻。那么多的記憶穿越歲月的塵封,在嘆息和傷感、壯懷與緬想中,再次蕩激起蒼老而依然敏銳的波瀾。 我說不清林莽在這些近年的詩作中,為什么如此頻繁地寫到“秋天”的主題,大約和心態有關系吧,我讀到了某種不易察覺的凄涼。畢竟經歷得太多,詩歌自會漸近于一種“悲鳴”。 然而這也正預示著一種真正的佳境,詩歌本就應遠離嘈雜和輕狂。而林莽正固執地迷戀著他那來自大自然的蒼茫與合鳴,那和秋天與秋水一起蒼老的色澤,秋風一樣深沉的蒼涼。他在徹悟著那水澤:“如今我才知道/白洋淀的秋風為什么那么涼/白洋淀的冬霧為什么那么濃……” 某種意義上,說“白洋淀詩歌”是“今天派”或者“朦朧詩”的精神源頭或者先導,也是毫不過分的。一些回憶文章表明,當年北島和江河等人都數次到白洋淀“以詩會友”,雖然從年齡上北島甚至比芒克還要大上兩歲,但從其作品的成熟期看,卻要明顯地晚于芒克。甚至他還有受到芒克影響的痕跡——比如《結局或開始》中的名句:“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就有從芒克的《太陽落了》的詩句中“化出”的“嫌疑”:“太陽落了,/黑夜爬了上來,/放肆地掠奪……”。芒克的這首詩寫于1973年,而北島的作品要晚了數年。即便是兩者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單從思想的深度看,根子寫于1971年的長詩《三月與末日》以及稍后的《致生活》,比起將近十年以后才問世的大多數朦朧詩作品來,也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精神巔峰。 一切都表明,這個時代的真正的精神中心不在別處,就在白洋淀。 林莽的寫作大約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根據他自己回憶,他是1969年插隊來到白洋淀的。很快地,孤獨與挫折感就使他開始嘗試詩歌寫作,并很自然地與其他寫作者發生了交流碰撞,“他們互相刺激,互相啟發,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文化氣氛。”或許,在所有的“白洋淀詩歌群落”詩人中,林莽并不是最“先鋒”的,但他在1974年寫作的《二十六個音節的回響》,卻足以稱得上是一次富有標志性的精神遠游,一次自我的超越。也是從這一年起,他“開始找到了自己的詩歌之路”,領略到精神獨立的思考與現代性寫作的奧秘。他這樣寫道:“手撰寫著遠古的歷史/大腦永遠在發問/荒謬從哪里誕生,丑惡又如何開始/人類的心靈中,從什么時候起/就反鎖了盜火的巨人……”這分明可以看出,他那時對現實的懷疑、對歷史和人性的求思,已達到了相當自覺的程度。 林莽詩歌的風格是非常“綜合”而又獨特的,這和人的氣質有關系。在我印象里他是一個溫和內斂而習慣于沉思默想的人,所以他的詩歌大約也有著“思想獨語”與“精神漫游”的性質。他或許不是那種具有“命名”氣質的詩人——像根子和北島那樣,有著可以“命名一個時代”的力量——但他的作品卻具有更多心靈性、更鮮明的個人性與抒情氣質,這就使他得以保持了一個詩人最可貴的東西:真誠、純粹,而且相當綜合: 記得童年,鄉野的風質樸而溫和 是母親和土地給了我一顆純潔的心 如今,仙人掌一樣地腫大著 在埋葬著朝圣者的沙灘上 長滿針刺的身軀,迎送著每一顆暴虐的太陽 這里依稀可以看出與根子的《三月與末日》相近的思緒,那個時代他們的確有著相近和共同的主題。但比之根子的決絕和堅硬,它卻是溫婉和深沉的,甚至說它流露著“軟弱”也不無道理。從《二十六個音節的回響》到《記憶》,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它們彌漫于內心世界的獨語和漫游的風格,都穩定地保持著。這可能源于他早年所受到的浪漫派詩歌的影響,讀讀這首寫于1970年的《獨思》,可以從中感受他語言的溫婉與音節的自然,似乎與食指的詩歌也有著異曲同工:“你既要離我遠去了,/為什么還留下那深情的回顧?/汽車的煙塵把車窗遮掩,/像日后那遙迢的路途。//不知是你眼中真有/未曾吐露的隱情?/還是我日后在孤單中/過于多思的緣故?//往日命運的無情驅使,/讓我們在那短暫的日子里,/在異鄉漂泊共度。/誰還有心把熱情傾訴?//不期而至的別離,/橫亙在悲苦的日子里。/從此,我對著那迢迢的天涯,/把青春沉入無夢無醒的云霧。//可我心靈的深處,/輕飛著一只彩蝶。/透過我深切的目光,/它可曾在你的心中飛舞?”這青年時代的作品雖然還透著些稚氣,卻可以讓人從中體察那份感情的純真和美好。 多多曾稱芒克為“自然之子”和“自然詩人”,而在我看來,林莽也有與之相近之處,他也稱得上是自然詩人。在收入了他最早的一批作品的詩集《我流過這片土地》(新華出版社1994)中,有大量吟詠白洋淀的土地和風情的篇章,那里有“正午的陽光”和“深夜的冷雨”,有“孤雁的鳴叫”,有“星光和漁火”……(《心靈的歷程》)無論是歡欣還是凄冷,它們都是這樣質樸無華地被呈現出來。我被這首寫于1969年的《深秋》深深地感動著,這是來自水的年輕的憂傷,但卻是真摯而充滿自然氣息的緬想:“深秋臨冬的湖水,/清澈而寒冷。/淡云深高的天空,/時而傳來孤雁的哀鳴。//隨風搖曳的蘆葦,/低奏著凄涼的樂章。/大雁孤獨的叫聲,/像挽歌一樣凄楚而哀痛。//那哀鳴而疾逝的身影,/掠過蔚藍的天空。/一切都如往的平靜,/留下的只是幾聲嘶啞的哀鳴。”—— 深秋的湖水, 已深沉得碧澄。 深秋里的人啊, 何時穿透這冥思的夢境? 解讀林莽,這無疑是一個入口和“綱”。那帶著悲劇抒情的氣質,為白洋淀所滋養的靈透之氣,還有與生俱來的同在的澄澈與蒼茫,性情深處的哀婉和憂郁,都已恰到好處地露出了苗頭。他的作品由此而具有了靈性和感人的品質,也注定了其某些不變的質地。這仍有似食指,內在精神的沖突形成了寫作的源源不絕的動力,也構成了他的作品的獨有的壯美。我說不清在林莽的內心最隱秘的沖突是什么,但我感動于他這樣的不變的堅韌和執著:“如果在最后的日子里/我能心安理得地/奉獻出我的九十九頁詩選/靈魂的歌聲縈繞著那些美好的瞬間/我渴望在人們心中拋下一片光焰……” 記得在1998年冬天關于食指的研討活動中,我也曾經提出過一個關于當代詩歌的精神源流的問題:人們通常所了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朦朧詩”(指以北島、顧城、舒婷等為代表的),并不是當代詩歌變革的惟一與最初的源頭,這個源頭應該更早。從精神氣脈上講,以北京為核心這一支,應該是以食指為源、以白洋淀詩人群為主體,后來的“今天派”與朦朧詩,不過是這個龐大主體由于特殊的時代原因而顯露出來的一小部分而已。隨著時間的推延,人們對歷史的認識自然會清晰起來。“文學史”中當然要講一個“文本事實”和“影響事實”的問題,沒有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會超過這幾個人的影響,但許多年后歷史自會顯現它本來的軌跡。像《紅樓夢》這樣的作品,也并不是在其誕生之初就立刻產生了“影響”的,而是過了許多年。另一方面,“白洋淀詩歌”在上實際七十年代已的確在相當的范圍內被傳抄,至少對朦朧詩的主要詩人已經產生了精神的影響,這就足以證明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基于對這“被埋沒”的歷史的一種不平,我記得當時自己說得比較“過火”,我說,“白洋淀詩群”應該享有比“朦朧詩人”更高的地位,因為他們在精神上構成了后者的“老師”。林莽馬上給予了一個矯正,他說,不能說是“老師”,兩者是差不多同時開始創作的,年齡也相仿,只是當時芒克、根子和多多他們代表了這個時代的寫作在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罷了。 我立刻意識到了林莽的謙虛和嚴謹。對一個詩人來說,這也是最難得的美德。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評論家)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隨筆砸談 > 正文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做女人事業,賺女人錢 |
| 06年暴利項目揭秘 圖 |
| 網絡招商首次揭秘 |
| 輕輕松松賺大錢 |
| 年薪百萬的財富之路 |
| 360行賺錢驚天內幕 |
| 二折提貨,千元做老板 |
| 2006藥界金礦招商指南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最新療法治結腸炎!! |
| 治氣管炎哮喘重大突破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治高血壓獲重大突破! |
| 高血脂!脂肪肝請留意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6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