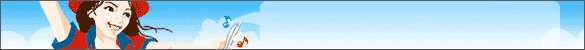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本報記者 孟雷/文
傳染病與我們共處的日子足夠長了,它與我們共同建構著社會生活和歷史。
同時,那些以我們的皮膚、黏膜、肌肉、骨骼、血液、內臟、神經為活動場所的“異類”,也正在建構著它們的歷史,在它們的歷史中,我們則成為歷史的附著物,它們的“變
異”在“異化”著我們,它們是統治者,而我們始終是“人民”。
零星的起義與局部的勝利從來沒有改變過這種格局——作為具體的“人”,我們既附著于“人類”的歷史,又附著于它們的歷史,始終作為“從屬”而存在。把我們和它們的歷史都抽象出來,作為并行的存在來觀察,我們甚至能發現些更微妙的地方:我們一直在供給著它們,豐富著它們。
我們的技術進步、我們的社會結構變化、我們的生活方式變遷,同時都在豐富著它們的歷史,我們在制造一些新的傳染方式或途徑,比如把傳統意義上的“非傳染性疾病”改造成“傳染病”。
在我曾調研過的一個地區,某些村莊里食道癌發病率到了十戶必有的程度,可見其“傳染性”之強,村民也把得了病稱做“誰誰又傳上了”。與此相類的,我們通過我們的行為方式,比如買賣血甚至打針和補牙,使個體的原發性血液疾病成了廣泛的社會性傳染病,而以往醫學史研究上,它們大多只作為以母嬰方式傳播的家族遺傳病存在。
還有更多的例子表明我們在創造更多的傳染病種,比如包括我在內的我的同事們輕或重的信息焦慮癥或抑郁,你不能不承認那就是病理學意義上的“病”,我們姑且就叫它“非病毒性傳染病”,它有一系列的生理、心理表征,而且它的傳播方式和途徑,使它就像“打哈欠也傳染”那樣容易傳染上。
在上述這些傳染過程中,我們既異化成了“生物性”的病毒,又作為傳播“介質”而以“物理化”的形式存在,我們無處不在,就像感冒流行時的空氣。這種徹底異化了的身份屬性,使我們躋身于它們的歷史中,成為它們的一分子。
肉體角色與社會角色
另外的一些觀察能夠讓我們認識到,隨著我們的社會分工、社會角色越來越細密和多重,病理學上的傳染病在成為社會學意義的傳染性社會病時,帶來的不再僅是身體病痛,它同時侵蝕著人群的肉體角色與社會角色,而且更多的在于后者。
當個體患病時,為了社會體系的穩定和正常功能,該人“必須”設法盡可能地恢復到他原來的健康狀態。如果患病的個體不能完成這個預期任務,則不再被認為有能力(或者被允許)扮演他的社會角色,則他就會被確認為是妨礙社會體系正常運轉的“社會的病人”了,這種判斷可能會來自法律、習俗或其他非病患者的“公意”等不同方面。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見解,這種病人角色有幾個特點:一是,“被免除”了正常的社會角色。個體的患病是免除其正常角色活動和社會責任的理由,疾病被認為越嚴重,被免除的活動和責任越多;二是,病人“應該”具有嘗試祛除疾病的愿望。病人應該認識到,因患病而免除正常責任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因此病人有“康復的義務”;三是,病人“應該尋求”技術上適當的“幫助和與醫學合作”。“康復的義務”包括病人有進一步尋求技術上適當幫助的義務。
按照這幾條的判斷,我們就不難理解愛滋病、乙肝病毒攜帶者等病患群體反對歧視、要求權利的行為由來。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上述的幾條幾乎都是“逆向”的要求,是社會對社會組成人員的要求。在這樣的權利義務框架下,作為病患者個體,權利與義務是不對等的,他們的社會權利(責任)被“社會意志”所免除,可以想到的會包括雇傭或被雇傭行為、婚育行為、受教育行為等等,成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而尋求康復的權利,則被“有康復的義務”所替代,在這方面的現實體現,大約都會表現為病人尋求嘗試更多的醫療方式并購買更多種的藥品,這在一個衛生健康法制和醫藥市場監管、醫療服務提供都還很不充分的社會,是需要病患者承擔比較大的健康和經濟風險的。
一個非個案的疾病解析
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傳染病社會中的這個權利與義務現狀,我們有必要抽取某一人群作一個解析。例如乙肝,這種病毒攜帶者在中國大約有1.2億人以上,對這個非個案、非“故事化”的疾病的梳理,有助于我們理解傳染病社會中,病患者群體、政府、醫藥行業在法律、經濟等社會角色中的情況。
一浙江大學周姓畢業生,在當地政府錄用公務員時被拒,因而刺死一名人事干部并致另一人重傷。被拒原因,緣自他是乙肝病毒攜帶者。醫學證明這種肝功正常的攜帶者日常接觸不具有傳染性,但仍被許多地方的體檢標準所排除。占1/10人口的龐大基數、周案前后同因引發的另外諸多惡性犯罪事件、周案引發的“人群”問題——以往各自獨立于社會不同位置的乙肝患者及更大范圍的病毒攜帶者,成為社會學意義上的“人群”,他們共同以“HBVER”自名。諸多要素的集合,使我們不得不把對乙肝的看待由單純的“疾病”調整為“已經存在并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乙肝攜帶使他們無法像其他“人群”一樣,能較容易地行使就業、婚娶等正常社會行為。當某一種病癥,使其罹患者不能自主地、廣泛地被隔離或半隔離于正常社會行為之外,并會因此而引起多種形式的社會連鎖反應,那么,它可以被看作是必須從社會角度去判斷的“社會病”, 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將是長期的、廣泛的。因此我們說,乙肝已成為嚴重的傳染性“社會病”。
罹患人群的多重心態。“人們在歧視我們,我們何不到人群廣眾中去,要吃大餐飯,要擠公共車,要進電影院。甚至對著那些歧視者偏去摸他們的手臉,對他們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就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了!”這是患肝病的賈平凹在他的散文《人病》中的表達,我們可以理解成被強烈的“被排斥感”所左右的思維。在深造無望、就業無路、婚配難合、缺少友愛的前提下,“不平”總會以各種方式體現出來。其作用于個體的反應,顯性的極端惡性的如周案,更多的則體現為賈平凹式或多或少的“怨念”。
政府的社會角色。雖然政府已在1992年將該病列入計劃免疫內容,但它不像天花、霍亂、脊髓灰質炎等疫苗一樣強制接種。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新生兒100%接種了疫苗;但是,縣、鄉一級的情況很不理想,一項調查表明,全國范圍內接種了乙肝疫苗的只占1/3。HBVER普遍認為,其他行業能否消除就業上的歧視,很大程度上將受到政府部門自身用人標準的影響。另外,最普遍限度的注射疫苗,是統籌解決恐慌、解除歧視的根本辦法。至于是采取“強力宣導”,還是“列入計劃”,或者“給予補貼”,無論哪一種方式都必須由國家行政力量來給予推動。
“乙肝問題”中的畸形經濟行為。衛生部數據說,目前乙肝患者僅每年支付的醫療費用一項即達約500億元,而且這僅是指已發病的2000萬患者,尚不包括因“大三陽、小三陽”遭遇就業、婚姻等障礙而四處求醫問藥期盼“完全轉陰”、“徹底治愈”的一億多病毒攜帶者。需求的龐大拉起增長曲線,病患人群在市場條件下成為掘金之地。
從這個以乙肝為樣本的疾病社會學解析中,我們大約可以了解到,狀況正像我們前述所言,“社會病”患者被部分“免除”了正常社會角色,即便他仍擁有履行這些角色的能力,這會由法律、政府行政行為、習俗或其他非病患者的“公意”來裁決,而不是僅憑醫學。在來自社會和個人的多重壓力下,患者會主動履行社會要求他的“康復的義務”,尋求“更好”的治療和藥物,但社會能提供的判斷標準往往只有“新”和“昂貴”。事實上,類似的狀況也同時在愛滋病、血友病等等領域重演。
顯然,在這個世界上,這些病理學意義上的傳染病和由此引發的社會病,以及我們由非傳染性疾病比如癌癥改造出的“傳染病”,還有完全由我們自身創造出的“非病毒性傳染病”比如焦慮癥和抑郁癥,共同構建了越來越多元化的傳染病社會,在我們與它們的角力中,走在前面的眼下仍然是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