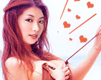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邵穎波
世風日下這個詞,不是用來說某個人、某個群體的良心如何淪喪,只有社會的整體道德底線滑到一定程度才會用到它。遇到惡徒光天化日之下羞辱婦女而四下無人過問,遇到窮困潦倒者撲倒在地而行人腳步匆匆無人施以援手,往往在這時候,人們會慨嘆世風日下。但其實,這種狀況只不過是一次偶然的集體失禮而已,因為依照一些社會學家
的總結,出現這種情況并沒有什么可奇怪的,這是一種特殊的群體心理相互感染所致。如果有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在場,就很容易喚醒周圍麻木的人們,這種局面也會立即煙消云散。
但是,真正的世風日下比這個可怕得多。這時的道德已不再是個人存于內心的約束,而是可以經常拿出來相互比較,這種比較,比的是所謂道德底線,是為求得一絲心理安慰,因此方向總是向下的。在這種不斷地向下尋找支撐的過程中,社會全體的道德就開始崩塌。
這種感受隨著我們社會轉型的深入正在一步步地加劇。我個人對于商業社會的來臨也由最初的歡欣鼓舞而日漸生出恐懼感來,這種恐懼現在已經達到了無以名狀的程度。
當然,如果再把時間向前多推移一段,在歡欣鼓舞地迎接它的到來之前,我們原本就先有一種恐懼感的。我指的是1980年代以前,那時的教育始終都有使我們憎惡資本主義的目的在里頭。
初中一年級時候,憶苦思甜活動還在繼續,但已經不再是強迫我們每個人都去做喂豬的事了,而是換成一種講歷史故事的形式,這比在小學的時候好受多了。雖說這些故事大都來自紅軍長征、八年抗戰之類,但也有專門講述地主資本家如何殘酷地剝削壓榨窮苦人民的內容。地主逼租的事情特別多,還有搶奪民女;資本家們仗勢欺人,壓榨工人血汗也一樣劣跡斑斑。階級之間的斗爭我們都已經非常熟悉了,但有一次老師講到了資產階級內部的斗爭,確實是我們先前聞所未聞。
這個故事據說是真實的。解放前,北京有兩家帽廠,都是老字號,競爭非常厲害。老師特意提醒我們說,資本主義制度把人徹底變成魔鬼,盡管他們同樣都是工人兄弟最殘忍的敵人,但相互之間也不放過,非要置對方于死地不可。于是處于下風的那個商人就出了一條計策。他先是到對方的店里買了100頂最貴的帽子,是當時北京城里達官貴人們喜歡的一種,然后又從全城招來100名乞丐。說每人發你們一頂帽子,三天內你們必須戴著這個帽子,在北京城最繁華的地段來回轉悠。三天之后,來店里領一塊大洋,帽子就歸你們了。
結果這種帽子就臭了街。老師問我們這商人壞不壞。我們齊聲說壞,壞透了,老師就告訴我們說,資本家窩里斗是天性,不值得同情,可憐那些窮苦的乞丐,以為得了便宜,其實還沒轉到第三天,大部分人就都遭到對方老板雇來的流氓的痛打,有些人竟慘死街頭。
這個故事我聽過之后得出了一些當時不敢說出來的結論:一是那個使壞的資本家確實聰明,能想出這樣的計策讓人不得不服;二是那些乞丐太傻,他們應該當時就拿著這種昂貴的帽子去找對方老板,肯定可以立即換回錢來,說不準還不止一塊大洋。最重要的是不會辛苦了兩天還要挨揍。
其實對于商人的鄙視我們從老祖宗那里就帶到血脈中了,這種故事只不過更加深了我們的印象而已。成人以后,我們學到了一些現代觀念,尤其是對于商業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經過一輪新知識的淘換,我們逐漸相信,商業本身對于社會的進步是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增加,現代商業所包含的公平競爭、誠實守信、尊重法律和習俗以及對財產本身的尊崇導致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等等,都對社會的精神文明的發展有著最重要的作用,個人權利不可侵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也隨著商業的逐漸繁榮而生發出來。所有這些東西都在我們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得到了證明。
但是我們沒有忘記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我們現在繁榮的商業并不像是西方國家那樣走的是一條自然演進的道路,我們自己將這個過程稱之為轉型時代,就是說它是通過一種強大的主導力量來完成的。盡管我們都驚嘆于這個偉大的、劇烈的過程所產生的翻天覆地的改變,卻也不得不承認,在這樣一個短暫的時段里,現代商業所包含的那些內在精神卻沒有來得及發育出來,而商業自身先天具有的對社會公德的破壞力卻在不斷壯大,很多為人的基本原則都被它消滅了。
1994年,我隨一個新聞采訪團去浙江溪口蔣介石老家參觀。途中遇到了蜂擁而上抬滑桿的農民。“來吧,抬你上山呢,二十塊錢,當年蔣總統一家出門就是這樣呀。”那是我面對商業第一次感到手足無措。同行的人便開始了一場辯論。有心理障礙的人堅決不坐,感覺自己欺負人,不像話,但主張坐的人說出更好的理由,你同情農民就得坐他的滑桿,不然他怎么掙錢,怎么養家,人家農民都進入商業社會了,你憑什么反倒觀念改不過來。商業社會就是這樣平等,他出賣勞力,你足額付錢,這就是平等。如果你好心可以多給一點小費,但你要是不坐還給他錢,這就是鼓勵他們不勞而獲,他也不會心安。
農民朋友們為這種說法叫好,我們不覺得什么低賤,我們賣的是力氣,又不是妓女,有啥不好呢。組織這次采訪的單位為我們集體付了賬,但是我和另外兩個人始終還是沒有上,那一次,我在道德觀上開始有些糊涂了。
后來,我聽到有人主張建立公開的紅燈區也很驚訝,那人的理由好像也很說得過去,他說這事現在如此泛濫,證明有這個市場,不去規范管理也存在,白白流失了稅收不說,性病也無法控制,最重要的一點,他問,人的智慧可以出賣賺錢,力氣可以出賣賺錢,名聲可以賣,資本本身更可以出賣,那為什么女人的身體不可以賣呢,她出于自愿,為什么不給她自由。那時候我已經年過三十,但在道德觀念上已經糊涂到十分痛苦的程度了。
商業仍然在不斷地發展壯大,買賣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可賣和不可賣之間的界限在無休止地模糊下去,人們卻始終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爭議,從1980年代末期反官倒開始,到愈演愈烈的腐敗與反腐敗,道德在商業社會下不停地掙扎,但它所能占的地盤卻越來越小。行政官員的腐敗讓人喪失了不少信心,司法機構作為社會公正的最后關口也開始屢屢失守,而媒體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有些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是借著維護社會公正的名義參與到商業活動中去,曾經打算將國家與教堂分離開來的人現在卻將兩者全都背叛,發表在報紙上的漂亮文字背后掩藏著他們驚人的私利。
我始終相信正義的永恒,相信社會公正存于人心,相信人類理想不滅,但現實殘酷,竟不知道德會如何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