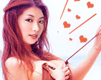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裴諭新
自從我做了性的研究——確切地說是關(guān)于年輕女性的戀愛、婚姻、職業(yè)發(fā)展等等的研究。只不過這一切,很遺憾的,我覺得從她們性生活方式去看更為有趣——我發(fā)覺我的朋友們對我總是暗含了一種期盼:就是希望我的私生活從此狂野起來。比如,他們會很幽默地問:聽說你“親身調(diào)查”啦?一旦我對他們的暗示加以反駁,他們就會不屑地加上一句:“
我X,還女權(quán)呢。”
那我就講一個女權(quán)的例子吧。
前一段時間我的教授聘了一個研究助理芝芝,聘她的重要原因就是她長得漂亮。這個研究助理的任務(wù)是混進歌廳,和舞小姐交朋友,以便調(diào)查她們的“多性伴”現(xiàn)象。教授做這個課題其實有她的目的性所在:她想知道,近來在西方后現(xiàn)代女權(quán)中流行的“開放式多性伴關(guān)系”,在香港有沒有現(xiàn)實可能呢?比如,這些舞小姐會不會告訴她們的性伴:其實你只是我裙下之臣中的某一位?
芝芝的課題還沒有太多進展,自己的生活先出了亂子。原來芝芝是有一個男朋友的,男朋友忙的時候,芝芝就會有“備用男友”頂上。在芝芝的生活倫理里,“備用男友”不會傷害到男朋友。因為第一:她和“備用男友”只是摟摟抱抱的關(guān)系,甚至有一次他們開了房,最終仍然沒有“真正的做”,那自然是因為芝芝堅持不做的緣故;第二:芝芝會把“備用男友”藏得好好,讓男朋友永遠不知道,所以永遠不會對男朋友造成傷害。有了這兩條生活倫理,芝芝在男朋友和“備用男友”之間過得好不逍遙自在。
可是女權(quán)主義一上來,芝芝的生活就亂套了。因為芝芝越是學(xué)習(xí)那些理論,越覺得其實“開放式多性伴關(guān)系”也沒有什么不好:無隱無瞞,坦坦蕩蕩,多好!女人為什么就要生活在欺騙中?為什么不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模式?就像她訪問的那些舞小姐,她們就是誰的男朋友越多越引以為榮的。
理論給芝芝壯了膽,她首先破了“備用男友”第一禁忌:兩個人又去開了房,上了床,而且“真正的做”了。接下來,第二條守則也突破:她選了一個自以為合適的時機,向男朋友“坦白”一切。
你可以想見那種結(jié)果——男朋友不斷地追問:When? Where? How? Why? 芝芝發(fā)現(xiàn),自己每一步的坦白,造成的都只是更進一步的傷害。
兩個人糾纏著,最終還是要分手。芝芝不堪其煩,辭了職,離開香港去了另一個城市。臨走前她問我:“你看過那本開放式性關(guān)系的書嗎?”這是教授叮囑我們的必讀之物。芝芝的功課顯然做得不好。直到這個時候,她還沒有真正讀過那本書。她不知道,書的作者是個美國人,同性戀。
有一個回答可以對付所有倡導(dǎo)我“親身調(diào)查”的建議:如果我研究暴力犯罪,是不是自己先要殺個人?然而這樣的回答似乎太過強烈,不符合我一貫的作風(fēng)。實際上我常常這樣說:“你知道嗎?女權(quán)有很多種。我是中國式女權(q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