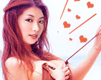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何勁松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今天我在工作之余信手翻閱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啟功書畫集》,忽然接到友人發來的手機短信:“啟功老于今天凌晨逝世。”接著就收到報社的約稿電話,囑我寫篇短文,以追思啟功先生。
一般意義上,追思當然不可避免地充滿著生人對逝者的哀思,但我覺得對于啟功先生的仙逝不必作如是觀。人總是要死的,啟功先生今年已是93歲高齡,這樣的壽終正寢在洞達生死的中國人看來已經令人欣喜——我們習慣上稱之為“白喜事”。作為一名佛教徒、一名信仰佛教的智者,我想啟功先生早已在生死關上自由無礙了吧。當年釋迦牟尼曾貴為王子,之后又曾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雪山苦行,這樣的大起大落終于成就了他對生命的正覺。
啟功先生的一生也可以說是大起大落。他自幼失怙,備嘗艱辛,經歷過家道的興衰和民族的危亡,以及之后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啟功又可謂大紅大紫,各種榮耀的光環都加在了他的頭上。我想,這種起伏、這種反差,肯定能夠成為智者覺悟生命本質的資糧。
的確,一個具有佛教信仰的人不僅能夠正視生死,同時還相信死并不是生命的結束,生和死都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態。實際上,祈求生命不因死亡而延續下去是人類的普遍愿望。人們不厭其煩地生兒育女,就是想讓自己的生命在子孫身上得到延續;而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命當然可以因為他的作品而不朽;同樣,一個教育工作者,為人師表,他的生命無疑地會由他的弟子們傳燈不息。
啟功先生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早已桃李滿天下;作為一名學者,其著述已經等身;作為一名藝術家,他的書畫作品也已為世人視為珍寶。
在我看來,啟功先生留給后人最珍貴的遺產還是他在學術上的求真精神,換言之,他本質上應當是一名真正的學者。作為學者,求真自不待言;而其他諸如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之類的頭銜,哪一個不是在和“真”字打交道?就是在自由地表達心性的藝術領域,也充分體現著啟功先生求真務實的作風。這里我且舉一個例子為證。啟功先生對碑學有著深入的研究,這是人所共知的。他精研碑帖,并將之借鑒到自己的書法藝術中來,但是他又不是簡單機械地加以臨摹,而是盡量將碑刻拓片和出土的墨跡以及唐人的摹本比較印證,究其得失,從而尋求古人書法的真面目。
啟功先生有句名言:“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這是他學碑的經驗之談。我們知道,古代碑帖上的文字一般都要經過書丹(或勾摹勒石)、鐫刻、傳拓等工序,再加上年代久遠、風化剝蝕或木板干裂以及搥拓的粗糙,往往和原作的面目相去甚遠,令學者無所適從,難以捉摸。啟功先生說,學碑帖的人,往往在帖中因點畫全白、筆畫無濃淡,便以為是毫鋒飽滿,中畫堅實,其實這是錯誤的。因此學習碑刻書法,必須明了刀和毫是兩種不同的工具,并細心體味刀、毫的特點和所產生的不同效果,才能把握書法的真諦。他還不無幽默地說:一個人如果見到口技演員學鳥叫便誤認為人的語言就是這樣,這豈不是大笑話?
行文至此,我的腦海里浮現的啟功先生是一個和靄可親、笑容可掬的老者。他在我的心中是活生生的,我無法在字里行間表達出我的哀思。我想,真正的哀思是不是要等到痛定思痛之后呢!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宗教藝術研究室主任,院書畫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