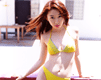|
童月
常去一家藥店買煲湯料,久了,和店員及店貓都混得爛熟。俗話說: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說的是養娃娃需讓他多見人,娃娃不認生,嘴巴甜,討人喜歡;養那種看家護院的狗,最好別讓它見生人,略略有個風吹草動,狗才叫得兇。養貓也一樣道理,這只“大營子貓”,見慣人來人往,見誰都咪咪叫著貼上去,拿腦袋蹭。有資料說貓這是在往人身上“涂
香水”——它耳朵旁邊分泌的一種獨特的氣味,借以向別的貓表明:此人甚好,歸我了!
有段時間店貓失蹤了足足一個禮拜,再回來時,有些黃瘦。店員意味深長地說:春天了唄。我說,恐怕已經懷孕了。要不要拿只驗孕棒測一下?店員大笑,把貓翻過來,仔細檢查它的小屁股,說,肯定有了,都不是小姑娘貓了。
我抓狂:難道貓也有處貓膜?
隔了將近一個月,再去那家店,不見貓,據說去分店出差了。我對店員千叮嚀萬囑咐:給它吃點幼貓貓糧增加營養;貓懷孕兩個多月就能生,要是看到它四處叫著找隱蔽處,八成是快了,提前準備好紙箱子……
我對一切可能孕育著生命的東西感興趣:懷孕的母親、種子、插土能活的柳枝……忘了哪本心理學書上說,小孩子拆開中國套盒、八音盒等一切“內有乾坤”的物品,源自一種成長的焦慮:他急切想知道自己體內蘊藏的是怎樣的一個未知的“自我”。我的小時候,這種焦慮卻表現為一種“種植”的渴望。
種過“太陽花”,老家俗稱“死不了”——你可以想象這是怎樣好活的東西。拿花盆種似乎有點不搭調,最好找個殘破的木箱子,鋪好土,撒種。種子只有英文句號大小,每天澆水,有個三五天的樣子,土上微微起了一層紅霧,仔細看,是一棵棵細苗。不到一個月就能開花,每日一朵,日出開,日落敗。開到入秋,頹了,爛爛的像一種叫馬齒筧的野草。但種子還在長,熟了便炸開,一粒粒落到腳下的泥土中。此時種植是一件省心的事,一年工夫,換來數年花開,直到那箱子被丟掉。
稍微復雜一點的東西,是花生。當年播下種子就遺忘,只因那塊地臨近水管,常年濕潤,一不小心便長成一大棵。秋季,父親替我收割,一鏟下去,竟是沉甸甸一大串花生。只可惜掘早了,殼子里還是一泡嫩水。
最近,也許是源自想為人母的渴望,重新種植。在花店里千挑萬選,花10元買了一袋“跳舞草”的種子。種植方法極其復雜:先用細砂土磨去表層蠟質,再放到50度溫水中浸泡24小時,看到種子露白,才可播種。依法炮制了8粒種子。播種第二天,花盆正中央即冒出一棵小芽。欣喜,又有些疑惑:資料上不是說,播種3-5天發芽嗎?第三天,又一棵小苗出土,和前一棵卻全然不同。疑惑更大,不知孰真孰假。好在第五天又發芽兩顆,均和第二棵相似。3:1,我判定最早出土的是野草。想想任何生命來到世間都不容易,任它生長。出土之后陰雨不斷,跳舞草熱愛陽光,陽光不在的日子,它們先后枯萎。而那棵野草沐浴春天的雨露,茁壯成長。至今,花盆里蓬蓬勃勃的一大棵,已抽出了花穗。不知道名字,但校園路邊,滿地都是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