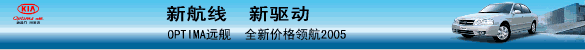登琨艷:誤入時尚圈的建筑師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21日 18:04 《全球財經觀察》 | ||||||||
|
他曾經有一段逃離人群的流浪生活,長達10年;他把蘇州河邊的舊倉庫改成時髦的藝術家工作室并且風行;他年過半百了,還經常即興逃到東京觀察建筑;他數十年堅持穿三個品牌的男裝,卻始終堅持自己的時尚是被動的,只是遵照了內心的想法而已 文|蘇德
從南蘇州路的這頭,到那頭,在冬天的下午里,有蘇州河水里的冰涼風氣和太陽折射后的疏暖微粒,靜默在兩岸旁的舊倉庫顯得很悚然,那是半個多世紀前上海灘大亨們搭建的工廠或糧倉。在解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們幾次被翻修被易主,梁垣交錯。如今,以成都路高架為界,一邊幾乎還保留原貌,一邊河堤已經翻修重建,很多倉庫也成為若干藝術空間或是工作室。而6年前,最早決定將工作室搬進這兒的人就是登琨艷。 也許因為姓名的特殊,“登琨艷”這三個字經媒體大肆渲染后總給人似是而非的印象,就連他自己也說,可能會有很多人知道“登琨艷”,卻不會有太多人知道這個人是誰,在哪,在做什么。這種與人群保持似是而非陌生度的疏離感,正是他這么多年來背負著虛名逃離臺灣建筑界后最想要的。 6年前,當他在租用南蘇州路某號舊倉庫的合約上簽下“登琨艷”這三個字時,那一劑在他說來給自己打的“逃脫麻醉藥”已經散了整整十年的藥力。他記得最初離開臺灣去歐洲和美國流浪整兩年的日子,每到一處,他看的關心的,都是建筑;他記得后來落腳上海,常包海鷗飯店住房的日子,每天起床看黃浦江兩岸泛舊的神色,不想工作。那時候的他,異于常人地將退休提前,把想去的想玩的地方走遍,最后才肯安定。 這6年來,登琨艷終于安定在蘇州河邊以舊倉庫改建的工作室里,重新又趴在設計臺前不休工作,幾乎從清晨到暮色,偶爾也會去位于楊樹浦路的工廠巡看一下。雖然他常常還是會冒出來“逃開”的念頭,但卻又很清楚那一劑麻醉藥已經漸漸散去,自己終還是要回到企圖跳脫開的現實里——在倉庫三樓的巨大空間里,垂吊于設計臺上的四盞聚光燈下,有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居所。 幾年間,經過幾次改建裝修,這座三層的巨大倉庫最終變成如今的模樣。對于它的歷史,登琨艷并非如一些媒體所言的那么熟悉,租下它,也純屬偶然,而這種偶然卻猶如時尚般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藝術家遷入南蘇州路的老舊倉庫。 除了建筑外,登琨艷還很喜歡拍照,無論是在臺北工作時,還是在歐美旅居的日子里,他都喜歡將各種有趣的建筑拍下來,定格在畫面里。而6年前,他最初在上海相中要做工作室的倉庫并非這一座,就是由于當時決定簽合約租下那之前,一時興起拿著照相機四處拍,一不小心踩斷了木樓梯,摔斷了腿,才不了了之。后來病愈,性格堅韌的他,硬是在不遠處租了大出原來一倍多的倉庫,干脆將工作室擴大,陳列各種建筑模型。 和大多數人相反的是,面對成功和安逸,登琨艷會想逃;但如果有困難和阻力在面前,他卻偏要踩過去走得更遠。 認識登琨艷的人都知道,在上海,他幾乎沒有什么朋友,經常獨來獨往。有時候,司機會在車子上跟他打趣地說:“登先生,你不覺得這種幾點一線的日子有點無趣嗎?”他也不動氣,反問道:“什么才是有趣?我覺得你的生活才無趣咧。”一笑了之。在他看來,現在自己的生活雖然很忙卻還是充實的,因為至少仍然是為了自己而活著工作著,不用遷就任何人。工作中的他看上去有些拘謹,沉默寡言,將樓下辦公室里替他工作的員工統稱為“小朋友”。年愈“知天命”后,對于這些“小朋友”,他既有老板的嚴厲又有長者的寬容。 登琨艷常常工作到間歇,會走去倉庫三樓巨大的落地門前停頓佇立,作為建筑師,他對于空間的感覺很敏銳,對視野的要求也很高。所以,那頂樓望出去的蔚天灰鴿,是他最為艷羨的輕松。少數幾次,某天他覺得有些累了,第二天便訂一張去東京的機票,暫時“逃”開,去買自己最喜歡的東西,順便再流連一下京都。他喜歡未經修葺的純樸,像是京都的古建筑,像是黃山腳下的原始村落,那些疏淡的安寧里,有經歲月洗禮后留下的痕跡,是任何現代建筑都搭建不起來的幽致深遠。 有人說,五十多歲的登琨艷很時尚,因為他常常在別人發現某種流行趨勢之前,早就行動起來。無論是倉庫改建工作室,還是張愛玲圖書紀念館的預想,他總能比別人快幾拍。可他自己,卻常為此覺得有些莫名。 登琨艷說自己在四十歲“不惑”之前,曾經很“疑惑”過,所以他給那時候的自己一劑麻醉藥,暫時麻痹工作神經,逃開建筑界,逃離臺灣,四處流浪。生活中,他會頻繁地更換各種品牌,嘗試不同的感覺。那十年里,他“捏造”過各種自己,在不同的地方,抽離出人群來看待生活。往往遇到陌生地里有人在對話在生活,他只是安靜地站在一旁仔細聽認真看,從不搭話也不介入。 在他看來,這種游歷喜愁百味的態度,倒讓如今的自己更為沉穩安定。至于時尚,他覺得自己不會講究,也不懂講究,他不過是覺得怎么做能讓自己開心,怎么穿能讓自己沒有束縛,就這么做,這么穿了。 因為經常要畫草圖,再加上身體瘦,很多西服上衣登琨艷穿來都會長出一些,他也不會改短,生怕里面的白襯衫幾天下來就烏黑難洗;他喜歡喝啤酒,又懶得一次次走去工作室里的吧臺,便用一大只紅酒杯來盛;他喜歡音樂,過去工作的時候幾乎無法離開背后的環繞音響,可當音響壞了后,在靜寂空間里他又能安然處之……他絕少會去留意所謂的“時尚”,更多時候,他就是隨性而為的,卻又偏偏被外界圈劃進時尚圈,美國某報曾經稱登琨艷為“中國最時尚,最有品位的男人”。 只是,這個時尚男人早在四十歲后,只穿三個保守品牌的男裝,一年四季如一的白襯衫加西服,雖然他的各種建筑作品或是設計構想里總不斷冒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前瞻靈感。 6年前,定居上海后,登琨艷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會留在這座日易新貌的城市。偶爾回臺灣,只是看看家人,和那邊的朋友同學聚一下,或是看望在東華大學做旁聽生時的導師。交談到尾處的時候,突然工作室吧臺上的電話響起來,正是在臺北的恩師。他們互敘了很久,最后,登琨艷略有些笑意地說,又有東華大學建筑系的學弟學妹們通過恩師打探詢問他的消息。在學校校友名錄冊里,也許并沒有“登琨艷”這三個字,可當年的那個旁聽生,現在的登琨艷卻著實成為東華大學建筑系最有名的人。 很多在臺灣的老同學多年后看到登琨艷時都驚訝于他的天真未泯,對于一些幻想性的完美,他依然非常計較,帶著各種不真實的理想。登琨艷說,和作家相比,建筑師的作品更容易被人“閱讀”,而且是強制性地被閱讀,建筑陳列在原地,帶著設計者想表達的一切,所以建筑可以說是建筑師思想的載體。 可他自己總只是在建筑剛落成時,興奮地拿著照相機遍拍一通,之后便再也不敢迫近了,就像位于烏魯木齊路的那家“三千院”。他很怕看到建筑尤其是經營性建筑經人跡后的毀壞,很怕看到自己以為的完美遭到褻瀆。這種難過,無與倫比。所以有時,寧可像孩童那樣,在圖紙、照片或是記憶里追溯最初的美好。 聯系編輯gloomy@gfo.cn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隨筆砸談 > 《全球財經觀察》2005 > 正文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