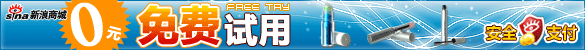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
吳曉波:以企業的名義記錄歷史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1日 11:28 國際航空報
本報記者 陳曉顏 對話語錄: 真正好的企業家是老烏龜,每年身上都要漲一層繭,殼很薄的時候,一踩就爛了,老烏龜就踩不壞,而且爬得慢,生命力有5、600年。 中國企業家一直以來都有原罪感,因為他知道我是在突破現有的法律,同時又有高尚感,因為我是改革的先鋒。 艾森豪威爾有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說什么叫知識分子,就是你必須要有一條不以此為生的職業,也就是說你失去這個職業還能活下來。 寫企業史對企業家沒有好惡感 本報記者:你是什么時候、在什么機緣下開始著手研究并撰寫企業史的? 吳曉波:2004年,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哈佛商學院有個企業學史教研室,有很多知名教授,也有很多歷史書,很多企業家傳記。但美國人對中國不了解,他們問我有沒有一本書,能夠講中國企業歷史的,或者有哪些好的企業家傳記,我發現都沒有。后來,我去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有個口述室,象洛克菲勒等一些企業家老了會把自己的歷史講一遍、留檔,作為別人幫他寫回憶錄最基本的原始材料,這在中國沒有。因此,2004年我開始關注中國企業史,我發現二三十年下來,沒人給這段歷史斷過代,你不知道這三十年歷史該怎樣分代,也沒有人清晰地描述過。我又覺得2008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還要舉辦奧運會,那時候民族情緒會很高漲,大家會回顧。當時肯尼迪學院請我去做一個中國民間公司成長歷史的研究,2004年離開的時候,跟他們簽了協議,做這方面的東西,回來后就開始寫,就寫成現在這樣一個狀態。 本報記者:一般情況下,企業不愿意把核心的內容向媒體或企業之外的人披露,你是怎么獲得第一手資料呢? 吳曉波:第一,我是1990年開始當記者,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已經當記者14年,寫過專欄、也寫過書,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已經寫了9本書,十多年接觸很多企業。第二,寫書一般不會受第一手資料所局限,你回過頭來想,清朝寫明史的時候,哪有第一手資料可參考。而且,現在其實是個檔案社會,記得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王石當時講中國入關后,房價跌15%,事實上漲3倍都不止。所以,當我寫到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的企業家是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的,我就以王石為例來講,這完全是反向的判斷。整個社會,尤其是公眾企業大量的東西是被檔案化的,我可以從歷史檔案中查到相關信息,最辛苦的是把老報紙、老的書拿回來重新翻檢一遍。 本報記者:你曾經也說到過寫作底線的問題,你怎么既保證閱讀價值,又不把企業的商業機密泄露出去? 吳曉波: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沒這個問題。在選材的時候,關于事實本身的東西我敘述比較多,我發現自己寫了很多年后,現在對企業家沒有好惡感,不會因喜歡他而寫得特別好,也不會因不喜歡他而不好好寫他,不會在價值觀上來判斷他,盡可能避免主觀的東西。 本報記者:中國經濟現在處于高速發展的通道,那么中國企業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是什么? 吳曉波:中國企業家面臨的機遇是中國處在一個高度成長的通道里,過去27年里GDP每年保持8%到9%的增長速度,這在過去100年里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但中國企業家每天面對的都是從來沒見到過的局面。創建公司就像爬樓梯,而在美國做企業,企業家本身受過良好的商學院教育,商業法規又完善,在2樓他就可能知道7樓是什么風光,而中國企業家在爬樓時,他在20樓時就不知道21樓是什么風景,所以中國企業家搞企業風險大些,成功或失敗的偶然性大。 本報記者:是否有這樣的情況,很多企業的總裁跟你溝通,認為你對他們企業的觀察和分析比他們本人還要深刻? 吳曉波:當然,我肯定比他們看得清楚,他們在那玩游戲,我在旁邊看,比較客觀。做企業跟做人一樣,企業家個人張狂,這個企業也一定很張揚。有些人還能自我反省。我曾經跟潘石屹聊天,我問他:你有10個億身價的時候,人家叫你小潘,現在你有140個億了,是不是感覺這個公司跟以前不一樣了?他說上市以后,我有兩個禮拜沒搞清楚我叫什么名字,有點懵了。后來我去見了一個智者,智者跟我講了兩句話:第一,什么都沒變,你還是潘石屹。第二,管理好你的時間。我在《大敗局》里寫的,很多企業是自然死亡,是行業的問題,但很多企業是崩塌式死亡,那就是做錯了什么事情。潘石屹雖然看起來很張揚,但他很清醒,他本性也很謹慎。真正好的企業家是老烏龜,每年身上都要漲一層繭,殼很薄的時候,一踩就爛了,老烏龜就踩不壞,而且爬得慢,生命力有五六百年。 企業家不是知識分子 本報記者:你的《大敗局》,對很多明星企業家的案例做了分析,那么這些帶有悲劇色彩的企業和企業家的命運帶給你怎樣的震撼? 吳曉波:我寫書的時候,其實已經準備了二三年的材料了,所以在寫的時候已經不太會有什么感情波動了。而且,企業看多了,我知道一個企業生死都有它的邏輯存在。另外,德魯克講過,一個好的企業家或好的公司其實是很寂寞的,公司管理是很無聊的事,當公司發生驚天動地、驚心動魄的事情時,公司就異常了,這是很多做企業的人沒有想通的問題。很多人覺得企業就應該生龍活虎,風生水起,其實,如果一個企業做到風生水起的時候,離死已經差不多了,你看看這幾年,喜歡講大話、拋頭露面、做重大決策的人,他的企業十有八九最后都衰落了。 本報記者:我們常說創業是需要激情的,但你曾經說過一些企業的死亡也源于激情,那么你認為企業如何把握“激情”的度? 吳曉波:這是最難做的問題,企業家一般都有工程師性格和賭徒性格,工程師性格只能按部就班地做,但你若按部就班,充其量只能當個副總,做企業還要有個沖動,就像男人的野心一樣是不可遏制的。企業家有一大半是天生的,由他的性格決定的,很多人不適合做企業家。賭徒性格可以使他以小博大。打個比方,人和狼、狗的區別在哪兒,一塊肉放在那,狗是不會思考的,看到獵物就會無顧忌地撲上去把獵物叼走,這就是動物性。而人是會思考的,這塊肉是不是我的,這是不是誘餌,這是否道德,他會想很多問題,等他把問題想清楚了,肉已經被一群狼叼走了,這就是狼文化和人性的區別,但你要是狼,每次都這樣撲肉的話,難免有一天會被肉毒死,這就是企業家做選擇的難處。我認為,企業家首先是條狼,在不斷賭的同時,要想到節制、要有道德底線、要考慮風險問題。 本報記者:你認為一個優秀企業家應該具備什么素質? 吳曉波:首先,我覺得企業家要有很強的冒險性,他敢于去嘗試,他某些方面動物性比人性大;其次,企業家邏輯思辨能力很強,如果企業家是個很感性的人,他做企業是做不好的;第三,企業家體力要好,做企業很苦,企業家多數過的是非人的生活,在很多企業里,企業家一定是飯量最大、睡覺最少、朋友最少的人。 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是不同的,最大的區別在于知識分子往往把道德放在首位,判斷是非,企業家則把得失放在首位,不是說企業家不講道德,企業家也講道德,但企業家為了利益會輕易穿越道德底線。我曾寫過一本書———《被夸大的使命》,講到企業家是不可能成為知識分子的,在中國不可能存在儒商,是儒就是儒,是商就是商,要么是企業家,要么是知識分子,如果重疊的話,公眾和輿論就會把該由知識分子承擔的責任強加于企業家,我認為一定要把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剝離開。 本報記者:華旗的老總曾說過,在中國做企業家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怎么看? 吳曉波:他講的沒錯,中國的法制還不健全。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突破現有的法規,中國的改革是企業家和民眾從下往上突圍,突破后,政策從上往下追認,追認其合法性,中國的法制就是這樣被不斷地完善。你在突圍的過程中,中間有個過程就是原罪階段,中國企業家一直以來都有原罪感,因為他知道我是在突破現有的法律,同時又有高尚感,因為我是改革的先鋒。 本報記者:您怎么看企業家的原罪? 吳曉波:從這樣分析來看,所謂的原罪,都是制度的原罪,不是人的原罪,如果法律足夠好的話,人是不愿意犯罪的,每個人都有惡的念頭,但法律能遏制人惡的念頭。 不愿當官、辦企業,我只會寫字 本報記者:作為財經作家,有沒有考慮像梁鳳儀那樣寫商戰小說? 吳曉波:不會的,我寫到現在為止,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經不會虛構了,喪失了虛構的能力。 本報記者:前一段時間,網上出現了一個圖書方面的《福布斯財富榜》,郭敬明、余秋雨都名列其中,你關心這個排行榜嗎? 吳曉波:我似乎跟這個排行榜沒什么關系,我的書才賣10幾萬冊,他們的賣100多萬冊。我07年出了3本書,加在一起賣了30萬,版稅一共90萬,這個行業賺不了錢。 一個神父講過一句話,人什么時候是幸福的,一輩子做你喜歡做的事,這件事順便還讓你有錢,第一點我們做到了,但第二點很可惜。我在財經寫作里已經算是全國前幾名了,但從財富角度來說,還不如我的房子每平米漲100塊錢的收益大。這是可悲的一件事情。 本報記者:回顧一下過去,你覺得自己最為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難的階段是什么? 吳曉波:我面臨的問題應該是所有年輕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大學畢業進入社會就會面臨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就是財務問題,第二個是職業有個天花板的問題,特別是媒體這個職業,很容易碰到天花板,你做了五六年后,就會發現自己沒進步了,總在跑新聞。 上大學時,艾森豪威爾有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說什么叫知識分子,就是你必須要有一條不以此為生的職業,也就是說你失去這個職業還能活下來。當我財務問題解決以后,我的心態就變得平和了,我在研究企業的時候更加客觀,能夠保持我的立場。 所以我比較得意的是,我30歲的時候,就把財務問題怎么解決、職業問題怎么解決想清楚了。30歲后我就很少焦慮了。二十八九歲的時候我看清楚一點,這個職業不會給我帶來豐厚的物質生活。但我不愿意出賣自己的職業,幫別人寫軟文,人家給你幾萬塊錢,盡管也可以完成原始積累,但很丟臉,沒底線了。我是搞財經的,長遠的一些問題能看清楚,我認為,中國土地最值錢,房價會漲,所以從那個時候一年買一套房,堅持了10年,包括在千島湖買了一個島,財務問題就這么解決了。所以我現在寫東西不怕人家跟我打官司,大不了我賠一套房子。 媒體人最后有三條路好走,第一是記者、編輯、主編、最后是管理者這樣一條軌跡。第二條把媒體當作跳板,到企業去做分管文化的副總裁,或去開廣告公司、公關公司,把這些年積累的東西套現,這也是一條很好的路。第三條就是還在寫字,一輩子都在寫字,當專欄作者或作家,我不愿意當官,我也不愿意辦企業或為企業服務,我只會寫字,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當年藍獅子發起人是6個,劉州偉、秦朔、胡泳、趙曉、劉韌,他們后來都當總編、做經濟學家,只有我還在傻呼呼地寫。 困難的階段是我2004年寫《激蕩三十年》之前,有1年到2年比較困惑。我寫完《大敗局》的時候,就不知道該寫什么了,那時候就面臨很多選擇,很多人建議我開咨詢公司、到大學教書,但我又覺得這些似乎跟我沒什么關系,我也不懂管理學,只能講案例,我又不是一個演講型的人,我是一個寫作型的人。2004年以后,我開始寫《激蕩三十年》,就很開心,為什么呢,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齡以后,不需要每天去完成任務,人的痛苦在于你要不斷選擇。因為誘惑、焦慮造成人一直處于無法滿足的狀態,那么怎么辦呢,我給自己布置個任務,3年完成。雖然很辛苦,寫60多萬字,還開著幾個專欄,再管理藍獅子,但我沒有選擇了。所以,我覺得人在35歲到50歲之間最快樂的事情是給自己每隔3年到5年布置一個任務,就怕半年任務完成了,又要面臨選擇,很痛苦。 老了到島上去當農民 本報記者:你對現在的生活是否很滿意? 吳曉波:我很單純,除了寫字我什么都不會,第二個,我的專業很窄,沒什么人競爭,《激蕩三十年》寫完之后,我會花兩年在2010年之前寫完1870到1970年這一百年的歷史,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以后我還會每隔4年寫一本《大敗局》,我覺得4年會死10個企業,很有特點,55歲之前就基本上安排滿了。 其實,50歲以后,這個社會就不需要你了,因為作為一個寫字的人,你寫字的方式已經被淘汰了,就像我們看巴金的小說一樣,那是前一代人的寫作方式,我們已經不用這樣的方式寫了。到我們50多歲的時候,30多歲的小孩已經不用這種方式了,我們寫東西就是為了傳播,人家不需要,我就不寫了。 所以,我買了一個島,老了就到島上去當農民。 本報記者:以后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吳曉波:我女兒快14歲了,要移民加拿大。2011年之前我要把激蕩一百年寫完,我太太要做世博會,然后我們移民加拿大,陪我女兒讀大學。大學畢業后,我們必須回國,陪雙方4位老人。他們都70多歲了,我們要陪著他們度過最后的時光,把他們一個個送走,那是我們最痛苦的時候。然后我也就50歲了,我的職業生涯基本結束了。現在如果沒有東方衛視那個《中國經營者》的欄目,我現在已經處于一種退休狀態,藍獅子交給職業經理人去做,把股份稀釋給我的很多管理人員和作者,我是第一大股東,但我不需要那么多錢,我就是想給大家創造一個出版平臺,讓大家都能發財也做點有尊嚴有理想的事情。 本報記者:借用一個書名《這一代的愛與怕》,你覺得自己或者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懼是什么? 吳曉波:我們這代人受了很大的存在主義教育,我進大學是86年,那時候存在主義在中國剛剛興起。復旦又是一個人文氣息很濃厚的大學,那些哲學對我們影響很大,總是為了一個理想或者夢想活著,但我們跟老一輩人比較起來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包袱。現在80后的孩子面臨著激烈的競爭,我們那時候沒有感受到這種競爭的壓力,所以我們這代人是夾在中間的,各有好壞。另外,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我們大學畢業分配到機關單位,然后能分得一套房子,在IT界,馬云他們都是積累了一定經驗以后就迎來了互聯網興起,新的行業誕生,媒體界也一樣,各大媒體的老總也都是我這個年齡,因此我們趕上了很多好的機會。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新浪財經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