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霖:從中俄比較看國企改革爭論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27日 12:33 《商務周刊》雜志 | |||||||||
|
從中俄比較看國企改革爭論 ——訪世界銀行高級專家張春霖 □記者 鐘加勇
“坐失”與“流失” 《商務周刊》:中國時下關于改革的爭論還在進行,我們希望跳出爭論本身,從俄羅斯轉軌的經驗教訓出發,談談其對中國有什么樣的借鑒作用。前不久您在翻譯了《世紀大拍賣》這本書后也提出要“從鄰居的不幸中學習”,讓我們印象深刻。對于改革與轉軌27年來的中國,現在又開始反思向左還是向右,向好的市場經濟還是壞的市場經濟,鄰居的不幸有什么樣的警醒作用? 張春霖:我在翻譯完《世紀大拍賣》之后,寫了一個翻譯后記。那是在2004年春,當時我最大的感受是,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發生的很多問題,跟我們國有企業改制中發生的問題非常類似,所以實際上我寫那個文章是想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自大,不要覺得人家俄羅斯一塌糊涂,我們一切都很好。 《商務周刊》:國內這場關于改革的大爭論,源于郎咸平教授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論述和案例的剖析,他認為國有企業通過管理層收購(MBO)加速了國有資產的流失,這非常不公平,實際是被雇傭的經理人在沒有信托責任約束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竊取了主人的資產;進而通過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率比較,他認為國有企業的效率可能比民營企業效率更高,因此,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式應當予以修正。您過去10多年一直致力于國有企業轉制的調查和研究,您認為他說的有道理嗎?應該怎么正確認識國企私有化的問題? 張春霖:我贊成引入信托責任,我們以前寫的報告也都強調在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當中要引入信托責任。全面引進信托責任這個概念,可以成為強化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公司治理的一個手段。至于說國有企業能不能搞得比私營企業還好,在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有名的“標桿(benchmark)”,是斯蒂格里茨和薩平頓兩位經濟學家1987年的一篇論文提出的觀點,叫做“所有制無關”。他們的基本意思是說,如果能滿足兩個條件,所有制就無關緊要,私人企業可以做的事情國有企業都可以做,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可以搞得和私人企業一樣好。哪兩個條件呢?第一叫做“國家是仁慈的”,第二叫“合同是完全的”。 什么叫“國家是仁慈的”?用我們的話說就是國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沒有任何私心雜念,沒有什么部門利益,沒有什么地方利益,更沒有什么私人利益,國家的每個部門、每個官員都是百分百地忠誠于人民利益。什么叫“合同是完全的”?就是每一層的委托代理關系,都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老百姓可以百分百地監督政府,政府也可以百分之百地監督國有企業管理層。如果可以做到這兩個,那國有企業跟私營企業就沒什么差別了。當然,你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都是非常極端的假定。這樣的假定目的是為進一步的分析建立框架或“標桿”,現實當中這樣的條件當然是不可能完全滿足的。即使私人公司,只要存在所有權和控制的分離、存在嚴重的公司治理挑戰,這樣的條件也是不能完全滿足的。但這個標桿可以大致說明,國有企業要搞得和私營企業一樣好,難在什么地方。 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來看,從1978年開始,國有企業改革試圖在國家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搞好搞活”國有企業,用了多少五花八門的辦法?能想得出來的辦法幾乎都用上了,全世界國有企業改革的辦法到中國來都能找到版本。最后到1990年代大家終于認識到,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要把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搞好搞活”,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因此才有了后來十五大確定的“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這樣的思路。盡管這個思路在這場爭論中遭到質疑和批判,有人甚至輕蔑地將之貶低為“拍腦袋”拍出來的,但我仍然認為它是正確的。當然,一部分國有企業可以經營得非常好,今天很多行業的排頭兵都還是大型國企;另一方面,私人企業也有虧損破產的。我并不懷疑一些國有企業可以經營得比一些私人企業好,也不主張國家從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退出。 但也要看到,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家從一些企業的退出既可以是主動的,也可以是被動的,不是說你不改制就永遠不會退出。比如說一個國有企業,假設原來有100萬資產,其中80萬的債務,20萬的所有者權益,那20萬就是我們說的國有資產了。然后它連續虧損到現在,資產只剩下60萬了,光欠人家的債務就有80萬,這個企業國有資產已經等于負數了。你看統計表格上寫著它還是國有企業,沒人把它私有化,但國家在這里面已經沒有權益了。這些企業叫“空殼企業”。1995年清產核資的時候,30多萬家國有企業有37%(按個數)的比例是這樣的企業。10年前,地方政府對國企的一般估計是,1/3是優秀的,1/3掙扎在盈虧點上,1/3是“長期虧損,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當時搞兼并破產試點的時候,一些地區摸底調查,整個城市國有企業加起來是資不抵債的,而且還是按賬面資產算的。到現在,仍然有相當大量的國有企業處于資不抵債的狀況。當一個國有企業資不抵債的時候,你可以不去動它的所有制,一百年都把它寫在“國有企業”那個欄目里邊,但是你得承認國有資產已經沒有了。而且,如果你不給它輸血,它不能按時清償到期債務,它就會被起訴破產,一破產就是“資產變現、關門走人”。有沒有搞私有化?沒有。國家退出了嗎?退出了,是被動的退出。不用私有化了,因為國有資產已經等于零,沒有什么可“化”的了。這就是所謂的“坐失”,你要賣企業可能發生流失,你不賣企業也可能發生坐失,坐失同樣可以讓國家從企業退出。 當然,坐失和流失比起來不那么聳人聽聞。這主要是因為流失多數是一種資產轉移,國家利益損失多少,少數個人就差不多能得到多少,這少數人于是很快就暴富了。這樣就很容易激起公憤。坐失經常不是這樣,在很多情況下,坐失的特點是國家利益的損失遠遠大于少數個人從中撈到的好處。大出來的部分哪里去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消失了,被浪費掉了。比如一些項目,幾十個億投下去,沒開工生產就知道要賠本了,生產越多賠本越大,這樣的項目多得不得了。這幾十億落到哪個個人手里了嗎?可能都沒有。你要去看還能找得到,就是在荒地上蓋起來的一片半拉子建筑,一堆任憑風吹日曬已經生銹的機器設備。當然有的時候也有少數個人得到了好處,但那也只是幾十億當中的很小一個比例。幾十億的國家財產基本上打水漂了,沒有讓誰暴富起來。所以,坐失和流失相比,更容易使人放松警惕。 政府改革更為關鍵 《商務周刊》:過去國有資產轉讓的方式非常粗放,雖然媒體報道過很多國企MBO的案例,但直到現在相應的機制都還沒有建立。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城市就可以限定期限要把整個城市的國有企業都賣光,而這當中出現的問題是誰的責任?下一步應該建立哪些相應的機制? 張春霖:如果從制度建設角度來說,經濟學家們其實很早就在研究。比如說1995年吳敬璉老師和我寫文章談國有企業改制,就提出過三條建議:第一,要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后來成立的國資委就是這樣的機構。有個機構負責,最后國有資產流失了,打板子也知道打到誰的身上;第二,就是要有一個底價,要有一個第三方參與來確定的底價;第三,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引入競爭,凡是有條件的地方都要在市場上公開出售股權。 我們不能說什么機制都沒有建立,只能說建立得很緩慢。比如成立國資委,2003年前沒有國資委,但在這之前也在賣國企。誰在賣?有時候市長自己賣,有時候工業局就賣了,最早的時候甚至還有企業自己賣自己的。所以第一條建立國資委是很大進步。第二條資產評估是一直很重視的,多年來很多人在國有企業轉制中害怕犯錯誤,那么保護自己的辦法就是資產評估,因為第三方評估過了,你很難說他流失。但問題是資產評估在有些地方經常被操縱,走過場,再有資產評估的方法也有問題,我們的資產評估多數情況下都是歷史成本法,而合適的方法應該用“收入折現法”,就是把未來收入流折成現在的收入,但是現在這個方法用的不是非常普遍,因為它技術要求很高。第三條,就是競爭,這是進展最緩慢的一個領域。其實這個東西用不著講多少理論,你大街上找一個老大爺問問,誰都明白這個道理:信息要公開,三公原則,尤其是不能自賣自買。但是這么多年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就是到現在也不能說解決得非常好。現在很多自賣自買都繞著圈去搞了——當然我也只是聽說——有很多曲線“MBO”的做法。產權交易也是這樣,國資委現在規定所有國資轉讓都要進產權交易所,但我記得有一次一個產權交易所的老總說:“人家都是身懷六甲了,到我們這兒來領個結婚證。”也就是說人家私下里都談好了,有的其實還是自賣自買。 《商務周刊》: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如果政府改革這個瓶頸不解決的話,其他競爭、評估等等一系列的市場機制都無法充分發揮其作用,甚至是癱瘓的? 張春霖:國有資產是政府代表全國人民在管,賣的時候也是政府代表全國人民在賣,所以,整個問題的癥結是政府能不能在賣的時候非常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流失不是因為賣才發生的,問題的根源在賣之前已經存在了,就是政府管理國有資產的能力、機制等等很多方面存在缺陷,一賣的時候這些缺陷就表現出來了,就變成了流失。 從俄羅斯的不幸中窺探未來 《商務周刊》:在您看來,俄羅斯當年轉軌的時候政府改革跟上了嗎?整個俄羅斯的私有化革命其實是一場鬧哄哄的“世紀大拍賣”,它除了財富轉移過程中無規則下的攫財秘密和迅速暴富比中國更加激烈和富有戲劇性之外,您覺得哪些地方跟中國有根本性的差別或者有驚人的相似? 張春霖:俄羅斯跟我們有很多不同。比如轉軌之前,它的國有企業雇傭了整個勞動力隊伍的90%,民營經濟在整個GDP中只占5%,基本沒有;而我們的國有企業在最高峰的時候其雇員人數也只有7500萬人,現在只有3000多萬人,占整個勞動力隊伍不到4%,這是個很大的差別。俄羅斯當時真正是國有企業一統天下,所以它沒有回旋的余地;而中國工業化比俄羅斯落后得多,我們可以有鄉鎮企業,有私營企業。這就好像你們家只有一處大房子,要翻修一下,就只好一邊拆一邊還得住在里邊,而我們家有一個小房子還有一個草棚子,我就可以先住在草棚子里來翻修房子。這邊國有企業在翻修,那邊非國有企業在迅速增長,所以即使國有企業真出了問題,整個經濟也不會塌下來。相比之下,俄羅斯沒有這個選擇,它國有企業沒有改好,整個經濟就掉下來了。 再有一個大的差別就是,當時的蘇聯共產黨拒絕改革,也沒有能力來領導改革,而中國的改革是由共產黨來發動和領導的,這樣就在政治體制上、在整個社會架構上保持了一個連續性。俄羅斯的改革是在整個政治體制解體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俄羅斯政府在出售國有資產的時候,它的政治地位、談判能力都要比中國政府弱得多。葉利欽當時在政治上是搖搖欲墜的。在沖突非常激烈的過程當中,葉利欽面臨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俄羅斯杜馬里勢力非常大的一個集團是國有企業的現任廠長經理。葉利欽要想在政治上立住腳,必須要得到這個集團的支持。所以俄羅斯的私有化方案,不管怎么做,要通過就必須得到這個集團的認可,這是當時葉利欽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制約。中國不同,中國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都是“黨管干部”,誰也不敢說你這個國有企業一定要賣給我,要不我就不給你干了,他們沒有這么強的談判能力。 當然也有類似的地方,比如中國經過1980年代的放權讓利以后,國有企業所謂“內部人控制“的情況也非常嚴重,后來自賣自買多數也都是國有企業廠長經理自賣自買,包括MBO。他們的談判能力也非常強,但是沒有強到俄羅斯那種地步。俄羅斯的這個集團在杜馬里是拿著投票權的,你的改革方案他們不高興就根本通不過。最后俄羅斯的私有化設計出來三種方案,這三種方案都很巧妙,都有希望在杜馬里得到通過。三種方案的要害都是把大部分國有企業的分紅權分給企業的管理層和職工,只不過代價不一樣,比重不一樣,而且三個方案都是讓企業自己去挑。結果70%的企業最后挑的是第二種方案,就是企業的廠長經理加職工可以拿到51%的控制權,但是要溢價70%來買這些股權。第一種和第三種方案的特點就是,基本上他們花錢不是很多,但是沒有控制權,第三種就是有控制權,但是你要按賬面價值的170%來買。最后絕大部分企業都選擇了第二種方案,就是我寧愿出錢,我也要控制。所以最后俄羅斯私有化實際上就是“化”給了內部人。在這過程當中不公平的現象就多了,尤其是那些廠長經理們,雖然說是把股份分給工人了,但是他們有很多辦法把工人的股份拿過來,比如他故意不給你發工資,你最后沒錢只好把你的股票賣掉。我的一位當時駐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后來講故事說,其實用不著那么復雜,就是下班的時候,弄幾個彪形大漢,拿著木棒站在工廠大門口,然后門口貼一個廠長辦公室的公告說,考慮到大家今天分的股份帶回家不安全,建議大家放在廠長辦公室替你保管。工人一看這架勢就明白了,就都放過去了,就這么簡單。當時俄羅斯的社會狀況跟我們“文化大革命”類似,就是無法無天,所以那時候你也談不上多少制度建設。 《商務周刊》:這20多年來,經濟學界對俄羅斯轉軌的評價基本都是“不行”,但對“中國模式”評價還挺高,應該怎么來認識中國現今的處境及其未來要走的前人沒走過的道路? 張春霖:“華盛頓共識”在俄羅斯和東歐轉軌中失敗了,這應該是毫無問題的,是共識。但中國模式是不是就行?只能說到現在為止是行的,將來行不行意見有分歧。有的人認為不可持續,最典型的就是那本有名的《中國的崩潰》,這本書認為中國到現在一切都好,但過幾年就崩潰了。我自己也認識一些這樣的人,10年來一直就在那里等著中國崩潰。 到目前為止中國是成功的,這應該是多數人的共識。國際上絕大多數人還是承認中國的改革不僅經濟增長是成功的,而且減少貧困也是成功的。中國減貧的成功在人類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我經常引用這樣一個數字,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們統計出來的數字,就是大概從1981-2001年這20年間,全世界的貧困人口減少了3.6億,而中國減少了4.2億。為什么全世界的數比中國還少呢?因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這20年貧困人口是增加的。印度大概只減少了幾千萬,所以,這20年全世界貧困人口減少主要的貢獻來自中國。中國減少的貧困人口的總數相當于現在非洲和拉美貧困人口加起來的數字。 中國經驗并沒有顛覆主流經濟學 《商務周刊》:正因為中國與俄羅斯相比改革更加成功,因此有經濟學家認為要重新認識主流經濟學。比如林毅夫最近常在一些會上認為,要對主流經濟學暗含的假設條件進行重新思考。您怎么看待這樣的觀點? 張春霖:我也注意到了媒體對林毅夫教授觀點的報道。現在有相當部分人認為,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的成功。比如雙軌制這樣的概念在經濟學上就沒法解釋,一個東西怎么可能有兩個價格呢?但中國就搞了,而且成為很重要的一個成功的機制創新;鄉鎮企業產權是不清晰的,但鄉鎮企業是19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推動力量。所以由這些反過來看,傳統的經濟學需要反思,有可能它有些地方錯了,有可能中國走出了一條經濟學無法解釋的道路。 確實有這樣的觀點,但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我覺得中國沒有那么神奇,還在地球引力的控制之下,沒有飛出去,只不過看你怎么去解釋它。現代西方經濟學是一種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個藥方的集成,不像翻開醫書就知道感冒了要喝麻黃桂枝湯,然后麻黃幾錢、桂枝幾錢都給你開好了。其實你去問問醫生,他也不是這么干的,他也是把醫書裝在腦子里,然后根據你的病情來開藥。如果說翻翻醫書就可以解決問題,那大家都成為醫生了。經濟學也是一樣。 所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原理有一個怎么運用于實際的問題。舉例來說,私人產權在企業這個層次上,它就是對一個企業的私人所有權,其要害在兩件事情,一個叫剩余索取權,一個叫剩余控制權,也就是分紅權和控制權。用這個概念來看一下我們1980年代的放權讓利,大家都承認國家所有制沒有改變,但從經濟學上來講,它其實已經是產權改革。放權就是把所有者應該掌握的一部分控制權下放給企業的廠長,讓廠長和國家分享控制權;讓利就是讓廠長、職工和國家分享分紅權,國家賺了錢以后不是都給國家,大家都分一點。所以為什么國有企業在所有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就有非常強烈的利潤動機了?包括現在有的國有企業,即便還是百分百的國有企業,它也拼命想賺錢,這種利潤動機從何而來?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是不想賺錢的,因為首先賺了錢不是我的;其次,我想賺錢也賺不了,我看到市場上缺這種東西但國家計劃沒批,我沒有原材料,沒有煤,沒有電,我招個技術工人都招不進來,沒有這個決策權。改革開放以后,即便是所有權沒變,國有企業也有利潤動機了。為什么?因為控制權和分紅權下放下去了,就是經濟學上說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給到他們手里了,所以你就看著它有點像私人企業了,它也想賺錢了,這就是經濟學原理。實際上看你怎么去解釋。你可以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它也有利潤動機,所以經濟學在這個地方失效了。但你如果抓住了經濟學核心的精神去看,它為什么想賺錢?就是因為它得到了一部分剩余控制權和索取權。而正是因為它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它并不是企業的真正所有者,并沒有自己的資本投入到這個企業,所以它的利潤動機非常強烈,但仍然是負盈不負虧。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種國有企業就有強烈的投資沖動,強烈的貸款沖動,強烈的上項目沖動,因為貸款上項目賺了錢大家都有份,賠了大家都沒事。你看,經濟學不是仍然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嗎? 所以我的看法,這些現象用經濟學的道理都是可以解釋的,沒有奇跡到不能解釋的地步。我不認同好像說整個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被中國的經驗所顛覆了似的。我比較贊賞斯蒂格里茨、科爾奈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當然了,你要說解釋中國的每一個事情,那也有很多困難,需要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理解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和經濟學原理之間有什么聯系,而不是說拿來就可以套用。但我想這個事情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這樣,就是拿西方主流經濟學去解釋法國和美國為什么不一樣,那也要費很多勁,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評論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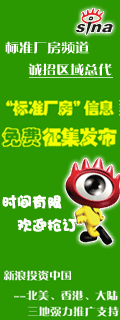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小女子開店50天賺30萬 |
| 介入教育事業年賺百萬 |
| 新型建材 月進10萬 |
| 女人錢,怎么賺 (圖) |
| 二折提貨,千元做老板 |
| 韓國親子裝?日賺30萬 |
| 我愛美麗招商!加盟! |
| 品牌折扣店!月賺30萬 |
| 泌尿疾病!特色新療法 |
| 拒絕結腸炎!! 圖 |
| 皮炎!濕疹!蕁麻疹!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發現! |
| 高血壓!有了新發現!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