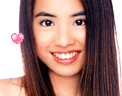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嚴重誤導了改革方向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2月16日 11:34 新浪財經 | |||||||||
|
李慧 經濟學家吳敬璉“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改革的四大缺陷:缺陷一是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缺陷,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壟斷行業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缺陷二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缺陷三是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
經濟學家劉國光在接受《商務周刊》記者采訪時,特別談到了應當“主張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強調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平精神和社會責任,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就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 而在春節前一個以城市貧困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提交的在不同區域做的調查報告,都給出一個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并沒有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表現出明顯地加重。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作為國家權威機構也正式公開表態,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但是,如果把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則實際基尼系數就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了。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改革似乎已經到了“山重水復”的地步了。吳敬璉認為,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行政腐敗擴散等造成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并引起了部分群眾對現實生活中消極現象的強烈不滿。而對改革的認識,實際上集中在“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中國過去改革的成敗得失”這兩大主題上。但無論是社會上的反思也好,爭論也好,似乎都存在過分籠統而沒有對問題作具體分析。譬如說關于醫療改革的爭論就很不明確。 的確,關于改革的爭論不是今天才有的,自從中國改革誕生的那一時刻開始,人們對中國改革的研究就沒有停止過,關于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可謂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棟,其中,既有對改革成功的稱頌,也有對改革問題的尖銳抨擊,還有對改革過程的總結回顧,但是,每當我們試圖想要從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大多要么是作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要么是對過程做一個簡單回顧,很難從根本上說明問題。 所以,當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到攻堅階段的時候,特別是改革仍然“攻而猶堅”的關鍵時刻,我們卻遽然發現,盡管改革已經經過了20多年的實踐,盡管改革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盡管我們到處都在講改革,但是,我們對改革究竟是什么卻仍然非常模糊。這些現象已經急迫地向我們表明,從“摸著石頭過河”一路走來的中國改革,亟待地需要一個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香港學者郎咸平突破性的研究結果表明,現在的問題并不是反對改革的問題,也不是否定市場化的問題,而是要尋找改革的路徑依賴問題。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認識下,“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成為人們爭議的焦點和中心。 為什么當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倍受歡迎,而今天同樣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卻是 “攻而猶堅”呢?研究改革的人大概都忽視了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當年的“摸著石頭過河”依靠的是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豐富的實踐經驗,特別是貫穿在實踐中的一套完整的、具有“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的科學方法,以及緊密依靠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的路線,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改革遇到的阻力,從而輕易地化解了諸多復雜的改革難題。鄧小平這種解決問題的系統實踐,特別是解決復雜難題的高超技巧,使他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燈塔。 但是,當改革走到了今天,現實已經為我們創造了相當寬松的環境,而改革也亟待著系統的理論突破和實踐指導的時候,當我們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來衡量改革的時候,才發現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嚴重地誤導了改革的方向,不僅偏離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而且,對西方經濟理論與管理行為的實踐也是生吞活剝般地理解。事實表明,對于改革這樣一個大課題本應當是很有研究價值的,但迄今為止,尚未見到把改革作為一個大課題全面而系統地來研究的專家學者,反倒是局限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爭論著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甚至相互攻訐的事情卻很常見。 特別是看了“郎咸平主持國資委改革,也許效果會更糟”一文,真為某些學者的無知與悲哀感到汗顏,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論研討,而是非常露骨的人身攻擊;而個別借著為“主流經濟學家”辯解,被人們評價為“企圖炒作自己”的學者,更是說出了這樣弱智的話:“在目前階段,讓獲諾貝爾獎的國外經濟學家到中國來,也未必就能適應這片土壤。”這樣無力和不負責任的辯白,更是暴露出了“主流經濟學家”的無奈與尷尬。妄談改革,卻不能深入地研究改革,并把改革作為一個大課題系統而全面地研究,這究竟是改革本身的問題,還是研究改革學者自身的悲哀呢? 中國第一個哈佛經濟學博士張培剛先生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我們應該高度關注這一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研究中國的經濟學不僅要從經濟因素的角度研究,更要重視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非經濟因素和歷史因素,因為中國的復雜情況決定了它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場非常復雜和艱難的過程。2005年之所以成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滑鐵盧”,恰恰是因為改革已經到了最關鍵的階段,同時,也表明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如同20世紀初人們試圖將儒家文化逐出中國主流文化的努力是一樣的,而這正是推進改革前進所必須的過程。 現階段,大家都在談反思改革;都在講在對中國改革系統反思的今天,重思改革的發展方向是十分必要和現實的問題。但是,究竟要反思什么卻很不容易判斷,因為只要你一提出你的理論觀點,比如就象“郎咸平現象”一樣,立刻就會成為無數人攻擊的“靶子”,什么“出身論” 、“資格論” 、“動機論” 、“炒作論” 、“無知論”等無數頂嚇得驚人的大“帽子”馬上向你扣來,但遺憾的是,爭吵到后來,反而不知道爭吵的原因是什么了。因為現有的大多數理論僅僅討論了這些問題混亂過程的邏輯現象,卻沒能從根本上清楚地告訴我們問題的本原是什么。所以,每個人就都在按照自己五花八門的理由詮釋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很顯然,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慣用的那種研究方法已經過時了,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受人詬病的原因正表明中國需要一個新的開始。所以,最應當反思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沒有人能把改革作為一個大課題系統而全面地研究?特別是為什么沒有人能真正從經濟、人文和歷史的角度而不是單純從政策的角度來研究,是從規律性的事物本質研究而不是僅從表面現象淺嘗輒止的研究?這其中大概有三個重要的原因: 首先,因為改革是一個“牽起蘿卜帶起泥”的復雜難題,從很多側面認識改革、研究改革都可以做到,但是,每每當你要深入探究的時候,各種各樣的問題就象火山爆發般地出現了。尤其困難的是,往往對改革的研究是從經濟現象的研究開始,結果卻不能獲得單純的經濟結論,而是涉及到了很多與經濟無關的理論和行為,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廣博的知識和敏銳的判斷能力,并能不斷深入地研究下去。 其次,對于改革的認識往往會受制于習慣性思維的影響,把改革中點、線的問題,做為一個課題研究是普遍的,但是,把改革作為一個面上的系統問題來研究卻是難以想象的。“改革”這個題目說起來很小,做起來卻大的不得了,這不僅要受到習慣思維上的限制,還要受到現實環境的制約,很少會有人敢把“破解改革之謎”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因而,需要研究者有系統思維的觀念和敢于從根本性問題著手的勇氣。 第三,對于改革的認識往往會受制于研究方法的限制,從一般規律性的研究方法入手研究改革是容易作到的,但是,要做到對改革的認識具有前瞻性、原則性和規律性的認識,就必須要有自己獨到的理論和思維。因為嚴格來講,與西方經濟學相比,中國尚沒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因而沒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們一般慣用的理論研究方法,經常是緊跟政策的走向,而不是為政策提供理論方向,這就注定了對改革問題的研究會經常流于膚淺的表面,很難打破一般的研究怪圈。 所以,把“破解改革之謎”作為研究題目,一般的專家、學者是難以做到的,那些只知道緊跟政策而沒有自己理論的人也是難以做到的,那些只知道為了職稱而研究的、被稱為“主流經濟學家”的人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真正是以天下為己任者,不懼付出,才能挑起這個重任。而“破解中國改革之謎”不在于誰做,而是因為要做這個題目,你就必須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角度看問題。曾有國外學者指出,如果有人能夠破譯了中國的改革之謎——這個現代經濟發展史上最大的謎團,誰就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獲獎另當別論,雖然中國人至今還沒有與這個世界最高獎有過緣分,但至少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具有相當難度,并極其復雜的經濟難題。 在探索“破解改革之謎”的過程中,我感到保持一個學者思想的獨立性是最重要的,而這種獨立性常常是發現和創新所不能缺少的。但是,對于追名逐利之徒和沉湎于世俗的“鉆家”而言,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而最讓我感到困惑和迷茫的是,我們過去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中,常常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缺陷,這種缺陷則是因為文化的混亂和自相矛盾、欠缺嚴謹的邏輯體系所帶來的。一般認為中國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主流文化,實際上中國文化不是哪種所謂的主流文化可以代表的,而我們過去理解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精英文化。 遺憾的是,考察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多學者僅局限于漢文化狹窄的范圍和偏重于對精英思想的研究,既沒有明確清晰地達到一個公認的“高標準”,更缺乏用這些“標準”分析判斷文化發展過程的“嚴要求”。從文化繼承的角度來看,假如我們沒有找到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和生命,更不了解文化的內涵本質,卻用某些歷史形態或一些經過修飾的“精英文化”來代表中國文化的全部,就會將中國文化淪為文明的“被造品”,更確切地說,就是將文化繼承變成文化褻瀆,不僅不會有創新和發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當我們仔細地對中國文化深入地研究的時候,才發現現行的種種文化與真正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事情。 儒家文化的實質究竟是什么?在三國時期出現的反映孔子生平事跡的《孔子家語》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孔子有著復雜的思想軌跡和多重性格特征:他既對自己的才學和信念充滿自信,但又時時流露出英雄失落的悲哀;既渴望理想被現實所接受,又不可避免地發生動搖;雖對現實人生有著積極的處世態度,同時也表現出迷茫和彷徨。在儒家文化中既有“舍身取義”(《孟子》)的大聲吶喊,也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論語·泰伯》)的逃避和規勸,這充分暴露出中國文化的整體觀與其脈絡之間是一種割裂的關系。所以,從儒學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在當時諸侯紛爭、餓殍遍野的社會背景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獨立思想的,孔子的理想和報復也是很難實現的。盡管儒家思想理論的實質是針對當時社會一種很強的實踐哲學,但其個人行為的反復不定,導致了思想理論體系的先天不足和內容的薄弱,自然也就不會有通達濟世的功能,更指導不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孔子結合當時的現實總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在國家政治清明時,言行就要正直,否則就應當謹慎。他還身心俱憊地感嘆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孟子雖然繼承了孔子的學說,卻采取了與孔子截然相反的做法,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認為不仁不義的君主不能算君,可以殺掉。“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不過,孟子生前的學說被視為“迂闊”,與孔子的學說一樣不被人重視。在孔子所處的時代,是沒有真正的道理可言的,曾經有人問過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當權者不喜歡你呢?” 亞里士多德回答說:“因為掌權者從來不喜歡那些比他們聰明的人——這是所有統治者的性格特征。”這里,一個同時代的外國人回答了孔孟的疑問。 然而,有趣的是,被人們視為儒家經典,僅用半部就可以治理天下的《論語》,竟然不是出自孔子的得意門生,而是一些他不太看重的愚笨弟子,這些弟子對孔子的尊崇無形中達到了這樣一種結果:使孔子本人被神化了,而孔子學說中仁學的思想精髓卻被曲解教化了。中國歷來是一個政治熱情多于民主熱情、并且是“政教合一”的國度,其結果是落實到了皇帝的絕對專制上,“贏家萬世是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陳獨秀詩)。以儒家文化為主流文化的中國文化背后,實際上就是一種皇權文化,特別是自從漢武帝“罷黷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后世將孔子視為圣人,尊崇無比,甚至超過對孔子學說的崇拜,而對真正意義上孔子學說的繼承和理解卻背道而馳,并把與孔子學說毫不相干的“三綱五常”以及宗教儀式一類的繁文縟節奉為圭臬。從而把尊孔變成了歷代帝王倒行逆施的招牌,以至陳獨秀說:“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憲,勢必復辟”。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治亂相循的歷史就是一部王權發展的爭斗史,除了抵御外來侵略以外,中國的經濟、文化(包括我們所看到的儒家文化)和民權思想都只不過是依靠在封建統治上的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最終都成為政治斗爭的附屬品和犧牲品。儒家思想的一統天下將中國文化引入到了一個更大的誤區之中,這個誤區就是人們不能從客觀現實和事物本質的角度理解儒學,卻形成了對儒家文化教派式的理解,以至后人對孔學宗教般虔誠式的詮釋雖易于被國民接受,但卻使人無法對事物的本質作出理性的思考,更無法清醒地使我們認識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雖然也曾有人對中國的文化提出過質疑和批判,但不是被統治階級所壓制埋沒,就是沒有觸及到中國文化的實質,僅僅是一種并不徹底的批判。 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主流文化最終是形成了嚴重的“文人政治思維”,而這種深厚的“文人政治思維”傳統,最嚴重的后果就是直接導致了非理性的思維存在,在政治上形成了虛幻的理想行為,在經濟上表現為不顧經濟規律的要求,在思維方式上直接遏止了創新的進步,最終形成的結果是制造了大規模的、長期的不公正行為,直接使中國的文化變成了歷史的糟粕,而這種余毒至今還在蔓延。所以,在政治上我們始終沒有掌握真正的憲政結構精髓,以至于忽視了公共管理體系的建設;在經濟上始終沒有關注到經濟的結構平衡和調節平衡的能力,以至于只是簡單地注意經濟的增長和衰退;在思維方式上始終把發展當成了創新,但實際上發展不等同于創新,發展只是一種漸進式的進步,而創新則是跳躍式的發展,所帶來的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思維觀念的更新。因此,理性、和諧、創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影響,對一個國家進步的意義更為重大和明顯。 恩格斯說:“一般針對封建制度發出的一切攻擊必然首先就是對教會的攻擊。”何新在《中西學術觀點比較》一文中斷言:“在中國的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存在過獨立于時代政治意識之外的學術文化體系。”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之所以掀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頁,就是因為這場運動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深刻批判和哲學反思的基礎之上。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那場“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我們至今仍記憶猶新,這場由民族狂熱所引發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混亂,雖然幾乎讓歷史停滯不前,但卻在“文化大革命”這場空前的浩劫結束以后,迫使中華民族不得不對自身的文化進行徹底的反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帶來了中國人思想上的又一次大解放。對“兩個凡是”的思想障礙、“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以及“公有私有”的思想桎梏的一次次突破的結果,從而短短幾年就進入了全面改革開放的社會變革時代,迎來了中華民族在21 世紀復興的偉大事業。 那么,支撐著中國幾千年文化發展的究竟是什么?其實,只要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并不是儒家文化所能夠代表了的,支撐中國文化發展核心內涵的并非是儒家文化,更不是皇權文化,而是另外的一種底層文化在支撐著中國的發展。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戰國時期與孔子學說相對立的墨子學說影響很大,與儒學并稱為“顯學”,即主流學派,雖然墨子的學說不像老莊孔荀那樣成為戰國文明表層的光輝,但卻是這一時期文明的深層基礎核心。墨子作為戰國文明中以追求理性和科學探索精神為基礎的思想代表,其研究內涵正是構成文明基礎理性活動的實質,在此科學探索精神基礎之上繁衍出來的古代發達的科技和實物科學,在另一層面填補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缺憾,它本身的輝煌同時也為中國文化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不僅制造出許多杰出的藝術成就,而且衍生出中國民族精神的深層內涵。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歷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借鑒。”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們大概都忽視了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真正推動中國古代輝煌的實際上是古代發達的實用科技和底層文化,而不是中國封建的政治制度體系。科學探索精神與政治、經濟雖然有很大關系,但它始終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既不會因為政治的變化而呈跳躍式的發展,也不會因經濟的豐富而改變。所以,科技水平的高低并不代表社會政治的發展程度,尤其是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經濟時代,科技的獨立性作用更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古代最發達的是實用科技和文化,因為這些已經形成了一種完整的體系,而專家學者作為重點研究的古代系統的管理思想和制度體系,實際上卻是凌亂不堪的,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所以,我們不能用古代發達的實用科技來掩蓋落后的管理制度,也不能用封建的落后制度來代表當時的科技發展水平。 盡管與儒家越來越被推崇的地位相比,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科技的蔑視,在客觀上造成了墨家學說的衰落,可因為墨家學說本身就是源于社會最底層的深厚根基,并確立了以自然科學和邏輯思維為研究對象的目的,再通過手工匠人獨特技藝的代代相承,使其外在衣缽的存在具有了獨立性和可持續性的發展。直到今天我們在考古發現中古代的一些科學成就,仍然是我們現代科技所無法達到的,這就證明了墨家學說雖然由顯學轉為了隱學,但始終頑強地在社會的基礎層面支撐著中國社會的平衡,這種高度發達的民間科技和豐富的實驗技巧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的另外一種文化核心。所以,中國歷史的輝煌真正開始于墨家,而不是儒家。比如印刷、火藥和指南針三大發明都出現在北宋,這是中國古代科技的一個飛躍時代,但北宋卻是中國封建統治最混亂薄弱的時期。有人將中國古代發達的科技實物技術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結構相聯系,將“文革”時期“兩彈一星”的技術成就與當時的政治氣氛相掛鉤,其根本原因是在本質上混淆了科技發展與政治需要之間的關系。 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戰勝東方文明,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科學理性的思維基礎之上的,盡管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但是,西方社會對科學的尊重是任何社會都無法相提并論的。對科學的尊重反映了人類理性精神的回歸,而這種理性的思考正是西方憲政制度、宗教改革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出現的基礎,這也就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終戰勝東方文明的真正原因,除此而外不可能有任何別的解釋。同樣,中國古代發達的實物科技也表明,由于中國古代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限制,戰國以后墨家文化并沒有真正的衰落,它不是以儒家文化那樣被歪曲篡改的形式來體現自身的價值,而是以另外一種實物形式在頑強地體現著與強權政治的抗爭,以極高的“生存智慧”延續了中華五千年社會的發展,從而,在另一層面成為支撐起中國文化的精神脊梁。 一個社會理性精神存在的多少,主要看這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反映了民意。歷史與現實之間最大的矛盾,就是我們總在回避具體的問題,似乎像孔子重新編改《春秋》做到“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為賢者諱”,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以至于有人從另一方面談到說,假如中國沒有孔子,中國的發展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歷史的經驗證明,凡是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期一定是最開放、最和諧的時期,而凡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敗的時期,一定是最保守、最喪失理智的時代。開放是進步之源,封閉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前提條件就是開放,必須充分的開放。無論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離開了徹底的開放,結果必然是趨向保守和落后;也無論是官僚政治,還是精英政治,都必須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礎之上,這樣才能保證政治制度的先進性。 鄧小平曾經指出,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胡錦濤總書記也特別強調:“要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最廣泛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團結奮斗。” 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利普塞特命題”,即民主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模棱兩可的,但經濟增長卻對民主化有著實實在在的影響,也正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全球民主化的進程得以加快。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經濟的話語權已經被重新奪回的時代,經濟已經開始對政治發生了極其深遠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人力資本優勢已經被挖掘殆盡的時候,制度資本則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而這種制度成本主要指的是道德素質、公共管理和人文環境而言。 所以,在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郎咸平現象”問題上,就郎咸平先生的個人力量來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闡述的事實卻極具沖擊力量的,所以,我們看到網友對郎咸平先生理論的熱烈追捧,而不是對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這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回歸,也是中國從改革開放走向開放變革的新標志。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命題是永遠不會動搖的,而人民締造并改變歷史的真理也永遠不會改變的。透過歷史,改革的路徑依賴究竟在那里不是很清楚嗎?“如果說有‘主流’這一說法的話,那我才是真正的‘主流’,而我的意見不能成為主流那是國家的悲哀。”郎咸平先生微笑之間,輕拈指尖就破解了這個由那些“主流經濟學家”設置的“魔戒”難題。 新浪網聲明:新浪財經登載此文出于傳遞信息之目的,絕不意味著新浪財經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評議學人 > 正文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開家麥當勞式的美容院 |
| 名人代言親子裝賺錢快 |
| 年賺500萬輕松實現 |
| 06年暴利項目揭秘 圖 |
| 千元投資,年利百萬! |
| 足不出戶 月賺30萬 |
| 原生態家居飾品招商 |
| 100萬年薪招醫藥代理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最新療法治結腸炎!! |
| 治氣管炎哮喘重大突破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治高血壓獲重大突破! |
| 糖尿病——重大發現!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