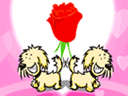開平教訓:從集體腐敗到集團腐敗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8月22日 15:01 和訊網-《財經》雜志 | |||||||||
|
來自銀行外部的強力推動是打破集體腐敗和集團腐敗真正防范金融危機的惟一路徑 □ 本刊研究員 陸磊/文 細看余振東的起訴書,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金融腐敗個案與一般腐敗的兩大個性特征。
一是集體腐敗,即整個中國銀行開平中行計劃、會計、外匯、信貸和財務系統已經徹底成為腐敗交易的載體,遠遠超越了一般腐敗行為中的主要負責人或關鍵崗位人員的個人行為,因而腐敗行為是公開而非隱蔽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種公開的腐敗行為,卻并非直接為中國銀行歷年的內部稽核及監管部門的現場或非現場檢查所發現,而是被國家審計部門在八年后的一次常規檢查所揭露。這說明了部分銀行內部已經成為集體腐敗的利益共同體。 二是集團腐敗,即中行開平中行具有團結并動員當地數十家企業為其貪污、洗錢提供渠道服務。一個起碼的直覺是,企業提供腐敗通道并非不存在風險,任何理性的經濟主體都不會在不獲得風險貼水的前提下承擔風險。因此,這一畸型的銀企借貸關系說明,在銀行和借款企業之間,已經結成了集團腐敗的利益共同體;一旦兩層次的利益共同體在銀行系統滋生壯大,地下的非規范金融交易取代了正常的信貸行為,潛規則取代了所謂的“金融三鐵”(鐵款、鐵賬、鐵算盤),銀行業勢必成為一筆糊涂賬。 在這樣的糊涂賬目下,誰是犧牲者?顯然,如果沒有不斷膨脹的居民存款增量注入,沒有國家的注資和不良貸款剝離,銀行的腐敗交易必將導致嚴重的流動性問題乃至金融危機。 經歷20多年的改革而中國奇跡般地幸免于金融危機,這并不能讓我們寄希望于下一次僥幸。銀行治理結構對金融穩定的關鍵性顯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具體落實到余振東等既得利益者身上的時候,我們很難看到“真改革”的跡象。 銀行改革需要來自銀行外部的強力推動,這是打破集體腐敗和集團腐敗、真正防范金融危機的惟一路徑。 集體腐敗:銀行支行的腐敗網絡 從起訴書看,中行開平中行套取、挪用聯行資金起源于1993年10月11日,這一金融腐敗案件的第一個關鍵點是永平賬戶。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該賬戶是少數行長的私人金庫,事實上,它是中國銀行開平中行的小金庫,也是該支行用以賬外經營等各種不規范金融操作的首要載體。從中國銀行開平中行貪污現金流量圖可以看出,永平賬戶成為腐敗資金分配的主渠道,幾乎全部資金往來均與該賬戶存在直接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從永平賬戶開戶、永平賬戶向企業貸款、利用多個企業賬戶轉賬、向境外匯款等一系列程序,需要涉及該支行的會計、信貸、財務、外匯等不同部門在違規操作中的配合與協調,僅憑行長的指令斷難完成整個系統操作。這說明永平賬戶與整個中國銀行開平中行利益攸關。 當然,行長責任大固然拿“大頭”,一般參與員工獲得福利上的好處是符合“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的打家劫舍規則的。正是由于各位當事行長在對員工出手上的豪闊,以及基于對“首惡懲辦、脅從不問”的司法預期,整個中行開平中行成為金融黑社會,各類風險偏好均能各得其所——行長在金融腐敗中處于高風險、高收益地位,一般干部則處于低風險、低收益境地,風險-收益在開平中行實現了奇妙的市場均衡。 由此產生的后果是有趣的——為什么三任行長是一丘之貉且八年腐敗沒有從內部暴露?這說明在這一均衡機制下,各方均希望具有腐敗傾向和冒險傾向的人出任行長,這意味著員工福利和集體利益。可以說,這是集體行動及集體選擇的邏輯。 腐敗案件的第二個關鍵點是香港潭江公司和友協公司。早在1991年11月,余振東、許超凡、梁樹相等人就在香港成立潭江公司有限公司;1993年2月,許超凡等人成立香港友協公司有限公司,兩公司主要經營物業、外匯、股票、期貨指數買賣,同時亦為余振東和許超凡、許國俊提供賭資。 可以說,這兩家公司是涉案當事人投機和揮霍的載體。從中國銀行開平中行貪污現金流量圖和中國銀行開平中行挪用公款流量圖可以看出,涉案主要資金的最終流向集中于上述兩家公司。需要關注的問題有兩點: 一是為什么在1991至1993年間成立上述公司。當時是賬外經營和逃套外匯最盛行的時期。從賬外經營看,商業銀行普遍利用信貸資金管理漏洞設立小金庫,對企業實施違規放貸。中行開平中行在境外設立公司從事投機金融交易的目的無非在于,與其看著賬外經營的貸款客戶盈利,不如“甩開膀子自己干”。通過永平賬戶和香港公司,中行開平中行實際上建立了自己的賬外經營封閉資金環流——資金從余振東等銀行控制者手中轉移同樣是余振東等境外實體的控制者手中,真正實現了“肥水不流(或少流)外人田”。 二是為什么在境外設立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銀行是主要的外匯指定銀行,甚至可以說是壟斷外匯金融交易的專業銀行。在1994年1月1日匯率并軌之前,人民幣一度因國內投資膨脹所導致的進口潮和資本外逃而出現了在外匯調劑市場上持續貶值的傾向,套取外匯、囤積外匯以盈利是不少經濟主體的直覺。在境外設立機構,一方面便于發揮中國銀行在外匯業務上的便利優勢,可順利實現外幣資金轉移,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境外機構實施外幣操作。 同樣,從“中國銀行-永平賬戶-香港公司”的三角關系看,資金實現真正的封閉環流,在中國的外匯管制條件下是很難具備可操作性的。我們發現,該支行結匯股等核心部門的主要干部均參與了制作假憑證、轉移資金操作;盡管上級對下級的行政壓力是一種可信的解釋,但是經辦人員在沒有收入激勵的前提下依然不具備參與洗錢的現實可能性。 可見,開平案的典型性在于,一旦金融腐敗從行長轉移到全體或大部分操作員工,銀行就進入了癌細胞擴散的癌癥晚期,整個機構陷入不可救藥的地步。 集團腐敗:銀企關系的腐敗網絡 無論開平中行的貪污現金流還是挪用現金流都顯示,開平市的主要骨干企業集團成為從貪污到洗錢的主要參與者。可以觀察到,在兩大現金流程中,開平滌綸集團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主體。據調查,開平滌綸集團資產規模位居全國五百強,擁有開平惟一的上市公司——開平春暉,是當地最具影響力的支柱企業,有著廣泛的國際業務往來。 第一步是賬外經營。從1993年開始,中行開平中行就向滌綸集團和其他企業發放賬外貸款,并利用滌綸廠名義開立賬外經營賬戶。銀行-企業之間形成了賬外經營的利益共同體。對企業而言,1993年是國家三年宏觀治理整頓的開始,資金緊張特別是外幣資金緊張,是許多企業面臨的基本問題。中行開平中行恰恰利用了企業對資金的渴望,而賬外經營實際上就是對企業貸款實施高利貸,同時把價差收益(高利部分)劃歸銀行小集體乃至個人的行為。 單純從經濟學意義上看,高定價是對供求關系的客觀反映,本不足為奇,甚至是利率市場化的自發表現,符合市場經濟基本原則。但是,中行開平中行與一般賬外經營相比的惡劣之處在于,許超凡、余振東等人不僅吃高利,甚至試圖吃本金。而企業并不關心銀行經營者是否吃本金,只要能獲得貸款,愿意為銀行提供任何渠道協助——畢竟銀行對企業是有貢獻的。此類尋租行為就是銀行利用金融資源稀缺性進行的腐敗交易,而銀行和企業在各取所需當中實現了市場均衡。 從起訴書看,涉及賬外經營的遠非滌綸集團一家,華士達制布企業有限公司、永平合成纖維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均與中行開平中行存在賬外經營關系。賬外經營是銀行-企業私相授受的主要模式,是銀行脅迫或激勵企業與之共謀洗錢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協助洗錢。在通過信貸關系建立利益紐帶后,洗錢成為企業把賬戶“借”給銀行使用以洗錢的必然邏輯。這一步驟又可以分為兩步: 一是虛假貸款,如1998年9月,由被告人余振東、許國俊向開平金城陶瓷有限公司、開平織布廠、平豐織布企業有限公司、華士達制布企業有限公司、新安達輪胎有限公司、開平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企業的負責人提出配合辦理貸款的要求。在八家企業同意的情況下,被告人余振東與許超凡指使下屬工作人員,以上述八家企業的名義辦理虛假貸款15筆,合計金額人民幣2億7932萬元。當然,更多的虛假貸款,均是通過與中行開平中行關系更為密切的滌綸集團進行的。 二是向境外洗錢。中行開平中行或者通過間接利用企業與香港公司的虛假交易向境外匯款,或者直接利用企業向地下錢莊購匯并匯款到境外(參見圖1、圖2)。 第三步是參與分肥。上述虛假貸款中的1億8576萬6218.83元通過地下錢莊被非法調成美元和港幣,匯入香港潭江公司用于投資經營和被告人余振東等人的個人投資消費之用。這是扣除租金的行為,即銀行向企業支付了利用其賬戶渠道、實施虛假貸款的風險貼水,剩余的巨額人民幣資金實際上成為企業信貸。而圖1和圖2所顯示的大量利用滌綸集團進行的洗錢均未發生直接租金,資金原封不動地轉入香港兩家公司賬戶。其原因在于,銀行與企業之間存在跨期交易關系,事實上的“分肥”行為在洗錢先后不斷發生,銀行可以不針對某一筆具體的洗錢行為支付對價。 銀行與企業成為一個腐敗集團所給我們的啟示是多層面的。 一是銀行和企業的利益共同體并非一時一刻所能確立,需要銀行人事和企業控制者存在長期的穩定。中國銀行開平中行能在近十年間不斷利用滌綸集團等多家企業開具假貸款申請,實施向境外洗錢等高風險操作,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一方面,三任開平中行行長均是開平本地人,且作為當地金融界“名流”,很容易與企業界“名流”建立良好的機構和私人關系。我們發現,余振東等人與滌綸集團的負責人梁樹相具有極佳的私交,這無疑得益于雙方的人脈。另一方面,無論企業人事變動還是銀行行長更迭,對銀企利益共同體均意味著風險,一個值得進行深度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銀行行長或企業負責人更換,往往是案件曝光率最高的時點? 二是所謂“好企業需要金融支持”是一個冠冕堂皇下掩蓋腐敗交易的最好借口。無疑,滌綸集團是開平市的好企業,好企業是銀行追逐的對象。從八年的案件演進史可以觀察到,中國銀行在滌綸集團發展之初就給予了賬內、賬外的多渠道金融支持。 值得警醒的是,越是好企業,越值得關注非正常銀企關系的發展。德隆、啤酒花等個案反映,不少金融機構(包括治理結構相對較好的股份制銀行)的不良資產均是所謂好企業帶來的,這是因為,上級行均認為對類似滌綸集團的企業提供金融支持順理成章,而基層銀行恰恰利用這種思維慣性逐步構筑銀行-企業腐敗網絡。 三是脅迫與共謀下銀企信貸關系進入畸型發展的軌道。銀行擁有的是資金,就轉型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而言,資金是稀缺資源,成為銀行脅迫或誘惑企業參與腐敗網絡的有力籌碼,在此情形下,企業往往別無選擇。但是,一旦銀企借貸關系進入集團腐敗體系,貪污、挪用和洗錢的長期橫行是可以預見的邏輯和現實后果。 治理結構與既得利益的矛盾: 改革方法論需要調整 金融腐敗案件給我們的啟示不僅僅是案件治理,更在于其中所體現的金融改革總體方法論問題。 無疑,在2005年,隨著中國銀行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幾乎按照完全復制其前輩開平中行余振東腐敗手法的案件發生,我們的思考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所謂少數負責人的操作風險以及操作風險的治理上;真正的核心問題在于——我們有沒有可能真正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以此形成對銀行內部既得利益者的約束。 但是,在當前的銀行改革中,被改革對象往往同時成為改革方案的實際制定者或至少是參與者、影響者,這導致了改革方案主要著重于解決包括腐敗所導致的銀行財務損失上,真正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確立仍需漫長時日。一方面,法人權力的喪失導致內部人控制問題依然嚴重,腐敗的發生概率取決于行長的道德水平而不是理性動機,既得利益成為腐敗的催化劑。另一方面,法人治理結構的薄弱導致了我們在機制上無法有效遏制腐敗案件的發生,類似開平中行貪污、洗錢案的揭露仍可能是審計署等外部機構的“偶然”發現,而不具備預防腐敗的有效機制。 面對治理結構和既得利益的現實矛盾,改革的方法論需要調整,必須依靠來自外部的強力推動。 第一, 法人應該是最后的買單者,法人代表應該是最后的責任承擔者。 從目前情況看,作為法人的商業銀行總行對分支行諸侯缺乏有效的正面激勵和約束,其原因是法人自身因不是最后的責任承擔者而缺乏真正的監控積極性。作為國有銀行甚至某些股份制銀行,一旦財務狀況不佳就求助于國家(或國有母公司)給予不良貸款核銷、注資;機構法人的主要領導者并不因此承擔經濟、行政或法律責任。整個金融改革層面體現的預算軟約束已經逐步成為造成銀行信貸軟約束和金融腐敗的基本生成機制之一。退一萬步講,即便我們因歷史因素和體制變動而無法追溯前責,至少應對今后的制度建設有一個明確的思路。 第二, 總行-分行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必須通過技術和制度手段加以徹底解決。 開平案證明,銀行腐敗最便捷的資金來源是套取聯行資金,而對聯行資金疏于管理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管理制度上的科層結構導致的上下級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上級行特別是總行很難掌握支行的真實資金流的規范性,這就需要實施事業部制度和組織結構的扁平化;二是恰如我們所論證,銀行-企業的集團腐敗來自企業和銀行人事的高度固定性。 應該說,隨著大量私營企業和上市公司的出現,國家或金融監管部門并不具備調整企業負責人的法理基礎和權力,但是,從金融機構法人看,分支行行長的定期輪崗制度必須加以落實,特別是要建立并真正落實核心崗位的異地交流制度。惟其如此,至少可以遏制集體腐敗和集團腐敗,把金融腐敗限制在個人道德的最低層面,所謂體制性腐敗可以得到真正解決。 第三, 宏觀調控不能制造稀缺,而應是利益導向。 開平案之所以發生,與上世紀90年代金融資源短缺有直接關聯。應該承認,涉案的不少企業在經營和財務上是好企業,但資源短缺導致它們不得不接受金融機構的脅迫或誘惑,淪為貪污、挪用和洗錢的渠道。這無疑是中國金融運行和經濟發展的悲哀。 因此,從廣義思路上,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立足于市場化調控而不是限制投資,融資決策權應真正下放給金融機構和企業;一旦繼續保持數量調控,其結果仍然是人為制造稀缺,就必然給銀行以更大的尋租空間和賬外經營空間。當然,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價格導向有望真正取代數量調控而成為融資交易的利益激勵,金融腐敗有望隨著改革方法論的調整而在改革中實現遏制。- (本文刊于8月22日出版的《財經》2005年第17期)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中行開平之劫 > 正文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開家麥當勞式的美容院 |
| 名人代言親子裝賺錢快 |
| 銷售排行榜:投資必讀 |
| 06年暴利項目揭秘 圖 |
| 小女子開店30天暴富 |
| 猶太億萬富翁賺錢36計 |
| 韓國美味 勢不可擋 |
| 100萬年薪招醫藥代理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最新療法治結腸炎!! |
| 治氣管炎哮喘重大突破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治高血壓獲重大突破! |
| 警惕高血脂!脂肪肝!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