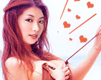誰還知道薩特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7月03日 18:49 經濟觀察報 | |||||||||
|
本報記者 李翔/文 “他像個壯健的、孤注一擲的救生員,花了十年時間拍打福樓拜的胸部,把氣息呼進他的嘴里;花了十年時間竭力想使他恢復知覺,這樣他就能使他在沙地上坐直身子,然后確切地告訴他,他是怎么看待他的。”
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為福樓拜撰寫的傳記《福樓拜的鸚鵡》中,這樣嘲諷薩特對福樓拜所作的評論。而當薩特百歲誕辰到來時,無數個救生員開始試圖拍打這位哲學家的胸膛,為他做人工呼吸,以便能夠告訴他,在他逝世40年之后,人們是如何看待他的——在中國,這種機會并不多,他是正在被遺忘的人,盡管在二十年前,他的名字和他用格言流傳的言論風靡全中國的大學校園。 “你比我們落后了20年,現在還在研究薩特。”23歲的郭小寒譏諷說。即便是薩特那些傳奇經歷、他和波伏瓦之間奇妙的關系,也并沒能把中國年輕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就像20年前他曾經在中國做到的那樣。上一代和下一代對于薩特這個人名的反應,已經成為瑪格麗特·米德所論述的代溝在中國的具體反映:吊帶女孩和長頭發男孩在書店為了紀念薩特專門擺出的書籍面前匆匆而過,他們父母則在書架上試圖尋找自己在20年前有幸擁有的一本叫《薩特研究》的搶手書。 “我們已經過了那個年代,現在已經不是1980年代了。”中國著名的哲學學者之一徐友漁說。他認為這是薩特被現代中國冷落的一個原因。 新啟蒙年代 1980年代——無論它是徐友漁所稱的思想解放年代,還是許紀霖所說的新啟蒙年代——薩特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年輕人依靠他來尋回失去已久的個體意識 “那是一個人們排隊購買《安娜·卡列尼娜》的時代。”徐友漁這樣描述薩特在中國最受歡迎的1980年代。 身處中國社會的人們在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自我封閉和沉默之后,突然井噴出蓬勃的熱情,吸納流傳而入的各種思想,從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到時髦的薩特和存在主義。 同在西方一樣,中國共產黨人先用批判眼神來打量這位意欲同自己結盟的哲學家,盡管薩特對共產黨中國表達了熱烈的贊揚和向往。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已有薩特的書被翻譯引進。當時有一系列介紹西方思想的黃皮書,其中就有薩特的幾本書,不過都作為批判用,只有高級理論家才能夠看得到。”生于1947年的徐友漁回憶說。在做文化大革命研究時,徐友漁發現,紅衛兵一代中有很多人,在文革晚期,開始表現出對薩特的濃厚興趣。盡管在六十年代末期接觸薩特的著作仍然很困難,仍有一批在思想上表現出探索欲望的人能千方百計找到這些作品。 在薩特逝世前后一段時間內,他在中國的聲譽達到頂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正像以英國思想家、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賽亞·柏林所描述的,在一段長時間的幽閉之后,會出現廣場時期,它意味著思想上的開放與探索。這段時期,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對個人崇拜的反思和對毛澤東思想的重新理解。具有代表性的時間是官方媒體發起的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由此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它成為中國執政黨進行改革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 而在民間思想領域,則表現出了巨大的活力。人們表現出的求知欲令人吃驚。一位哲學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體育館開辦哲學講座,滿場爆滿,徐友漁說。這讓人回憶起20世紀最初,中國人擁有同樣強烈的求知欲和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心。當胡適在北京大學舉辦講座講西方哲學時,同樣出現爆滿情形。 研究思想史的學者許紀霖喜歡將1980年代和五四前后作類比,他認為兩個年代和兩個年代的年輕人之間具有很多相似性。 薩特思想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正是在這樣一段許紀霖所稱的“新啟蒙”年代。在當時大學里的辯論中,很多人言必稱存在主義和薩特。“1982年上海演薩特的《骯臟的手》,人山人海。”許紀霖說。 徐友漁稱,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流行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就是階級斗爭和專政,要求對人進行思想改造,林彪甚至提出“狠斗私字一閃念”,提倡絕對利他主義。而薩特利用存在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聯姻,則對馬克思主義提出另外一種解釋。“薩特的思想滿足了兩種需求:第一,不能不要馬克思主義;第二,還要講人道主義和個人意識。” 柳鳴九的《薩特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風行一時。“薩特的學說認為,事物的本質就是人自身,對個人的主體性和個人意志給予肯定。這對于此前非常強烈的禁欲主義來說,自然是另外一種學術。”徐友漁說。 人們通過薩特的小說、戲劇甚至他和波伏娃的奇妙關系來接觸這位哲學家,同時把他的思想以格言和語錄的形式傳播開來。“人們從宏大敘事轉向個人敘事”。 “一般來說,建國之后,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進行思想解放。”徐友漁說。無論是徐友漁所稱的思想解放年代,還是許紀霖所說的新啟蒙年代,薩特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年輕人依靠他來尋回失去已久的個體意識。 未完成的啟蒙 此后,再未有人能夠達到薩特和此前的杜威、羅素們所曾經具有的影響力,他們大多停步于學者的書齋和大學的課堂。而薩特們在公眾層面則被迅速遺忘 薩特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可以被視作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試圖依靠引入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來完成對中國的啟蒙,或者說喚醒中國的努力的一部分。 西方哲學思想的進入貫穿著喚醒和啟蒙東方這頭“沉睡的雄獅”的過程。被引入的西方哲學家包括斯賓塞、杜威和羅素。 與之對應,二十世紀最初二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開放、各種學說最盛行的時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哈羅德·拉斯基也通過他在中國的眾多學生和仰慕者,如儲安平、吳恩裕、張君勱等,對中國思想界的自由主義產生重要影響。與此同時,另外一位西方哲學家馬克思的學說最終成為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宰制性思維。此后啟蒙和喚醒的過程進展平緩。 這一過程的再延續即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時期。在這一時期,薩特在中國年輕人中的影響力可以同歷史上斯賓塞、羅素在中國所曾經達到的高度相媲美。 而在五四時代就被中國知識分子借以來喚起個人意識的尼采,此時也被重新提及。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大量引入。然而,他們在大眾中的影響力都未達到薩特所曾經達到的高度。 1980年代突然爆發的活躍期隨即消退。但引介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和思想的工作卻從未停止。進入1990年代之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馬克斯·韋伯、羅爾斯、列維-斯特勞斯、哈貝馬斯包括米歇爾·福柯都曾經在知識界風行一時,但再未有人能夠達到薩特和此前的杜威、羅素們所曾經具有的影響力,他們大多停步于學者的書齋和大學的課堂。 而薩特們在公眾層面則被迅速遺忘。對新一代的中國青年有著多種描述: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互聯網一代、財富下的一代。他們被認為是沒有付出太多努力就享受到長久以來“喚醒”和“啟蒙”所帶來的收益,以及將近30年中國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經濟繁榮。他們是坐享其成的一代,也是天生的個人主義者,無需被喚醒和被啟蒙。而由于翻看了底牌,他們更無需去了解薩特的思想就可以指摘他的種種過失。 功利主義與人文精神的割裂 “我們身處一種‘淺薄的光明’之中” “當啟蒙不再面對傳統的集權體制,而是一個復雜的市場社會時,其內部原來所擁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兩種不同面相,即世俗的功利主義傳統和超越的人文精神傳統就開始分道揚鑣”,許紀霖說。 思想家及其思想在公眾層面的式微,清晰地呈現出這兩個面向的分道揚鑣。問題在于,分道揚鑣之后,誰占了上風? 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立和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使經濟事件客觀上一度成為惟一重大的事件,中國最具知名度的學者和最能贏取人們尊敬的學者開始集中在經濟學領域。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引進,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開始進入加速期。而在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經濟學者開始在公共媒體拋頭露面,經濟理論的傳播為媒體所挾持,離開它所本來最應輝煌的學院之內。 今天,經濟學家和他們的思想理論,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整體開始替代薩特曾經在中國起到的思想啟蒙效應。與此同時,在政治思想上的改革則并不能像經濟思想上的革新那樣容易進行。 而從個體來看,即使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思想和學說能在大眾中盛行,他們卻從未喚起過羅素、薩特等在中國所激發起的熱情。在今天中國和世界的接觸中,很難再有足夠讓中國年輕人和知識群體感到激動人心的思想和思想家。某種程度上,群體性熱情和興奮被群體性冷漠所代替。 也許,這可以視作開放和多元化帶來的必然結果,是價值體系豐富必然呈現的狀態。但是,即便是薩特的思想和學說,也是在一種多元化的環境中產生,從而風行一時。薩特和薩特思想需要行動來作注解,這并非所有時間和所有國家都能提供的。 “我們身處一種‘淺薄的光明’之中”,徐友漁說。淺薄的光明和淺薄的解放讓我們自認為自己不再需要被啟蒙和被喚醒。個人意識在一定程度上的覺醒讓薩特顯得不合時宜,沒有人希望耳邊有一位哲學家訓導似的喋喋不休。過多的選擇涌現在新一代人面前。人們也假定自己在選擇,盡管可供選擇的本就是篩選過的。 現在,走向世界的熱情停留在貿易爭端、知識產權上,停留在ipod、windows和紡織品之上。我們似乎正在喪失那種20多年前中國再次同世界親密接觸時的熱情: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不無困難的開放,幾乎將思想上同世界接觸的熱情連同啟蒙和喚醒的愿望一同淹沒。取而代之的則是對消費的狂熱和對經濟理性思維的奉行。 薩特所帶來的激情離我們遠去。是我們已經成為薩特,還是我們不再需要他?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正文 |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票:今日黑馬 |
| 韓國時尚品牌女裝招商 |
| 海順咨詢 安全獲利 |
| 風情小布藝店生意火爆 |
| 超值名牌時裝折扣店 |
| 蟲蟲新女裝漂亮才被搶 |
| 日本服飾時尚沖擊波 |
| 投資3萬元年利100萬! |
| 美味--抵擋不住的誘惑 |
| 開麥當勞式美式快餐店 |
| 05年開什么店好賺錢? |
| 防治皮膚白斑外陰白斑 |
| 男人,你想更幸福嗎? |
| 中國特色治療精神病! |
| 3個月,重振男性雄風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