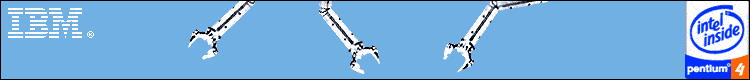|
閔良臣
不怕挨小說作者的罵,我是不大看現在一些人寫的小說的,緣故之一,就是不知從什么時候,我們的小說仿佛只關注“小資”,只關注新生的“中產階級”。就好像我們的社會真的是已經全面實現了小康似的。請原諒,我是個只相信事實、只相信自己眼睛、只相信自己的感受的人。媒體也好,“文件”也罷,說真的,都只能“僅供我參考”。
從媒體最新消息得知,南京有作家以南京的市罵作小說標題發表后引來軒然大波,有人贊同,有人反對;有人說是揭露丑惡,有人說是對城市丑化;有人說南京應該反省,有人說作者是嘩眾取寵。不一而足。
這一切,我都不關心。哪有一篇小小說就能把一個不是丑陋的城市弄成丑陋了的。一個城市真是脆弱到如此地步,我看比描寫的那些丑陋還要更加影響這個城市的發展。再說,總是一個城市有了丑陋人們才去寫,而難以想象因什么人的說和寫會把一個美麗的城市就變得丑陋了。一個城市丑不丑陋,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是完全能感受得到的。至于說到一個城市在某一點上是丑是美,這要看事實。即如11月7日《娛樂信報》的報道中所說,一位“南京人”一家報社派駐以色列的記者,去年回國向記者直言:“去年回來以后自己也覺得南京話確實很難聽。雅蘭(那篇小小說的作者)的小說標題雖然粗俗了一點,但畢竟反映了事實。我發現南京的年輕人尤其喜歡說臟話,幾乎每句話都帶著臟字。我曾經陪著外國朋友去五臺山看球賽,幾萬人一起喊‘南京呆B’,我聽了都臉紅。南京整個城市的文化素養確實不高。”這說明南京城市中至少有不少青年人喜歡“出口成臟”是事實。當然,我們永遠要記住:不能遇見一個壞人,就把所有的人都作壞人看(魯迅語,大意)。更要記住一位偉人所言:除了沙漠地帶,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種人。肆意丑化一個地區,肆意丑化一個城市都是要不得的。
回過頭來說,我更關心的是我們現在的一些作家都在寫什么,因為寫什么也就意味著他們關心什么,他們關心什么,也才會寫什么。前不久,我批評有人認為我們現在因為有了“中產階級”這個階層,因此我們似乎就應該有《英雄》《天地英雄》這類的影視劇供這個階層享受。我們確實有了一個可以稱得上“中產階層”的人群,也確實應該有讓他們去“享受”的文藝作品。但古今中外證明,這種作品不一定就是像《英雄》和《天地英雄》之類的東西。尤其是對一個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度的作家而言,就算你已經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你依然不能只去關注中產階級——即使中產階級在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了——因為全國更多的卻是才剛剛溫飽不久的人群。這里且不去統計現在我國大小城市中的絕對貧困人口數(想來不會是一個小數字),單按2003年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結束后答記者問時說的話,即目前沒有擺脫貧困的人口約3000萬(從后面的文字中可以認定這僅是指農村而言),這僅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標準計算的,如果把標準增加200元至825元,農村貧困人口就是9000萬。一個人一年只有825元呀,恐怕還不及有些人請客時的一頓“便飯”。
對此,《娛樂信報》的報道中一位大學教授有清醒的認識,他說:現在很多作品其實是一種嘩眾取寵,只是寫了城市的影子,像大商場、酒吧之類,對社會底層卻不曾關注。這實際上是在一種想象中寫作,而且還不是一種健康的想象。如果想通過這些作品去了解城市,是誤入歧途。
說至此,不能不令我又想到了魯迅。幾年前有“莊周”在《書屋》上連載《齊人物論》,其中“百年新文學余話”中有一小章,題為《百年“樹人”的魯迅》,對魯迅的“定論”是這樣下的:
魯迅先生世紀中國文學第一人的地位,無人可以撼動。我的理由很簡單,只有魯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筆向國人奉獻出的下層民眾形象,才使得我們可以像俄羅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國人提到亞哈船長、桑地亞哥老頭、法國人提到紐沁根、“局外人”那樣,提到我們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堅信他們的確存在過。這是真正屬于中華大地的民眾形象,他們的屈辱和蒙昧,高貴和卑賤,性格和情感,都具有無可置換的中國特色,這三個在小說里最終都悲慘死去的中國百姓,恰恰具備甫一現身便進入不朽的文學偉力。魯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業余愛好者的產量而能奠定在中國世紀文學的崇高地位,的確只能反襯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2000年第12期,第44頁)
我還想到了學者朱學勤先生在《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中所言:“他那樣肅殺的文風,我一度以為是他個性所然,后來方明白是那樣的現實環境逼出了那樣的文風,甚至可以說,是那樣的時代需要那樣的文風。他正是以那樣的文風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黑暗。反過來,現在讀林語堂,讀梁實秋,你還(能)想像(得出)就在如此雋永輕淡的文字邊上,發生過‘三·一八’血案,有過‘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又說,“我懷念魯迅,有我對自己的厭惡,常有一種茍活幸存的恥辱。日常生活的塵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蓋著恥辱,越積越厚,足以使你們遺忘它們的存在。只有讀到魯迅,才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癥,才迫使自己貼著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均見鄢烈山選編《2003中國雜文年選》第470、471頁,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我不知我們有哪一位作家也會像朱學勤先生這樣,因認為自己的“茍活幸存”而產生對自己的“厭惡”。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