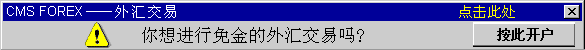蘇浙企業家成長環境比較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28日 20:54 中評網 | |||||||||
|
新 望 1755年,法國經濟學家康替龍首次提出了“企業家”的概念,認為企業家是承擔某種風險活動的人;之后,有些經濟學家用它來泛指建筑業、農業、工業等領域中的冒險家;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將企業家視為能把經濟資源由較低的生產率水平轉變為較高生產率水平的人;劍橋學派創始人馬歇爾認為,企業家是以自己的創新力、洞察力和統率力,發現和消除市
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商界名流”欄目的開場白有一個非常煽情的表述:他們注定為挑戰而生;他們在事情發生之前就作出決定;他們尊重人,發現人的價值,發掘人的無限潛力;他們都有不平凡的經歷。因為他們有不平凡的腦袋。 當我數次坐在電視機前記住上述解說詞的時候,我感到國人對企業家這個中國大陸的新生事物表現出近乎盲目的虔誠和歡呼。他們曾是“奸商”、“末民”、“資產階級”,昔日走馬路只能靠邊,不許走中央。今天他們進人大會堂,上天安門城樓,電視上有圖象,廣播里有聲音,披紅掛彩,揚眉吐氣。企業家們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寵兒。 一如專家們所言,企業家是最稀缺的要素資源,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靈魂。甚至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市場經濟就是企業家經濟。企業家資源的多寡,對一個地區的發展起重要作用,有時或許是決定性作用。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之后,企業家資源不僅對區域經濟競爭有決定性影響,而且更多的經濟社會資源會經過企業家之手得到優化、整合,從而導致區域經濟的協作化和一體化,顯然,這種作用是政府的職能難以企及的。 然而,僅僅認識到企業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還遠遠不夠,企業家的成長及其行為并非只是一個自身素質問題。因為企業家是“高度社會化的經濟動物”。企業家的勞動是一個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交換過程,社會價值的取向、大小直接決定著這個交換過程的成功與否、質量高低。同是華人,海外的華人企業家與大陸的企業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華人在總人口中間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業界70%~80%的人都是華人。這并不單純是因為個人素質。一個可能是“異類”、“邊緣人”的奮斗精神在起作用,而另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則與制度環境有關。 中華民族,一體多元。蘇浙企業家及其成長環境之比較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歷史上吳越兩地曾是兩個互為競爭、互為依存的實體,一部“吳越春秋”從武——文——商演繹了千百年時間。至今,歷史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于區域經濟特征之中。因此比較蘇浙經濟應當具備一種歷史眼光和文化眼光。筆者認為,隨著分權式改革的進程,區域經濟特征及其競爭將繼續存在并有強化之勢。今后蘇浙經濟走向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地企業家資源數量、素質,歸根結底取決于企業家的生成機制和社會環境。 從嚴格意義上講,江蘇企業家和浙江企業家并不是特征十分明顯的兩個群體,整體可比性并不是很強。如江蘇分蘇北、蘇南,二者經濟基礎、人文傳統迥然不同,因此企業家成長環境也就明顯不同。蘇北雖也出了不少企業家,如“維維”之崔桂亮,“森達”之朱相桂,“春蘭”之陶建幸,“綜藝股份”之咎圣達等,但其作為一個企業家群體的共性不明顯,企業家總數也較蘇南少得多。因此我們在這里主要將區域特征相對明顯的蘇南企業家與浙江企業家來比較。 但浙江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浙江的杭嘉湖地區與蘇南并無二致,其經濟地理特征及文化、體制背景與蘇南有很強的同質性,二者沒有比較的必要;在浙江的中東部、中西部,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著名的寧波商幫、龍游商幫,但如今已呈式微之勢,總量不大,而且在今天看來,區域特點不很明顯;而最能代表浙江企業家總體特征的應當說非浙南的溫州、臺州企業家莫屬了。因此我們在這里實際上是運用抽象法,將最能代表蘇浙企業家特征的蘇南企業家與溫臺企業家做比較。這兩個企業家群體都是改革開放之后的新生代,成就突出,區域特征比較明顯,備受人們注目。尤其誕生于兩種不同的農村工業化模式——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之中,其成長環境的比較或許能夠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也能夠對企業家隊伍建設諸如企業家生成、發育、成熟乃至新陳代謝等問題有現實的啟發意義。 蘇浙企業家成長環境的相同之處甚多。 ——同處于歷史上的經濟發達地區,物產豐富,非農產業發展起步較早,是歷史悠久的“副業大省”,有深厚的手工業及近代工商業傳統,草根工業都有一定基礎; ——民眾的商品意識普遍濃厚,吃苦耐勞,有強烈的追求剩余的沖動,且能工巧匠多,勞動力素質相對較高; ——有深厚的人文傳統。科舉考試中屢屢金榜提名,文人墨客,代不乏人。尤其受功利主義、合理主義思想影響深,人們為追求功利目標,不惜作出犧牲; ——由于區域地理位置上的相對優越,人口稠密,市鎮、集市、碼頭珠連網接,交換市場化,市場網絡化。近現代在“外來挑戰——內部回應”的現代化進程中占近水樓臺之利,得風氣之先,如近代江浙財團,算是中國商幫史上的新式商人,較早進入面粉、紡織、買辦、娛樂、航運、成衣等現代產業或高等級產業; ——同為東南經濟發達省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速度一致居于全國前列; ——蘇南、溫臺兩地的國有工業基礎都不是十分雄厚,其經濟起飛肇始于農村工業,且以農村工業為主,因此兩地企業家大多為農民出身; ——在經過鄉鎮企業改制之后,兩省都已是非公有經濟大省,工業產值當中,非國有經濟比重均超過80%; ——正是上述特點決定了兩地企業家總量大,貢獻突出,覆蓋面廣,成為兩處引人注目的企業家叢林。環境上的相通之處,也決定了兩地企業家有著許多共性:他們在市場中長大,是天生的“市場派”;他們善于運用非正式制度資源,也善于創造和運用非正式游戲規則;他們來自社會底層,土生土長,曾經長時間游離于計劃體制之外,較少受到舊體制、舊觀念的束縛,這也造就了他們的優勢和自信。 然而,畢竟蘇南、溫臺兩地企業家成長環境在許多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秘密往往隱藏在差異性當中,找到了差異也就發現了規律。環境的差異又導致了他們在行為方式等方面明顯之不同。 第一,就自然地理環境而言蘇南要比溫州優越得多。一個是平原水鄉,歷代糧倉,水陸交通十分發達;一個是臨海山區,農業基礎十分薄弱,人地比例高,糧食缺口大,交通不便。溫臺企業家的企業家精神是被逼出來的,多數人出身很苦,歷盡坎坷,甚至經受過極限狀態下的生存鍛煉,如正泰集團的老總南存輝就曾是溫州幾十萬修鞋大軍中的一員。這一點頗似歷史上的徽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溫臺地區農民(農村剩余勞動力)為尋求生路,他們寧愿背井離鄉,在外面開闊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積累之后,他們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識、經驗及外界人緣等資源向親朋好友擴散。溫臺經濟發展最初的沖動來自于民間,由卑微又見多視廣的民間能人推動、發動。 蘇南物產豐富,但長期以來賦稅苛重,民眾便在富庶而高壓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隱忍的性格。這一地區農本思想、農戰觀念源遠流長,人們普遍有較強的本土意識,視出門在外為畏途。溫臺人幾乎沒有什么本業(即農業)觀念,相反,視做生意為正途。他們愿意長期出門在外,也從而普遍善于捕捉機會,察言觀色。蘇南企業家擅長的是“軟功”、“內功”,而溫臺企業家擅長“硬功”、“外功”。 蘇南還由于靠近市場和中心城市,其農村工業型式多屬城市輻射帶動和外資外貿拉動;溫臺則是典型的市場加工循環型,前店后廠,重視專業化市場建設,有相當一部分人純粹靠經商起家;蘇南有加工制造優勢,但中間產品多,利潤薄;溫臺地區雖是起點很低的百姓經濟,家庭經濟,但卻大多生產最終產品,直接面向消費者,因此他們的市場直覺更好。 第二,文化傳統、輿論氛圍,價值觀念上有許多微妙的差異。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東文化),蘇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吳文化。吳文化有利于工廠制度的產生,因為工廠內部管理離不開合作與秩序。在蘇南,“鄉鎮企業”也是“鄉鎮集體企業”的同義語,這是思維定勢;永嘉文化則更利于企業家精神的成長,因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說到底是一種個人主義精神。所以,溫臺地區鄉鎮企業一詞實指各類戴紅帽的私營企業。自轉制以來,蘇南經營較好的鄉鎮企業普遍存在集體股太大,經營者買不起,企業改不動的問題,而浙江人卻果斷地以“創業股”的設立解決了轉制中存在的“馮根生難題”(經營者買不起大股),從而使企業家地位迅速合法化;蘇南農村企業產權模糊,企業家收入不明確。平均主義盛行,個人的創造價值難以確認,且迫于輿論也不敢露富。美國《福布斯》雜志上一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中國大陸最富有的50人中,作為大陸經濟最發達最富有地區之一的江蘇,竟無一人入選(見《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6日)。 蘇南多管理型的企業家、政治型的企業家,而溫州多戰略型的企業家和技術型的企業家。這就如同民間所謂“吳中多管家”、“紹興出師爺”。蘇南地區過分注重等級制度和現有秩序,以制度為本,較容易形成企業傳統,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漸漸顯示出制度之美,但卻缺乏管理創新;而溫州人較少受到傳統制度的約束,善于不斷超越自我,進行管理創新、思維創新,直接與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接軌。如最早出現的民間自治的小商品市場,民辦金融機構,個人承包飛機航線,集資入股修建鐵路,城市建設市場化等等。這就是周其仁所謂“制度企業家”;而蘇南更多的是“管理企業家”,或者說“職業經理人”,顯然前者更接近企業家的本質。 第三,蘇南與浙溫有不同的工商業歷史傳統。在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商幫中,蘇商是實力強大的近代新式商幫。以張騫、榮德生等為代表,蘇商是清末以來實業救國的一支勁旅。《馬關條約》(1895年)允許外國人在上海設廠之后,臨近上海的蘇南士紳見識到了大機器和現代工廠,便紛紛回蘇、錫、常、通興辦紡織、冶金等加工制造業。蘇商主張“貨殖為急”、“時任知物”,實業為主,商貿為副。強調信譽為本,精細作業。由于文人紳士加入其中,蘇商整體素質較高。可以說,蘇南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源地,也是中國近代企業家和產業工人的誕生地。這個基礎是國內任何其它地區所不可比擬的;溫臺地區沒有什么近代意義的實業基礎,甚至新中國之后也沒有什么象樣的國有企業和大項目。其商業傳統僅限于走街串巷雞毛換糖的貨郎、跑江湖剃頭修鞋的手藝人,其工業產品起點大多是一些塑料時代的跳蚤產品。甚至溫臺地區在1980年代一段時間里,從事制假售假的人和從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蘇南近代民族資本家既受外國資本傾軋,又受官僚資本欺壓。歷史上的蘇商基本都有一種自知之明,他們埋頭做事,低調做人,“遠官僚,親商人”,也因此才避免了因政治風云變幻而大起大落。但是,這一情況在蘇南鄉鎮企業出現之后又有了微妙的變化。在蘇南,由于文革和公社時代單一的政府強勢整合,社會結構大大簡單化,人們的經濟行為意識形態化,鄉鎮企業內部干群之間二元分化。蘇南鄉鎮企業家(干部、準官員)曾十分善于樹典型,跟形勢,喊口號,好大喜功。這甚至已經成了蘇南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不過,在經過改制之后,政企關系有了新的調整和定位,此一情況或許將會有所扭轉。 溫臺人的經商意識是滲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場上賣菜的年輕人,他們也從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謀生活費的小販,他認為他是在經商,是在做經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機。他們永遠是自己的主人;而蘇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柔順到近乎奴性的意識。許多人認為,“工作”是領導施舍的“飯碗”,自己能當企業家是由于某官員的青睞和提拔。不論機關還是企業,“領工資”(法定勞動收入)從來只叫“發工資”(可隨意賞罰的賜予),而事實也正是這樣。一些人走上企業領導崗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不再是“群眾”,而成了“干部”、“公家人”。 第四,農村工業化的歷史起點不一樣。蘇南農村工業比溫臺早出現近10年,產生于計劃經濟年代,帶有那個時期的特征,與舊體制有緊密的關聯度。蘇南企業家們在費勁把就舊體制撕開一個大口子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已不適應新的市場規則;溫臺企業產生于改革開放之后的1980年代,多數游離在舊體制之外,“民營性”強,舊體制的包袱輕,也更符合古典市場經濟發育的內在規律。溫臺企業家們越是市場化程度高,越是如魚得水。 蘇南企業家與溫臺企業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懸殊。樂清柳市鎮電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氣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經歷;蘇南企業家基本都能得到體制內的保護,而且只要產值達到幾千萬或上億元,就可農轉非,可到不同級別的黨政部門兼職、掛名。蘇南企業家政治資源多,風險小。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的將小車開到北京部長們的家里,“跑部錢進”,駕輕就熟。在整個1980年代里,蘇南各縣的領導反復號召農村基層干部“備些好煙好酒,親自上門,把重要關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縣官們此計一出,指令、指標、“三材”調撥單等市場禁錮和計劃配額紛紛被拿下。“賄金”、“關系”在蘇南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功莫大焉。但也因為找慣了“市長”,找“市場”的本領和意識就比溫臺企業家要弱一點;溫臺企業家有著極強的配置和組合資源的本領,幾乎帶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瑤膽大包“天”,成立包機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行業;1992年陳金義一口氣在上海收購六家國營商店,之后又進軍三峽,盤活幾家涪陵的國有企業;徐文榮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視城,建大學,硬是闖出了“橫店”的金字招牌。這些人找沒找過政府官員?肯定也找過,也不排除“賄金”和“關系”,但他們主要靠自身的企業家才能來實現上述業績的。 在融資方式上,溫臺企業家善用民間資金市場,也產生了一批民間金融家;蘇南則由社區政府出面搞貸款或搞拆借、集資。另外,由于產生時間上的先后,蘇南企業規模較大,基礎好,相應的其企業家年紀目前也普遍偏大,改制,尤其經營者持大股,是第一代與第二代大換班的契機。順便指出,有人認為蘇南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的家族化現象要比溫臺弱,其實這是一個錯覺,蘇南搞得好的農村企業都是帶有家族式、合伙式的企業。 溫臺企業內部對人才的待遇、激勵早已超出國家有關政策規定,他們對人才價值的認識要深刻的多,更加重視人力資本,有明顯的以人為本的取向。溫臺的飛躍、星星、天正、康奈、正泰、德力西等大公司開始借鑒西方所謂“工人資本主義”的一些經驗,重視員工勞動價值,尊重職工發展權,實行“四高一優”,即高工資福利,高員工素質,高工作質量,高企業效益,優秀職工優先入股;在蘇南,由于滲透至深的城鄉分野和干群鴻溝,企業轉制后又突然出現了勞資矛盾,普通職工對自己在企業位置沒有信心、對企業走向漠不關心。蘇南企業家慣于使用強大的行政背景來支配職工,因此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過程中,蘇南企業家們的企業文化、人才觀念等意識要比溫臺滯后一些。 第五,兩地在企業家生成的體制環境和體制傳統上也存在許多差異。曾經顯赫一時的蘇南模式其內核其實是已被現代市場經濟所拋棄了的“社區政府公司主義”。蘇南模式的本質特征正如萬解秋所概括的四個字:政府推動。社區政府是企業最初的發動者,資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護者,還是企業內部分配的主宰者。 在蘇南,1980年代承包制的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短暫分離,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準企業家”(因帶有指定性質,承包人產生過程不明確,所以只能稱作準企業家)。但當地規定企業領導人公開收入最多是普通職工的三倍等政策,企業家行為大受摯肘。集體產權和平均分配分散了企業家的風險,但卻削弱了企業家的創新沖動。在蘇南,企業家干部化,他們得到了體制內的保護,真正到了基層黨政領導崗位之后,也因為懂經濟工作,能牢牢抓住經濟工作中心。但問題卻在于,他們漸漸變成了政府(任命)的企業家,而不是企業的企業家,慣于依賴行政力量。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一旦“上調”后,領導就變成了代替,不是找貓去抓老鼠,而是“領導”親自抓老鼠。政府公司化,鄉村干部農場主化,與民爭利,其結果導致官富民窮。有些人即使到了純粹黨政工作崗位上也不愿意放棄企業剩余索取權,從而使企業內部管理的自主權受到侵害,也給公務員隊伍建設帶來極大難度。一個最通常的說辭是“我所管的鎮里,私營企業和轉制企業領導都發財了,我作為鎮領導總不能連他們也不如吧?”這種邏輯固然與吳文化中“當官就是發財”的民間意識形態有關,更主要的是與上述政企之間打通式的級別結構有關。蘇南至今仍然存在著一種十分危險的“官商一體”現象。在蘇南,即使一些較純粹的企業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分裂癥”,一方面要盡力去應付頻繁而隨意的政府行為,一方面又對那些與企業效益最大化無關的形式主義恨得牙癢癢。蘇南一些企業家深受“政績經濟”和“政府行為”之害。有些企業家則干脆進行“適應性體制復制”,變成了毫無想象力的平庸政客,斤斤計較于攀比待遇、撈取好處,對企業吃拿卡要。 在溫臺,大多數資產所有者也是經營者,這種企業制度之下,企業家風險過大,抑制了企業家的快速長大,但企業家生成的門檻低,后備人才多,且由于擁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權,風險與激勵緊密相連,經營中的靈活度更高。 溫臺企業社區性沒有蘇南強,許多企業長大后搬遷異地,生產廠遍布全國,導致本地經濟空心化、食利化;而這一情況在蘇南是不存在的。蘇南的情況恰是本土情結太重,懼外,排外,企業利益服從社區利益。企業家們普遍都有社區建設的任務和壓力。 秦暉先生曾對中國農村工業的發源地概括出兩個特征:“市場半徑所及,政府控制弱區”,這一概括也適應于農村企業家的產生條件。顯然蘇南的優勢在前一句話,而后一句話正是溫臺優勢所在。據說,19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領導很少到溫臺去,其中一位省長在位五年,一次也沒去過溫州。1980年代浙江鄉村工業開始引起人們注目,務實變通的溫臺人發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瞞天過海也罷,偷天換日也罷,反正“制度租”已使他們擺脫了意識形態之爭。溫臺企業家曾經害怕政治,反感政治。這種情況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顯改變,一些溫臺企業家表現出高漲的政治熱情。這種熱情有的出于經濟利益考慮,為爭奪更多資源,有的則是因為民間經濟發展之后導致了新的基層民主政治模式。企業家們不僅有行業自律之要求,亦有較強的民主自治能力和需求,他們不僅有較強的納稅意識,也有強烈的行使納稅人權力的需求。他們渴求公正的權力,渴求透明的政治運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蘊和體制環境,蘇南企業家與溫臺企業家有坐商與行商之別。溫州模式在溫州之外。300多萬溫臺人遍布海內外的角角落落,歐陸各國城市幾乎都能見到從事皮具、時裝、百貨、土產、托運、餐飲的溫臺人。在溫臺人看來,從來就不存在什么“買方市場”的說辭,那只是經濟學家們在給官方企業家上小兒科式的市場啟蒙課。本地沒有市場他們會找到外地去,國內沒有市場他們會找到外國去。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十分龐雜,可以說“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沒有固定行業,沒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間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國猶太人”的說法。 溫臺人靠原始的“差序格局”建起了一個龐大的現代營銷網絡。早期是供銷員,如今是大老板。“跑供銷”是溫臺企業家們的第一堂課。蒼南縣的曙光印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朱詩力,1982開始為家鄉的眾多家庭工廠跑業務。19歲第一次出門時實在是迫于無奈,父親重病臥床,而他28天跑遍廣東省花去263元還沒有拿到定單。最后他費盡心機闖進一家大企業的總經理辦公室,老總答應他以低于原供方20%的價格、13天拿出樣品的條件“試試看”。之后10天時間里,朱詩力一眼未眨,找人刻模子、制版、出樣,提前三天把樣品送到對方的辦公室。目瞪口呆的廣東老總馬上簽定50萬元供貨合同,并預付10萬元定金。這一次朱詩力就賺了25萬。實際上這種發財模式是溫臺地區最常見的版本,也是溫臺企業家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經歷。在溫臺,這類以市場營銷為紐帶而組合起的虛擬企業至今還大量存在。 溫臺企業家組合生產力要素的本領簡直達到了企業與市場沒有邊界的程度。溫臺人尤其樂清人他們最早在國內實行營銷代理制,其代理制的運用出神入化。溫臺地產品就是靠早年出門在外的一些手藝人來代理推向海內外市場。也因為溫臺企業多屬“市場導入型”,企業內部多數是老總主外,副總主內。而蘇南企業“產品導入型”居多,一般是老總主內,副總主外。 第七,在治安狀況等社會環境上,蘇南明顯好于溫臺。這對企業和企業家的成長而言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社會條件。在東北、西北、華南、華中地區,敲詐劫掠民營企業及企業家個人財產的事時有所聞,給投資環境帶來災害性影響,而在財富、人口均相對集中的蘇南則比較少見,黑社會等非法組織很難露頭,更難成氣候。我住在蘇南農村已近五年,對此有切身感受。在北方的大鋼廠、油田經常有成群結伙的盜竊活動,反盜竊成為一個大問題,收購贓物的原油收購站、廢鋼回收站生意興隆,有些油田、鋼廠甚至要養一個公安分局或派出所,但我在江蘇永鋼集團(位于張家港市南豐鎮)的兩年時間里從未聽說過鋼材被盜的事情,甚至在方圓幾里地之內除與永鋼聯營的永南金屬回收公司之外,居然沒有一家零星收購廢舊金屬的公司。在永鋼時我曾聽到某送變電公司一施工隊負責人對此地治安環境和效果的贊嘆。他說在其它地方施工時用來架高層高壓線用的竹竿腳手架,在施工結束后一般都要“丟失”1/3或2/3,但為永鋼架了七、八公里的高壓線,竹竿未丟一根。 從另一方面看,民風民俗也會影響到企業家行為方式選擇。很多人在發了財后,確實暴露出很多惡劣的個人品行,如吃喝嫖賭。在這一點上蘇浙二地也各有其特點,而且也是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蘇南企業家往往都是社區領袖,不僅受體制內的約束,也比較注意公眾的道德認同及自身形象;但在溫臺不會因為企業家A方面犯了錯誤,用B或C的方面就把他一鍋端了。 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社會風氣是企業家尤其是那些新生的民營企業家和農民企業家們給搞壞了。是不是這樣?我不這么看。人們對有成就的企業家只是尊重乃至崇拜,只看到了他們風光和輝煌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他們幾乎都是在一種人為的制度“逆境”中摸爬滾打出來,很多民營企業家是在付出高昂的權力租后才完成原始積累,他們洞悉體制內的弊端所在,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不透明的市場環境下,他們的心態肯定不平衡。即使那些被樹為“典型”的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其自我成就感也是十分有限的。這一點,多數人并不理解。依我看,周冠五、于志安、褚時健他們既不算什么“先進典型”,也并不是什么“壞人”。他們所處的制度環境注定他們成不了圓滿的企業家,他們之所以身敗名裂,是制度害了他們。體制內傳統的制度安排產生不了企業家。中國的體制轉軌是一個新舊體制反復博弈的過程,企業家們處在博弈的最前沿,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成為體制博弈的犧牲品。當今中國的企業家是特殊時期負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企業家。套用馬克思形容十九世紀德國產業工人的一句話:他們既為舊體制的殘存所累,也為新體制的發育不足所苦。 好了,讓我們索性走出蘇浙兩地企業家叢林(人工林和原始叢林?),從更廣闊的視野上來回答如下問題:為什么中國民營企業“長不大”?為什么中國企業家“不長壽”?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大企業家?除了上述區域性的社會環境、體制環境、人文環境之外,我想還有一個整個國家的法律環境乃至憲政秩序問題。通常人們講“改善投資環境”的時候,只注重引進外商的投資環境,但卻忽視了我們身邊企業家的投資環境和成長環境。 而對投資環境,今日改之,明日善之,也不是個辦法。能為企業家的成長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可以預測的社會環境才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社會,如果對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調節越是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里進行,那么企業家成長的社會環境就越趨向透明、穩定和可預測。現在有一類所謂“國有民營企業”(如海爾等),都是因為一個企業家強人出現(當然這種企業家所在企業原先肯定很差)之后跟隨而來的現象。他們只能謹慎地走在體制的邊緣地帶進行一些有限的創新,其創新環境都有一些企業家個人的鐵碗、威信及當地政府的寬容、大度、支持等因素在起作用。并且,這類企業家一旦由“異類”變為“正宗”之后,其企業家精神也就要大打折扣了。在中國現實社會里,對經濟社會生活的管理、調整通常有這樣幾種方式,中共黨章——憲法——法律——行政命令——政策——領導指示——領導意見。從左向右,越往右的管理方式越多變,越往左的管理方式越穩定。在中國,最常見的管理方式是政府的政策,比政策更多變的是領導指示,比領導指示更多變的是領導意見。領導指示大多數時候還有個書面文字。而領導意見,常常是打個電話或和領導喝個酒,就能得到。對中國的企業家而言,現實當中的情況卻往往是:口頭(意見)>白頭(批條)>紅頭(文件)>黑頭(法律)。對個人創新精神的保護和激勵也是這樣,越是在法律框架內的越穩定,越是靠領導意志越靠不住。優秀企業家總是流向最適合創新地方,也即對創新精神的保護和激勵最穩定、最有效的地方。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新望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