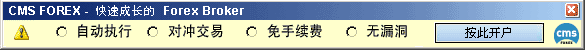埃爾切縱火事件與中國的全球化(之一)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0月14日 14:10 21世紀經濟報道 | ||||||||
|
9月17日,西班牙東南部小城埃爾切發生了西班牙人攻擊并焚燒中國僑民鞋店的事件。這似乎也是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事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件。但是,這個時代的這類矛盾與沖突是否有它特別的地方?它們是如何出現和發展的?我們如何通過這類事件來重新思考全球化以及中國參與全球化的路徑? 本報記者 張 翔
9月17日西班牙東南部小城埃爾切攻擊并焚燒中國僑民鞋店的事件已過旬余。據《國際先驅導報》報道,目前,西班牙埃爾切中國鞋商的生意雖然有一些小的下滑,但生意仍然正常進行,每天到那里買中國鞋的人還是熙熙攘攘。其實,對中國鞋商抱有敵意的只是極少數,多數西班牙人對中國人還是友好的。 盡管隨著事態漸趨平靜,中國內地的關注亦趨淡然,但當地中國僑民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困局并未有根本改變;其故土如何理解這些新移民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境況,仍然有待繼續追問。 事件當天,在埃爾切的中國鞋城,約400名西班牙人聚集街頭,燒毀了一輛載有溫州鞋集裝箱的卡車和一個溫州鞋商的倉庫。當游行人群到埃爾切市政府示威之時,當地警察隨隊伍而行。六天后的9月23日,當地又爆發了一輪針對中國商人主要是溫州商人的示威游行。示威者揚言以后將每周舉行一次抗議示威,以抵抗中國商人的廉價產品給西班牙本地商人帶來的不公平競爭。 在此之前,來自溫州等地的鞋商在其他國家(如俄羅斯、意大利、尼日利亞等)已經遭遇過類似事件,只是程度有所差別而已。這類暴力沖突以后看起來也會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常見。它們似乎也是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事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件。但是,這個時代的這類矛盾與沖突是否有它特別的地方?它們是如何出現和發展的?我們如何通過這類事件來重新思考全球化以及中國參與全球化的路徑? 香港《信報》9月27日的評論認為,這起事件并不是過去發生在東南亞的排華運動,而是當前全球化引起的“后遺癥”中的一種,不必為事件加上種族沖突色彩。這一很有代表性的評論點出了人們關心的兩個問題,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國的海外移民。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是什么樣的全球化使埃爾切事件發生,它與美國企業或者日本企業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的遭遇是否一樣?盡管這起事件不是東南亞的排華運動,但是這起事件中的中國海外移民與東南亞海外移民的遭遇區別何在? “中國制造”的全球境遇 那些埃爾切人對中國鞋商的憤怒和怨恨,最重要的火力點就是中國商品價格太低,以及在銷售網絡方面的擴張,導致“不公平競爭”。其他如中國鞋商在經營上不合規矩(例如變相逃稅、假冒偽劣)以及華人區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責只是陪襯。以西班牙相對較高的勞動力成本和其他成本,埃爾切的鞋商的確很難打贏與中國鞋商的價格戰。 埃爾切是歐洲制鞋業的重鎮,素有“歐洲第一鞋城”的雅稱;由于溫州鞋近年來在西班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占有市場份額節節攀升,埃爾切市制鞋業自然受到強烈影響,該市制鞋工人的失業率也隨之上升。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在全球一體化的貿易中同樣如此。因此容易理解一些埃爾切商人會對政府施加進行貿易保護的壓力,但在多次以各種方式向當局投訴中國鞋商的經營問題之后,以這種激烈的暴力方式呈現出來,多少折射了他們在價格戰中嚴重的挫折感。 可以預料的是,在這類貿易戰中,埃爾切鞋商通過游行等方式表達的訴求可以對西班牙當局產生相當有效的壓力,他們的挫折感在此后很可能出臺的合理保護措施之下將有所慰藉。此前俄羅斯和意大利羅馬的案例中,當地權力部門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這類貿易競爭。 本來,能夠做到價廉物美,成功地以低價策略介入國際市場競爭,是闖蕩海外的各種中國企業的一大能力,也是其競爭力的一大王牌。溫州商人在海外開拓市場屢有建樹,憑借的就是發現市場空間的敏銳和低價競爭的能力。價廉物美對當地消費者而言也應該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現在這是溫州鞋商遭遇抗議的主要罪狀。這其實也是相當部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制造的本土產品走向全球時遇到的難題,近年來針對彩電、紡織品等等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可謂“全球烽火”,真算得上中國加入WTO之后在境外遭遇的“第一波”挑戰。 在反傾銷的國際貿易規則之下,中國企業的低價營銷的能力面對所在國的貿易保護行動,根本不能像知識產權保護的權利伸張那樣,構成在貿易紛爭中的強勢訴求地位。低價戰略在貿易競爭的攻堅戰中的作用要遠遠大于保衛戰中的作用;當中國的低價產品占據了當地的一定份額之后,問題便變得嚴峻起來。只要以主權國家體制仍然是全球貿易的基礎,這個困境就無法消解。 難道中國企業擁有低價銷售的能力竟然是一種錯誤?如林毅夫所言,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利用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難道不是一種可以采取的發展戰略? 問題并不在這里,擁有低價的能力就沒有理由不運用。問題在于中國企業何以具有低價銷售的能力?這種能力在目前面臨什么樣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平對西班牙研究有年,對埃爾切縱火事件亦一直關注。他認為我們應該從這一事件反思目前一些國內企業勞工工資過低、損害環境不計成本的發展模式,而不是將責任推就于西班牙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者貿易保護主義。他的看法提示出很有意義的問題,即如果說中國商品價格低廉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勞動力價格低廉、環境保護費用低,那么目前東南沿海已經出現的“民工荒”等現象是否意味著這個基礎條件已經在開始改變? 這種改變其實已經是無法扭轉的現實趨勢了。盡管目前國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中的工會組織還未有很好的發展,工人在勞資雙方的薪酬談判中的議價能力還比較低,但是工人在勞資結構中的聲音已經越來越有分量。例如,民工在就業過程中“用腳投票”帶來的“民工荒”現象是一種企業體制外的表達,中央政府對民工欠薪問題的關注和相關決定則可以看作化解企業內部失衡問題、“執政為民”的前奏。這些變化無疑將提升企業的工資成本。同時,在人們的經濟水平提升之后,對環境保護的訴求迅速升高,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也隨之上漲。 此時再要求一種合意的低工資、輕環保的發展模式,就需要消解民眾和政府已經興起的勞工保護和環境保護的自覺意識。這種消解顯然難度極大,“支持民企發展”之類的訴求顯然也不能勝任,因為這兩者在根本上并不沖突。因此,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成本必然將受此影響而有所提高。 這樣看來,對于海外拓展的企業家來說,國內勞動力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成本提高的挑戰比國際挑戰更具推動性。在國際貿易中,自己的成本優勢沒有不用的道理;而在國內,自己的成本優勢卻在逐漸減弱。這種變化,無疑將促使中國企業進行企業戰略的轉型,相對而言更注意企業品牌塑造以及技術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發展。一位溫州鞋商在埃爾切事件之后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說,“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那把火,把溫州鞋燒到了國際市場;現在西班牙又燒了,處理好了就會燒出世界品牌。”應該說,如果沒有國內市場的變化,西班牙的一把火更可能把溫州鞋燒到另一個有待開拓的市場;有了國內市場的變化,溫州鞋的轉型和品牌提升才能具備內在的動力。全球市場的處女地畢竟有限,要想不說“別了,埃爾切”,溫州鞋商就得拿出自己的辦法來。 新移民的雙重背景與認同困境 對于那些已經移民西班牙的鞋商來說,埃爾切這把火燒出的不僅是商品的競爭問題,更是他們如何生活于當地社會的問題。移民“扎根”比一本生意經更難盤算。而如何對待這批與國內經濟政治生活有著密切聯系的海外新移民,也是中國政府需要面對的新課題。 縱火事件中部分埃爾切人與當地中國移民之間的沖突,多少反映了不同族群之間的隔膜和華人新移民在當地的認同困境。這部分改革開放之后闖蕩世界然后在歐洲“扎根”的移民,究竟處于何種狀態? 《讀書》雜志今年第五期與第十期刊發項飆、王蒼柏等學者的多篇文章,討論了海外華人問題。通過埃爾切事件以及相關部分移民的了解,可以對他們的討論有所推進,同時也可以進而理解中國參與全球化過程中呈現出的一些重要問題。 改革開放后溫州等東南沿海地區向西班牙的移民主要有兩類,一是企業家、專業技術人員、家庭團聚移民等,其中相當部分與跨國商業活動相諧,此次事件中已移民的跨國鞋商就是例子;二是為數眾多的草根階層,包括那些非法移民。這里主要分析前一類移民。 這些新移民不同于從傳統移居地東南亞遷至發達國家的“再次移民者”,也不同于早期移居海外、開放后重建與大陸聯系的華僑華人。他們隨著頻繁的跨國生意往來,強調合同關系,間歇性地穿梭往來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及短時間的逗留。而老一輩移民基本上是從移出國向移入國單向遷徙,最后或者逐漸融入乃至同化于當地社會,或者拒絕同化而返回移出國。新移民的這種移民方式因此大不同于那種永久定居和排他性地獲得居住國公民權的舊做法。 這些新移民擁有雙重身份,他們既屬于故土,又屬于移入國。他們總是與中國公民身份的同鄉和親戚保持密切聯系,在埃爾切事件受攻擊的就不僅有移民,也有中國公民。他們的移民旅程由全球化所推動,但最強勁的紐帶卻不是全球化,而是以往熟人社會中建立的關系。項飆在北京的浙江村調查中(《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發現的那種在同鄉和宗親的熟人社會中形成的信用關系,在溫州人的全球性流動中同樣存在,并且以此為基礎營造了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網絡。 也就是說,在溫州商人的全球性流動過程中,并沒有全球性的想象體可以認同,他們只是在具體的跨國關系中建立自己與故土、移入國等地域的聯系,這種聯系甚至更像一種“反全球化的全球運動”,他們來自熟人社會的跨國流動的動力和靈感,更像對那些同一的、標準化的全球化因素的不自覺的抵抗。 這種雙重身份和特別的日常跨國旅程,使得這部分新移民的認同方式別具特色。他們同時與不同的國家實體和文化歸屬相聯系,但是他們又不依賴于其中任何一種。這樣,他們就在移入國建構了一種王蒼柏所說的“外地域認同”,他們將認同根植于熟人群體內部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想象之中,而不是僵化的地理疆域,這種外于地域的認同才可以“既處處為家,又無處為家”;“既在此,又不在此”。這種“外地域認同”其實也是多地域認同,他們改造和利用了故土的地域和血緣關系,也利用和改造了歐洲華人圈子和移入國的社會政治資源,這樣才編制出跨越國界的全球網絡。 但是,這種便利同時也是他們的局限。他們在跨國生意和生活往來中建立的共同體,就像一塊跨國“飛地”,與故土和移入國兩方面的聯系都顯得有些脆弱。埃爾切事件正暴露了“外地域認同”的基本困難,那就是,他們必須同時處理國際貿易沖突和故土的階層矛盾,而以低價策略為核心的跨國經營戰略在故土與移入國同時遭遇了挑戰。 也正是在這種矛盾中,可以發現這種“外地域認同”的轉化可能。不過,這種轉化并不是放棄他們的雙重背景,簡單地融入當地社區,而更可能是繼續依托和發掘原有跨國網絡的潛力(比如溫州鞋商在銷售網絡的營建上加大力度),更新經營戰略,提升產品層次,切合當地法治要求,在與當地人的競爭中爭取更多的利潤、權利與自由。在眾多報道中不難看到,不論是否已經移民,那些在西班牙奮斗的溫州鞋商都有一個共同關注的最大問題,那就是“我們溫州鞋將有什么樣的前途”。在經歷了埃爾切事件之后,原來的“我們溫州人”的共同體認同并未改變,“外地域認同”面臨著提升的挑戰和機遇。 這種本國公民與跨國移民復雜糾纏的情況也給中國政府提出了新的課題。這些新移民都是美國學者Aihwa Ong所說的“彈性公民”,他們追隨的是國際資本的運行規律,不再是某一國家傳統意義上的公民,他們要積累的是屬于他們卻不受某個國家控制的資產。但是他們又通過資本紐帶深刻切入了本土社會的階層分化格局。那么國家應該在他們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后他們的實力會越來越強,游說能力也會越來越強(就像印度隨IT業跨國發展興起的移民群體一樣),政府如何處理他們依憑投資實力提出的降低勞資成本和環境治理成本的訴求? 而且,這類新移民的出現是否會推動我國的僑務政策發生變化?1955年的萬隆會議兩個重要與會國中國和印度都以憲法和條約的形式明確表示,不承認雙重國籍,僑民必須在居住國和母國之間二者擇一。這表明了當時兩國反殖民反霸權、發展民族國家本土社會的信仰。直到1986年和2000年斐濟的兩度排印(印度僑民)政變和1998年印尼的排華暴亂,中國和印度政府都采取了謹慎關注但不干預的姿態。其后,印度政府從1990年代開始重視印僑、印人問題,到2003年和2003年兩度召開最高規格的“海外印度人”大會,并正式修憲,承認雙重國籍,僑務政策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在埃爾切事件中,由于同時波及新移民和中國公民,中國駐西班牙使館在第一時間對事件表示關注,并一定程度介入了事件的處理。目前新移民所呈現的新特點,以及此后類似事件的頻發,估計將不斷刺激中國僑務政策的變化和調整。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