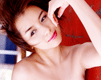揭黑醫生陳曉蘭的八年抗爭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6月15日 13:47 南京周末 | ||||||||
|
她叫陳曉蘭,今年53歲,曾經是上海市一家地段醫院的一名普通醫生。 1997年至今,八年間她孑然一身,獨自調查搜集證據,舉報醫療問題。 2003年6月起,她用“一個有良心的醫生”的網名,在網絡上發表了一系列揭露醫療黑幕的文章。
為了揭黑打假,她甚至親自使用這種她認為有害的醫療儀器,使自己成為一名受害者。 她的行為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同行的反感。 本報記者 張 辰 記者撥通陳曉蘭電話的時候,她正在上海閘北某小區的家中忙著準備材料。由于晚上經常只能睡三四個小時,陳曉蘭的聲音中透著掩飾不住的疲憊。陳曉蘭說,4年前她一個人搬到現在住的地方。自從女兒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已漸漸習慣這樣一個人的簡單生活。“現在我家里書房、客廳的地上,全是各種與醫藥有關的材料,還有不少我自己購買的藥,這些都是‘證據’。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基本上就是在電腦前整理準備材料,聯系知情人了解情況。” 記者擔憂以她多年的舉動,還有什么醫院能夠接納她。陳曉蘭苦笑了一聲:“我已經退休了!”記者從她口中得知,2002年,50歲的陳曉蘭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編制”退休,但因為其身份特殊,醫院沒給她辦理正式的退休手續。陳曉蘭說,她去醫保局咨詢,赫然發現自己的“四金”賬戶分別于1999年7月和2001年4月被“強制封存”,但是她既未收到任何通知,也沒得到任何解釋。 “雖然沒有什么經濟來源,好在我還可以靠以前的積蓄和父母留下的遺產支撐著。家里的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掃描儀、傳真機,有些也是朋友支援的。”陳曉蘭輕描淡寫的話語背后隱藏了耐人尋味的艱辛。 準備拿輸液問題開刀 談到目前手頭的工作,陳曉蘭憂心忡忡地說:“一直以來,我關注的重點都在醫療器械。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一些藥品的使用。眼下,我準備以‘輸液’問題作為突破口,希望能夠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早日將醫療器械問題的立法提上日程。” 陳曉蘭說,輸液是一種看起來十分普通的醫療方式,但是絕大部分人包括醫務工作者都未曾意識到,其中存在著相當大的隱患。“很多病實際上根本用不著用輸液的方式來治療,何況這種方式會增加污染的環節。本來沒有質量問題的藥品,如果碰上了不規范的操作或者是不合格的輸液器具,就會被污染。然而很多醫生卻將輸液當作是一種萬能治療方式。”陳曉蘭說,她在很多醫院都發現有一些只會讓病人輸液的“一瓶”醫生,“他們的專業水平在我看來一塌糊涂,不論男女老少,不管什么病,都是掛一瓶水了事。” “實際上,醫生完全可以開同樣成分的藥片給病人服用,但是這樣一來醫院就賺不到錢了。”陳曉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先鋒6號”抗菌素來說,采用輸液的方式,算上器械費、藥費、治療費、躺椅費什么的,一下就比用藥片的方式貴了六七元錢。 “更可怕的是,藥液經過劣質輸液器增加了污染。一些無法溶解吸收的微粒可以形成各種異物栓子隨血流動,對器官、臟器存在著潛在的栓塞、梗死威脅,使其增加了感染機會。尤其是肺栓塞,在X光等射線下,無法判斷出其與癌癥的區別,許多醫務人員就會按照癌癥來進行治療。” 令陳曉蘭更加不安的是,一些醫院在補液中擅自加入各種藥品的問題更加嚴重,“現在不少醫院將一些中藥材提煉出的成分直接加進輸液的補液中,有些成分只能用糖水來稀釋,但是遇到糖尿病人的時候,不少醫生會直接將其注射到生理鹽水中。而這種做法完全沒有進行過合理的臨床實驗。” 說了實話,卻丟掉了飯碗 陳曉蘭出身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當年的名牌院校大學生。15歲那年她下鄉做了“赤腳醫生”,1976年回上海。從工人、廠醫一直做到地段醫院的醫生,她處事小心謹慎,頗有人緣。陳曉蘭說,在同事眼中,她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不計較獎金的多少,也不喜歡討好領導。“說實話,要不是因為‘光量子’的事情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當年我也不會想管這樣的事情。”陳曉蘭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是發生在1997年的一件事。 陳曉蘭說:“當時我是虹口區一家醫院理療科的醫生。一天,一個老病人跑來找我。她說醫生讓她打激光針,還說不打針就不給開藥。這個病人為此很苦惱,因為她見過其他病人打激光針的慘狀,幾乎每個人都會打哆嗦。” “我一聽,當時心中就一驚。根據醫療常識,我知道打針出現打哆嗦的情況,很可能是一種‘輸液反應’,估計所輸藥液內有不潔物質。我就到補液治療室轉了一圈,那里的護士指給我看一臺正在使用的一臺電腦主機大小的簡陋機器,這就是所謂的‘激光設備’了。我很疑惑:有些藥經過氧化光照后,藥性可能會改變,再輸入病人體內安全嗎?于是我仔細檢查了治療儀。發現儀器上寫著‘光量子氧透射液體治療儀’,同時還有ZWG-B2的字樣。根據物理常識,所有可見光發出的粒子流都可稱為光量子或者光子,而后面的英文字母,很顯然就是‘紫外光’三個字的拼音縮寫。所以,這顯然只是紫外光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激光’。我立刻明確告訴自己的病人千萬不要打激光針。” 然而陳曉蘭沒有料到的是,在不久后的一次醫院全體職工大會上,院長宣布:禁止任何人說“光量子治療儀”使用的不是激光。“我聽完感到更加奇怪,所以就下決心要弄清真相。我找來了‘光量子氧透射治療儀’的使用資料,看到光量子氧透射的治療理論是由上海醫科大學的陸應石教授提出的。后來我曾兩次前往上醫大人事處,結果卻讓我感到震驚——查無此人!” 陳曉蘭說,最后她終于了解到:所謂的“光量子透射治療”一次收費是40元,每開給病人一次,醫生可以拿7元的提成。每天都有病人在醫生建議下排隊打“激光針”,最高峰時一天達80余人次,營業額占到醫院的60%以上。難怪院方對她勸阻病人的舉動反感。 “越是這樣,我越覺得是在坑害患者,仍然堅持舉報。1998年3月24日,院方通知我‘全脫產自學’,這個時候我實際上就下崗了。到了6月份,上海市藥監局查實,和光量子氧透射治療儀配套使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輸液器’,其生產許可證編號、衛生許可證編號、產品登記號和國家專利號都是假的,責令醫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療,生產廠家被要求停產并回收產品。” 盡管當年的11月,醫院作出了“關于陳曉蘭同志自動離職的處理決定”,但是陳曉蘭覺得,至少“光量子”被取締了,這讓她多少有些欣慰。“我萬萬沒想到,這僅僅是一時的,后來我的同事朋友告訴我,光量子實際上還在使用。我騎著自行車跑遍了區內其他醫院,發現情況居然正像同事說的一樣,只好又一次到藥監局反映,結果工作人員告訴我,其他醫院沒有接到舉報,所以無法處理。而且不是誰都可以舉報,只有違規醫院的職工或受害者才行。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讓自己成為受害者。1999年2月1日至3日,我在四家醫院接受‘光量子’治療,拿到了充分證據。終于在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衛生局會同醫療保險局、醫藥管理局,作出禁止使用光量子治療儀和石英玻璃輸液器的決定。光量子這才被徹底取締。” 母親因誤診去世,陳曉蘭下決心不回頭 記者問陳曉蘭,當初舉報“光量子”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就決心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了。她很坦白地告訴記者:“一開始沒有想過那么多。但是,母親的過世給了我很大的打擊,她的囑咐成為我堅持下去的重要支柱。” 談起自己的父母,陳曉蘭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她說:“1999年8月2日,母親從澳洲回來不久,因咳嗽又去那家醫院內科看病,醫生改開了復方新諾明、敵咳,一周后病情好轉卻開始上腹部疼痛,惡心。到了10月10日,母親才告訴我胃痛了1個多月了。10月15日,母親的檢測報告出來了。我實在不敢相信,他們居然連癥狀非常典型的幽門梗阻也沒查出來,一直當胃炎治療。在我提出做胃鏡后,才發現是胃癌;發現病情之后,手術單上寫的是根治術,真正做時卻做成姑息術;手術3天后母親腹痛,值班醫生居然什么也不查就決定打杜冷丁……”陳曉蘭越說越感到氣憤,她覺得只要醫生在以上任何一個環節上負責一點,母親或許就可以多活幾年。 “也許我不該學醫,不該懂那么多,那樣就看不到母親在醫院里遇到那么多‘冤屈’了。” 經一再誤診而病故的母親的死給了陳曉蘭很大震動,而母親的囑托更是讓她銘記。陳曉蘭說,母親臨終前囑咐:“病人不懂,你作為醫生,任何時候都要保護病人利益。”這句話重復了多遍。 再次“以身試針” 揭露“鼻激光” 陳曉蘭告訴記者,2001年2月,經上海市信訪辦協調,多個部門聯合作出了對其問題的一系列處理意見,將她調往另一家地段醫院任理療科醫生。“我到了新的醫院后不久,又發現了問題:這里為患者提供‘鼻激光’療法。與‘氦氖激光血管內照射治療儀’(簡稱激光儀)配套使用的是‘口鼻腔光纖頭’(簡稱鼻頭)。在我看來,這個東西與原單位使用的‘激光照射’如出一轍。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這又是個包治百病的東西,使用范圍包括神經系統、心血管、內科、外科四大領域。” “外包裝上寫的是‘光纖針’,可是栓狀的‘鼻頭’怎么看都沒法跟‘光纖針’畫上等號。”陳曉蘭說。隨后的調查很快證實,“鼻頭”又是盜用了其他產品的注冊證號。經她反映,藥品監管部門這次很快取締了“鼻頭”,部分經營單位和使用單位受到處罰。 “但是‘氦氖激光血管內照射治療儀’沒有被取締,一種叫作‘光纖針’的東西隨后取代‘鼻頭’與‘激光儀’配套使用,其過程是:將針頭扎在病人手背上注入靜脈,藥物順著輸液針頭里石英玻璃光纖火紅色的激光同步注入病人的靜脈血管內。我收集的一些光纖針的包裝袋上,有些生產廠家明確標明著‘不可輸液’,有的卻標明‘可同時輸液’。” 陳曉蘭認為,“光纖針”要扎入病人體內,問題比“鼻頭”更嚴重了。于是,從2003年1月份起,她開始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反映氦氖激光血管內照射合并藥物輸液治療問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于2004年1月14日召開了一次論證會。國內激光醫學領域的權威,解放軍總醫院教授、中國醫學會激光醫學分會主任委員顧瑛表示:氦氖激光血管內照射療法的理論在臨床上尚沒有經過驗證,國際上也沒有得到承認,一開始就是不合理的。然而,2004年2月20日上午,同樣主題的會議再次召開。最后形成的意見認可了III類光纖針的存在,不過要求‘說明書告訴醫生如何使用;說明書未說明造成的誤用由廠家負責’。” 可是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出緊急通知之后,仍有醫院在激光照射時加入藥物。無奈,陳曉蘭說,2004年6月,她繼5年前親身體驗“光量子”之后再次開始“以身試針”,希望證明這個情況并且成為一個有資格反映問題的“受害者”。 此后,陳曉蘭又發現了一種“高壓靜電治療膜”的問題,并涉及醫療衛生領域的“騙保”現象,于是又以受害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訴訟。2005年3月1日上午9點,閘北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陳曉蘭起訴閘北某地段醫院一案。然而在被告醫院方的律師遲到40分鐘到庭的情況下,案件不了了之,而醫院沒有派人出席庭審。“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這個問題由來已久,不是我一個人三兩下就可以糾正的。” 陳曉蘭深感道路的艱難:“這些進入醫院的醫療器械很多是假冒偽劣產品,但在實際操作中,因為是‘醫療器械’,工商行政以及質監部門都很難對其進行處罰。而藥監部門,通常僅是按‘未經注冊’查處,一般是罰款了事,很難真正起到懲戒作用。至于對那些注冊過的但采用偷梁換柱的手法騙取醫療費的企業,甚至連罰款也很少進行。”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職場故事 > 正文 |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票:今日黑馬 |
| 怎樣迅速挖掘網絡財富 |
| 短線最大黑馬股票預報 |
| 海順咨詢 安全獲利 |
| 風情小布藝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時裝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創業賺大錢? |
| 品牌服裝 一折供貨 |
| 火爆粥鋪 四季穩賺 |
| 開冰淇淋店賺得瘋狂 |
| 美味--抵擋不住的誘惑 |
| 新行業 新技術 狂賺! |
| 投資3萬元年利100萬! |
| 05年開什么店好賺錢? |
| 05年投資賺錢好項目!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