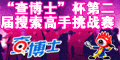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記者朱偉東
2003年11月30日,北京大霧彌漫,而煙臺這座海邊小城,由于剛刮完一場大風,天氣格外晴朗。滿街的張裕葡萄酒廣告特別晃眼。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們誰也不曾想到,讓煙臺人引以為豪的張裕葡萄酒已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品牌之戰。
糾紛
張裕對“酒業盟軍”的戰爭
中國葡萄酒行業卷入了歷時最長、牽涉企業最多、影響最大的一次商業糾紛。
11月3日,隨著長城、王朝等葡萄酒業巨頭聯合向國家工商總局反對張裕注冊“解百納”商標,使得“解百納”商標之爭正式進入司法仲裁階段。
事件進入白熱化階段可追溯到去年年底。當時張裕集團5年后重返央視招標現場,共投入2890萬元競得兩個時段,重點宣傳包裝“張裕解百納”這個核心品牌。但是,國內葡萄酒市場以“解百納”冠名的干紅葡萄酒不下20種,張裕全面包裝“解百納”商標的行為遭到了同行的激烈反對,他們邊反對邊通過價格戰搶占“解百納干紅”市場,推出的產品從10元到80多元不等,一時間解百納之爭風生水起。
就在此前,中國葡萄酒業發生了一件更加意外的事。2002年8月10日至14日,中國釀酒工業協會、煙臺張裕、中國長城、中法合資王朝等單位在甘肅召開行業會議,修訂10年前制定的《葡萄酒國家標準》。不久后,中國食品工業協會葡萄酒專業委員會及新天國際酒業也聲稱,要在2003年全國葡果酒會上拋出另一個新的“釀酒葡萄及葡萄酒技術標準和質量標準”,當然里面的技術標準制訂離不開“解百納”。一場關于解百納的“商標之爭”終于被演化成技術爭奪。只是后來由于企業間的意見不統一,最終結果不了了之。
針對市場上出現了不同廠家出品的30多種“解百納”,張裕葡萄酒集團總工程師李記明表示,正是因為張裕對“解百納”商標的歸屬有信心,才會堅定不移地為“解百納”的市場推廣進行大筆投入。除了在西部設廠外,同時還投入了大量資金布局高端產品市場,分別與泰國泰中酒業和法國卡斯特合作,擴大張裕在“解百納”干紅等高檔市場的市場份額。其中,與全球排第二的卡斯特合作內容包括:張裕投資參股49%卡斯特集團在河北廊坊的紅城堡葡萄酒;卡斯特投資參股30%于張裕在煙臺福山籌建的張裕酒莊,合資金額800萬美元。
而長城等其他葡萄酒巨頭也不甘示弱。2002年6月,新天國際葡萄酒公司以控股近80%的方式收購西域酒業;從去年開始,排行國內老大的中糧集團開始整合旗下的三大長城品牌,改變長城三家公司產銷一體、各自為政的現狀,不斷擴大自身的市場。華夏長城一位高層公開表示,中糧整合三大品牌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改變長城過去“一盤散沙”的局面,整合資源與張裕在高檔葡萄酒市場上展開爭奪。
解百納
“金山”還是“私家花園”
被業內人士尊為“高檔葡萄酒尊貴品牌”代名詞的解百納是座“金山”,而張裕堅稱這座“金山”從歷史上就是自己“私家花園的一座山”。據李記明介紹,早在1931年,當時兼任張裕經理的中國銀行行長徐望之就一直為張裕積多年之功而獨創的一種高檔葡萄酒沒有名字而苦惱,故在當時的煙臺國際俱樂部邀請了一批文人墨客來為之取名,最后決定秉承張裕創始人張弼士倡導的“中西融合”的理念,取“攜海納百川”之意,將之命名為“解百納干紅”。隨后,張裕于1936年9月15日經當時的“中華民國實業部商業局”批準,正式注冊了“解百納”商標,并取得了注冊證書,注冊證號是第33477號。
“這些資料可以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到,張裕并不是杜撰歷史事實。”李記明博士如是說。據李介紹,張裕曾在1939年《釀酒雜志》刊登了一篇關于葡萄酒的分析報告,拉開了“解百納干紅”叫板國際品牌葡萄酒的序幕。1959年,張裕又向當時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注冊“解百納”商標,并準予備案。爾后,張裕先后對解百納干紅的工藝進行了改造,并多次在布魯塞爾等國際博覽會上獲獎。同時,為了保護自己傾力打造的核心品牌,在商標法頒布后的1985年和1992年,張裕又將解百納向國家商標局申請注冊,但因張裕高層人物更迭頻繁,最后不了了之。2002年2月,張裕再次向國家商標局申請注冊成功,4月拿到證書。
可是就在張裕解百納商標注冊成功后一個月,就遭到了長城、王朝等企業的聯名反對,并上書國家工商總局申請取消張裕的注冊。“張裕不能私自擁有解百納,因為解百納應該是紅葡萄品種的中文名稱,而不是商標專用名稱。”中糧集團長城酒業生產部有關人士如是說。
王朝的高層人士表示:“假如因為自己從英文里找到一個單詞,就把中文意思給注冊了,并宣稱這個名稱是自己創造的,那也有點太荒唐了。”據反對張裕私自擁有解百納商標的人士介紹,解百納一詞是由“Cabernet”翻譯而來,解百納干紅的一些主要原料赤霞珠、品麗珠、蛇龍珠的英文字母都有一個共同的字頭“Cabernet”,所以它應該是紅葡萄品種的中文名稱,而不是商標專用名稱。反對張裕的這些企業也用書籍記載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有關葡萄酒的書籍中,有將赤霞珠稱為“解百納”、品麗珠稱為“解百難”、“卡門耐特”的說法。
對此,李記明博士反駁說,70多年來,張裕始終將“解百納”作為一個品牌和一個注冊商標在使用,有著不可否認的連續性,其他少數企業抄襲和仿照張裕的產品生產時間也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不能因為少數企業近幾年的抄襲仿照使用,就認定其是葡萄酒品種、品系或商標的使用名稱,而去否定一個具有70年生命力的商標。
雖然張裕遭到了其他葡萄酒巨頭的聯合攻擊,但是得到了葡萄酒專家及中國農學會葡萄分會、中國釀酒工業協會等部門的支持。中國農學會葡萄分會晁平教授表示,解百納僅僅是商標,而不是一個品種或品系。晁教授說,我國葡萄品種近千余種,在已正式公布的葡萄品種名錄中,并沒有“解百納”這個品種,而且將赤霞珠、品麗珠和蛇龍珠等三個截然不同的葡萄酒品種歸為一類顯然不合適。他解釋說,“解百納”首先出現是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山東張裕葡萄酒公司所生產的一個紅葡萄酒品牌稱之為“解百納”,但在全國葡萄學術界和生產上一直沒有應用過“解百納”這個葡萄品種名稱,同時葡萄品種中也沒有“解百納”這個品系。
博弈
WTO語境下的品牌保衛戰
“解百納”商標之爭背后所隱藏的是利益之爭。解百納干紅實際上已成為中國中高端葡萄酒的代名詞,成為了國產葡萄酒與洋品牌對抗的重要產品。
據有關數據顯示,世界葡萄酒業每年增長速度不到1%,而中國葡萄酒業每年增長速度超過了10%,中國乃至亞洲已經成為葡萄酒業最具潛力的市場,而解百納的銷量占整個產業銷量的近三分之一左右。目前全國已經有30多家企業在使用“解百納”招牌。正因為此,長城、王朝等企業認為,解百納目前已成為一個品種的通稱。如果張裕注冊“解百納”商標成功,其他企業都要面臨承擔侵權責任、銷毀包裝、更改名稱的系列后果,這樣將使更多的廠家利益大受影響,甚至影響到整個葡萄酒行業的發展。
但是,張裕的李記明也表示,30多家企業一擁而上,讓消費者無法分辨真假,損失最重的還是消費者。從長遠來看,解百納一旦淪為假冒者牟利者使用的品牌,中國葡萄酒行業就等于失去了對抗外資洋品牌的利器。
導致品牌之爭如此激烈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洋酒壓境。據了解,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進口葡萄酒關稅高達65%,加之高消費稅和增值稅兩項,綜合稅率曾高達150%,這導致了進口葡萄酒的價格一直偏高,而在以后關稅減低的情況下,必然會降低洋酒進入國門的成本,估計大部分洋酒的價格會與國酒持平。如何盡快爭得更大的份額,也是國內幾大葡萄酒巨頭最關心的事。
“未來兩年中國葡萄酒企業將與洋品牌處于同一起跑線。”李記明表示,按照WTO協議,中國葡萄酒關稅將于明年繼續調低至14%。屆時,洋葡萄酒將會大舉進入。在張裕看來,這種局面早已被預見。張裕打算以解百納的自有知識產權去對抗外來品牌的侵襲,本質上就是更高利益層面上的一種博弈。
-記者手記
百年木桶靜說歷史
在長城、王朝等企業發難后,記者第一時間與張裕方面取得聯系,要求前往煙臺采訪張裕集團負責人,但卻被對方以“媒體報道太多但不準確”為由遭到了拒絕。無奈之下,記者提出采訪對“解百納”技術非常了解的張裕總工程師李記明博士,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復。
見到李記明后,給記者印象最深的是,他老在重復著一句話:“歷史勝于雄辯,我們擁有最原始的證據,誰也無法抹殺張裕與解百納之間的歷史。”而在張裕的地下酒窖,記者看到,不少有著百年歷史的橡木酒桶靜靜地陳列在那里,黑漆漆的桶身仿佛在向每一位參觀者傾訴著解百納70年的滄桑。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些大橡木桶多來自法國。張裕生產的葡萄酒需要把新桶盛的酒和老桶盛的酒按一定的比例進行適當調配,而這些技術參數都是張裕經過多年的摸索積累而得,也是其他葡萄酒企業難以望其項背的。
“明年中國葡萄酒行業競爭將異常激烈,如果再不珍惜機會,保護解百納品牌,張裕將很難有超越對手的機會了。”李博士的話透著一絲焦急。可是,誰又知道解百納之爭何時是盡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