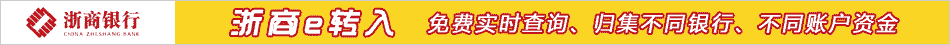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需新制度平臺 須保護農民土地權益
新型城鎮化需要新的制度平臺
唐黎明
十八大以后,新型城鎮化再度被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成為輿論關注和討論的熱點,甚至引發股價和房價的波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可見,新型城鎮化與以往城市化路徑最不一樣的,就是從城市規模的擴張,轉向城市質量的提升。
過去三十年的城市化模式,主要依賴于“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即以政績考核體制為中心,環繞著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與行政化的城鎮等級制度,它們共同構建了現有的城市格局和經濟發展模式,也種下了城市問題的種種因果。
所謂城市化,無非就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過程。在市場經濟國家,在沒有任何限制人口遷徙的政策環境里,農民進城,或者是城市間人口遷徙的選擇,只是受市場因素的影響,政府無法干預他們的選擇。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人們可以選擇大城市,也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生活成本、就業機會和居住環境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然而,中國近代的城市化進程,從一開始就是伴隨著對人口的限制。上世紀50年代末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目的是把農村人口強制束縛在土地上,低價提供農產品(5.70,-0.12,-2.06%),用以維持城市居民的低工資,確保國家通過獲取剩余價值來完成工業化積累。實際上,戶籍制度不僅僅限制了城鄉人口的流動,也通過集體經濟組織按照戶籍制度分配土地和福利,限制了農村村莊之間的人口流動。
戶籍制度的約束,使得名義城市化率和實際城市化率之間有很大的差距。截止到2011年底,我國的名義城市化率達到51.3%,但實際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這16%的差距,是生活在城鎮里的“半城市化人”沒有城鎮戶口,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和配套設施的差距。城市化,意味著人們的生產方式、職業結構、消費行為、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都將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而半城市化,是這部分人在生活和消費等方面都沒有達到城市居民的水平,是一種典型的城市化質量不高的表現,也難以拉動消費和內需。
與戶籍制度相呼應的是,土地制度也是決定現有城市格局的關鍵制度。
城市化最重要的載體是土地,過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路徑,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土地(政府征收土地的成本是低廉的)基礎上的粗放擴張。
2001年,我國開始實行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收購儲備機構成為了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供應者。在土地收購儲備制度之外,還輔之以“招拍掛”,以及 “價高者得”的參與規則,使政府成為土地市場的壟斷供應者,保證了地方政府成為土地出讓收益的最大受益者,也使得地方政府嚴重依賴于土地財政,除了賣地賣房別無發展路徑。現行的土地制度,是城市規模不斷攤大餅式的擴張,城市化質量卻乏善可陳的主要原因。
這種低成本的粗放擴張,是以損害農民權益為代價的。農民付出了土地,卻沒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利益,征地沖突不斷,也埋下了社會不穩定的導火索。實際上可出讓的土地是有限的,一個城市的擴張也有邊界,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以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為切入點,遏制城市的粗放擴張。
簡單來說,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提高農村土地價格,要讓土地收益更多地進入農民自己的口袋。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城鎮化推進的成本,逼迫各地放慢推進城鎮化的速度,從而更加注重土地的集約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另外,農民通過土地制度改革拿到更多財產收益,既可以縮小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也可以推進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從而進一步提高中國城鎮化的質量。
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處在“后土地經濟”時代。各地方政府需要看到,土地不僅是商品,可以拿來買賣,土地以及以土地為基礎的城市更是寶貴的資產,需要用心經營,使之增值。在經營土地方面,除了蓋房子,地方政府需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產業升級等諸多方面下工夫,推動資產價值提升,并從中開辟新的地方財源,形成良性循環。
除了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外,行政等級化的城鎮化體系,也在擴大城鄉差距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差距方面推波助瀾。城鎮化與城市化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卻決定了資源和政策的不同投向。中國的城市是等級化的金字塔型結構,從行政級別而言,市可以管縣,縣可以管鎮,鎮可以管鄉……上下級城市間存在著公共財政、公共資源管理和分配的關系,使得資源和資金可以更多地流向行政等級較高的城市。
城鎮分級固然沒錯,全世界都有不同等級的城鎮,但這是自然形成的結果,有著內在的經濟邏輯和社會邏輯。中國等級化的城鎮體系,是由行政等級造成的,是人為造成的格局。這種等級體系的實質是:資源隨權力聚散,而不是由市場定價,這樣的流動是以損害弱勢地區的利益為基礎的。
高等級的城市通過行政手段和等級優勢獲取更多的資源,日新月異地完善著自己城市的基礎設施,改善著本地居民的公共福利。而級別較低的城市,賴以為生的資源可能被剝奪,本應大力改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福利,因地方財政薄弱也顯得遙遙無期。京津和周邊的城市差距,無疑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北京作為首都,依托行政權力,吸收著周邊乃至全國的資源供給,留下的卻是貧窮,甚至形成了著名的環京津貧困帶。
行政等級化的城鎮體系,與政績考核體制糾結在一起,加劇了大城市與中小城鎮間的不平衡。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長、市委書記的晉升途徑和城市的利益關系就變得緊密起來。一方面是政績的利益,一個城市的發展好壞,可以作為政績的最好體現;另一方面,高等級的行政官員一般都住在等級較高的城市里,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居住環境的改善,直接和官員的個人居住環境發生了關系。這使得資源和公共服務更傾向于向高等級的城市集中。
決定中國城市格局的三個基本制度,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唯GDP是從的政績考核機制”打轉。
1953年,聯合國[微博]發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及其附表”,GDP是核心指標,此后,GDP受到部分經濟學家追捧。在中國,GDP成為官員考核的重要指標。GDP考核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僅僅是流量指標,無法反映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否協調,貧富差距是否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環境是否可持續等。從拆遷矛盾到環境問題,從形象工程到群體事件,這些尖銳的社會問題,都可以從既有GDP考核體制中找到制度根源。“唯GDP是從”的政績考核體制,鼓勵官員只注重經濟指標的片面增長,而忽視社會的均衡發展;只盯著數字的增長,而忽視民生的幸福;只看到表面的光鮮,而忽視發展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城市也成了彰顯政績的舞臺,大廣場、大馬路、大景觀無處不在,非大不足以說明當政者的豐功偉績,然而這樣的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新型城鎮化,呼吁的是新的發展模式,展現的是新氣象,不再是以往依靠基建投資驅動經濟發展,不再是過去依靠大拆大建的表面城市化,更多的是制度層面的變革,尤其是政績考核制度、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行政等級化的城鎮制度的變革,否則,新瓶裝舊酒,缺乏制度變革,何來新型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