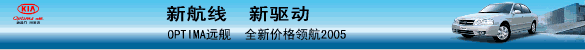沒有身份十分神秘 賭博成暴富后生活方式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21日 09:49 三聯生活周刊 | |||||||||
|
特約記者 劉鑒強(發自朝鮮) 在離中國邊境54公里的朝鮮羅先市東海邊,一座在朝鮮境內從未見過的豪華高樓孤零零矗立在海邊,那里是“英皇娛樂酒店”,中國人稱其為“英皇賭場”。2004年底,記者在賭場的時候,五六十位中國人,正在里面沒日沒夜地玩“百家樂”、輪盤賭和老虎機,將鈔票大把大把地扔給賭場。
如果再看一眼周圍的環境,會發現,在這里發現如此豪華的賭場,是多么奇異的事情。賭場不遠處,即有朝鮮民居,低矮破舊,門窗極小,想來是為了抵御朝鮮北部冬天的寒風。再往遠處走,有一個市鎮,其陳舊蕭條,極像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小鎮,一派灰蒙蒙,惟一鮮艷的,是那氣勢恢弘的高大水泥宣傳欄,上書鮮紅的朝鮮文:“金正日是21世紀的太陽!” 而在英皇賭場內,充足的暖氣、紅色的大理石地面與紅色的座椅,以及綠色的熱帶植物盆栽,會立即讓人忘掉這里是寒冬中的朝鮮。大廳里的上百人,全說中國話。即便是朝鮮服務員,也操著流利的漢語。賭場的大門,有朝鮮保安把守,除了朝鮮員工,嚴禁其他朝鮮人進入賭場。中國人同樣是這里最主要的賭客。不久前,中國吉林延邊州交通運輸管理處處長蔡豪文,挪用公款351萬元到境外賭博,事情敗露后,畏罪潛逃。 最便捷的賭資通道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簡直無法相信,避開中國的法律,到朝鮮賭博,居然是如此輕而易舉。 2004年12月中旬,記者來到吉林延邊州,這里有許多旅行社,門口豎著刺眼的招牌:“入住英皇”。“英皇”即是設在朝鮮北部羅先市的大賭場。這里的旅行社,將入住英皇進行賭博,作為招徠游客的金字招牌。不需要護照,只要交上450元,拿到一張“入出境通行證”,你就可以去朝鮮一賭。 第二天早上8點,33位賭客,乘坐旅行社的白色中巴車,從延吉出發,赴琿春圈河口岸。在導游手里的名冊上,這些人的身份清一色全是由旅行社代填的“個體”。顯然,如果賭客是領導干部和公務員,身份也不會暴露。吉林延邊州原交通運輸管理處處長蔡豪文,就像這些賭客一樣,沿這條線路,很方便地赴朝鮮賭博。7個月間,他去了27次,輸掉公款351萬元,以及親戚朋友的借款。 對東北三省和華北的賭客來說,與遠赴澳門、緬甸參賭相比,近在咫尺的朝鮮賭場顯然更加方便。蔡豪文案后,延邊州紀委到圈河口岸調查得知,這個口岸一年出入朝鮮人次達25萬。而從州公安局得到的數字,其中“休閑游”,也就是純粹到朝鮮賭博的,超過5萬人次。 中巴車在冰凍的圖們江左岸疾馳,江那邊,就是被白雪覆蓋的朝鮮。導游小姐提醒乘客,朝鮮規定,入境只許帶人民幣6000元,或是美元5000元。“你帶美元比較合適,”導游小姐說,“那等于40000人民幣,而且,在英皇賭場,籌碼也是用美元計算的。” 導游和記者說,如果需要帶更多的錢入境,他可以給你提供一個交通銀行的銀行卡號,你把錢存入卡內,拿著銀行的收據,到了英皇賭場就可以提現金。 實際上,即使不用銀行卡,大量現金過鏡也暢通無阻。在中朝邊境,朝方對現金入境的控制,只是象征性的,朝方禁止入境的是以下物品:手機、傳呼機、MP3、光盤。對報紙、雜志、書籍的入境也嚴格控制,如果是在朝工作的中國人,堅決要求帶入某些報刊,則必須登記,不管在朝鮮境內呆多長時間,離境時,一定要帶回曾登記的報刊。英皇賭場的一位工作人員后來告訴記者,一位中國賭客誤將手機帶進朝鮮口岸,被朝方查獲,等他賭完回國時,朝方人員給他一個塑料袋,里面是拆碎了的手機。對所有的信息傳播載體,朝鮮閉門不納。他們最歡迎的,是中國賭客的錢。 英皇賭場里,有一排排的老虎機,也有輪盤賭,人氣最旺的,是5臺百家樂紙牌桌,最低下注額分別為10、50、100、200、300美元。在賭場一邊的臺階上,屏風后面,是兩臺下注額最大的牌桌。一位40來歲的東北男子最引人注目,下注額最高,短短10分鐘內,就贏了40000人民幣。每當開牌時,大家狂呼亂叫,翻紙牌的手顫抖著,等翻過來,紙牌已皺得像折扇一般。幾個回合下來,輸了的人,一句話也不說,轉身離開,轉戰別的牌桌。 邊境線上賭場林立 英皇賭場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英皇賭場屬于香港英皇集團,老板是楊受成,幾年前英皇集團經朝鮮同意,在此地建造英皇娛樂酒店,花費數億港幣,賭場開業不久,成本便收回。 延邊州紀委的李敬民主任曾赴英皇賭場調查。他說,英皇賭場的稅收不交給朝鮮羅先市政府,而是直接交給朝鮮中央政府。但至于每年交多少錢,他沒有確切的數字。 賭場的那位工作人員說,英皇賭場有大約500名員工,高層管理人員大多來自香港,其余職工,中方和朝方各半。中方一般員工,月薪自2000元人民幣起不等,而朝鮮員工不論職位高低,一律月薪80美元。后來,朝方提出,因為美國是朝鮮的頭號敵人,朝方不愿領美元,改為月薪80歐元,約合人民幣800元。 但是,朝方員工的大部分收入要上繳國家,自己僅能留下大約24元人民幣,這等于朝鮮一般工職人員月薪的兩倍。李敬民在調查時,曾問過一位朝鮮員工:“你們的收入還不到中方員工的1%,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這位朝鮮員工很自豪地說:“賭場向我們國家交了大量的錢,我們很榮幸為國家做貢獻,所以,我們不在乎自己的工資。” 為朝鮮財政做貢獻的,自然不是朝鮮員工,而是中國賭客。李敬民在賭場秘密調查時,親眼看見一位長春女士,在一天兩夜里,不吃飯,不睡覺,連續36小時賭博,最后輸掉5萬人民幣。而賭場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曾見到,一位中國賭客在一天半的時間內,輸掉400多萬人民幣。而目前被通緝的交通運輸管理處處長蔡豪文,在7個月里,挪用的公款加私人貸款、借款,共貢獻給英皇賭場700萬元人民幣。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朝鮮大量走私日本汽車進入中國,使延邊許多汽車走私商人暴富。“英皇”建立后,最先來賭的就是這批人。很快,這些暴富者的錢全扔進了賭場,現在大量被賭場套住的人,除了地產商人,就是企業主和官員。 李敬民算了一筆賬,每年有5萬人次進入英皇賭場,如果以每人每次輸掉5000人民幣算,一年就是2.5億人民幣。這還是最保守的數字。 更為嚴重的是,像英皇這樣的賭場,密布在中國的邊境線上,并且正在快速增加中。在黑龍江的中俄邊境線上,只要有口岸,就會有大大小小的賭場。最近,在綏芬河的中俄邊境線上,香港上市公司“世貿中國”投資100億元建設的“綏——波”貿易綜合體里,就包括一個巨大的賭場。 從圈河口岸往北走30公里,就是長嶺子口岸,從那里可以進入俄羅斯。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克拉斯基諾市,中國一公司開了一個賭場。如果從克拉斯基諾市乘船,兩個半小時后,就可到達海參崴,那里有個大賭場。當然,不管是哪兒的賭場,賭客基本上都是中國人。 而在中蒙邊境線上,也剛剛建了一個賭場。據云南公安部門最近公布,周邊國家靠近云南邊境地區就有賭場82家。這些賭場的基本目標都是中國人,在朝鮮,除了英皇的朝鮮員工,任何朝鮮人不許進入賭場。 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一次會議中說,黨員到境外賭博的,要一律開除黨籍。 但如何查處這些官員,顯然并不是那樣容易,延邊州紀委黨風室主任李敬民現在掌握了到朝鮮的5萬人名單,但是,調查賭博者非常困難,“他要是死活不承認,你沒有旁證,也沒有辦法。”他說。延邊州公安局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說,中國公安部目前對中國公民赴境外賭博也沒有好的辦法,“我們希望他們盡快出臺一個政策,否則我們不知道怎么做。”他說。 斯里蘭卡:沒有身份的中國賭客 很難說,是賭場的神秘讓賭客顯得神秘,還是賭客的神秘造成了賭場的神秘。反正,在賭場,沒有人會追問你的身份和賭資的來源,在管臺的荷官們用筢桿把滿桌花花綠綠的籌碼推成一撂的時候,錢一點也不具體。記者在科倫坡賭場看到的絕大多數面孔都是中國人,他們中的有錢人不多,并且大部分身份曖昧。在科倫坡開餐館的王玉民告訴記者,在這里,有人把賭博看成正式工作之外謀的另一份差事,有人是用白天掙得不多的錢拿去下注,也有人只是為了一頓免費的晚餐,另外一些人在賭場里等待或尋找各種機會和生意。賭場成為這些沒有身份的人生存的一個獨特空間,作為賭場最主要的客戶,科倫坡的華人和賭場形成了相互寄生的關系 朱文軼 “21點”和身份曖昧的中國賭客 1月3日,斯里蘭卡當地時間下午3點多鐘。科倫坡最大一家賭場MGM里熬通宵的客人剛剛差不多散盡,服務生在小心地擦拭金碧輝煌的欄桿扶手,距離再一次賭客光顧的高峰時間還有七八個小時,這是MGM一天內惟一的清閑時光。剩下的人里,一個叫易琴(化名)的中國女人最顯眼。記者是后來從別人嘴里知道了她的名字,科倫坡的華人不知道她的實在沒幾個。這個40歲左右的中年婦女,皮膚白皙,文雅地扎著高高的發髻,頭發和衣服整理得一絲不茍。她看起來有一張沉著的臉,目光不時輕巧地瞟旁邊的另一個中國人,手指熟練地玩弄著籌碼,拇指和食指飛快地把第一個籌碼挪到最后一個,再把最后一個挪上去,如此反復。這是賭場熟客們的標致性動作。科倫坡賭場每一個籌碼的面值通常在500、1000、5000、10000盧比(1000盧比大約等值于100人民幣)不等,在這家MGM賭場,為了招徠更多賭客,很多賭場在換籌碼時還多給客人10%到30%,如換100美元,可以領到120或130的籌碼,稱之為虛碼,但是這些錢不能換成現金,只能在賭的過程中逐步換成實碼。 易琴在綠色的賭桌前時站時坐,她的手指在三顆寶石戒指的底襯下顯得更加纖細修長。這種紅、藍寶石是斯里蘭卡最負盛名的特產,有人告訴記者,像易琴手上這種好成色的玉石品種,只有當地經營種植業和寶石礦開采業的有錢人才能擁有。 易琴正在玩的是“21點”。MGM最主要的三種賭博是,21點、百家樂和俄羅斯輪盤賭,記者沒看到老虎機,后來聽別人說,在科倫坡賭的中國人,要么是蹭飯吃的,要么都玩得很大,老虎機在這兒不受歡迎。“21點是這幾種賭博里技巧多于運氣的一種,中國人更傾向于它,有段時間,賭場輸多了,曾禁止中國人玩21點。”說這話的叫Lewis Lee,是在斯里蘭卡經營服裝生意的臺灣人。Lewis Lee是個玩21點的行家。他告訴記者,21點講究“消牌”,這是可以算的,賭的人越少,算得越容易,贏的把握也越大,所以他總在晚場散了,下午的時候進賭場。“這個時間人最少”,他說,要盡量把湊21點的牌控制在3張以內,而且都在3倍和4倍消去,每輪的牌是有限的,這樣可以增加消去的機會。5張小牌消去是最不實惠的,一個A和一個10點組成21點是最佳選擇,其次是兩個數組成11,再來個10點,因為10點太多了,所以在3、4倍區域存的牌最好都是11點,這樣很容易消,富余牌在空的4倍消去是最好。 易琴顯然玩得并不太好,她跟另一個后進來的女人發牢騷,聲音很響地說,今天的手氣太差,輸了500萬盧比,所以她一直不肯走,賭了將近16個小時。這個數目聽起來實在很難不讓人對她的身份產生好奇心,記者在她離開后,試著向周圍人打聽了一次,但被拒絕了。 作為交際場的賭場 一年中多數時候都享受著印度洋充沛陽光的斯里蘭卡首府科倫坡的大部分時間里,店鋪有氣無力地開放著,這里的商業和娛樂活動遠沒有它的宗教氣氛那樣濃厚。倒是一些骯臟、不起眼的市井之地,垃圾成堆,烏鴉遍地拾食,忙碌地走動著光腳的蘭卡小販和戴著頭巾的家庭婦女,展現著充徹本土氣息的原始生機。這些地方給許多底層的斯里蘭卡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并衍生出其他的種種交易,比如倒賣外匯和皮肉生意。色情業被這個佛教國家明令禁止,卻成為來自泰國、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等性服務業人員在當地的主要謀生手段。而這些魚龍混雜之處最豪華的建筑往往就是賭場,在某種意義上,賭場成了底層和權貴、商人階層的銜接物。Lewis Lee說,科倫坡沒有太大規模的賭場,BALLY’S和MGM算是大的,MGM的老板很愿意在科倫坡華文報和華人廣告公司登廣告,收費貴點也不在乎,可能就是料定中國人口袋里的盧比和美元是最容易放到他的賭桌上的緣故。 王玉民把華人嗜賭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他認為,出境的華人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異域,缺乏當地語言文化基礎,難以融入當地社會,不約而同地走入賭場,“有錢人因娛樂生活單調乏味而到賭場消遣,辛勞的打工階層因薪水太低而進入賭場去尋找機會”。 Lewis Lee說,賭場成本開支相當之大,去年科倫坡一家賭場一年要向政府上稅1000萬美元,今年稅金再度提高,幾乎翻了倍,要交將近2000萬美元。并且,MGM從開放賭場設置到現在的10年時間,賭場光在食物與飲料上的支出就砸下天文數字,以確保能夠將賭客留在賭場之內,他們光去年在這方面的開支已經達到5000多萬美元,這樣龐大的投資很自然地,使其他沒有經營賭場的餐館,完全失去競爭力,這也是科倫坡賭場周邊的商業和娛樂如此冷清的原因之一,“我知道,1995年MGM開業前,科倫坡三區的餐館還有60多家,開業后只剩下11家,等于有七八成的餐館倒閉,而其中多數是中餐館,可見華人在賭場的消費占了多少”。 1月4日,記者在BALLY’S賭場看到了在這次海嘯中受傷的阿芳,她一瘸一拐地拖著傷腿走進賭場,跟賭場每個碰面的人笑著打招呼,全然看不出,幾天前,記者采訪她的時候,她還渾身是傷。聽說,當天接受完采訪,她又去賭場了。阿芳也是這幾個賭場的常客,和每個工作人員都熟。她在MGM賭場里認識她現在的男朋友,是一名斯里蘭卡現役飛行員,在這個國家這是相當體面的一個職業,這也是件讓她在科倫坡華人朋友圈里頗為得意的事情。阿芳和另兩個在海嘯里死里逃生的中國女孩接受記者采訪時有過很多顧慮。在賭場打工的中國人阿素后來告訴記者,事發后,在當地華人中有很多傳言,說三個人當時是去加勒海邊一家旅館做應召生意的,“這讓她們很生氣”,阿素說,不過,另兩個人的確是在科倫坡一家按摩院上班,“斯里蘭卡禁娼,色情場所往往以醫院和醫療按摩院的面目出現”。 從大陸到斯里蘭卡做皮肉生意的小姐并不一定從開始就是直接奔著色情業去的。王玉民說,這個國家并不發達,也沒什么市場,中國護照去斯里蘭卡很容易簽證,一些蛇頭利用這點大量組織偷渡,最有吸引力的賣點,是說這個國家可以作為跳板到第三國謀發展,比如歐洲的主要國家、加拿大等,“辦一個人的費用,他們收得很高,通常要3萬~5萬,錢到手了,人接到科倫坡,就不再管了,許多女孩子流落他鄉,惟一能選擇的就是色情業。因為中國小姐近年增多,她們之間也相互壓價,一次性交易的價格甚至只有泰國小姐的一半”。 阿素對記者說,阿芳和易琴都做過蛇頭生意。她說,在賭場一擲千金的易琴在上世紀90年代初靠辦非法移民的資金起家,開了按摩院。那時候,色情業在斯里蘭卡剛剛興起,生意很好做,加上她騙到科倫坡的中國女人,沒有工作做,最后就都到她的按摩院干活,“每月好的時候可以有1.5萬~2萬美元,房租和伙食都是小姐自己付,一次交易易琴還得從中抽700盧比的人頭費,所以易琴現在少說也有幾百萬美元的身家”。 “對有著各自目的的賭客來說,賭場成了另一個意義上的交際場。”Lewis Lee說,一些做皮肉生意的小姐把晚上掙的錢白天全輸在賭場上,不過,她們的目的不止于此,她們希望能在賭場結識一些做生意的香港、臺灣商人。“賭場也滿足了一些小姐對奢華生活的想象”,他說。 越南芒街:邊境賭場的一個樣本 記者 李菁 進入芒街的第一刻,并沒有感覺“出境”,反而需要一遍遍地提醒自己才意識到:這已經是越南了。很多方面都是那么相似,國旗、國徽、甚至包括大街上橫拉著的紅色標語、為慶祝2005年新年的彩色小旗,如果不仔細看上面的文字,只會感覺自己是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鎮,而“芒街”又是那么一個有中國味道的名字。 我們是從廣西的東興口岸進入越南的,之前除了交給旅行社的費用外,又花30元拍張照片便很快拿到有效期只有幾天的“入出境通行證”。中午11點,等待過關的大部分是中國游客。從越南過來的導游阿珍瞥了眼人群,很直接地說:“你們一人拿十塊錢吧!可以快些!”大家每個掏了十元,阿珍夾在薄紙里遞進窗口,果然很快就入境。 自90年代以來,東興的邊貿成交額每年高達十幾億元,已經成為繼深圳羅湖、珠海拱北后的中國第三大口岸。出了東興大門,就是橫跨北侖河的友誼大橋,導游說當年中越戰爭時,這個橋曾被炸得支離破碎,后被中方修復。兩國就以大橋中間的一條黃線為界。中國東興這邊群樓林立,河對岸則放眼望去一片平坦。據說芒街是越南北方最富裕的城市。1元人民幣等于1700越南盾,所以從理論上講,只要帶超過600元人民幣入境,在越南就已是貨真價實的“百萬富翁”。 “我們馬上將要‘參觀’一個賭場。”一進入芒街,導游不停地強調這個詞,所有的中國游客也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站在街旁沒幾分鐘,很快來了一輛面包車,徑直把大家拉到一座寫有“利來國際博彩俱樂部”的淡黃色圓頂建筑前。后來才知道原來這并不是公共汽車,而是精明的商家派出的免費接送車,每天固定在芒街的賭場和幾個購物點之間往返,周到得讓人吃驚。 與芒街其他建筑相比,這家“俱樂部”已經相當氣派。可以看出,從外形到賭具,利來基本模仿澳門賭場,但顯然遠遠落后幾個檔次。不過賭場的“起點”并不低:賭城里只接受人民幣、港幣和美元,但都必須兌成美元籌碼下注,而最小籌碼是1美元。 這家賭場是2000年建成,股東主要是中國人。因為賭博在越南被明令禁止,所以這家賭場嚴禁越南人進入——后來發現賭場的門口坐了兩個穿制服的越南人,他們應該就是專門負責禁止本國人入內的。但奇怪的是,來來往往很多游客,自始至終沒有發現他們要求誰出示證件,萬一有越南人入內,他們怎么發現呢?阿珍淡淡地說:在芒街呆長了,一眼就能看出誰是中國人,“穿著、舉止、眼神,特別是眼神,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在與中國毗鄰的邊境小城設置的賭場,越南本地人又被禁止入內,它的目標其實很明確:中國人。賭場的情況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從服務生到賭客幾乎全是中國人。不過細細觀察,這種邊境小賭場的高端客戶似乎并不占多——與我們同團的是山東一個農民企業家代表團,雖然這里只與中國一河之隔,但也算是他們的第一次出國。其中據說是團中最有錢的木材商輸掉了最多的80美元。 利來2000年春節左右開門迎客。據說開業頭一年,利潤就達1.6億人民幣,所以一度獲越南有關部門的“通令嘉獎”。有人說近兩年,中國賭客為這家賭場帶來了每年8億元人民幣的利潤。導游小方說,在與廣西北海相對的越南的海防市,還有一個圖山賭場,由越南政府與何鴻聯營。 一個統計數字說,現在每天到東興和芒街的游人和客商都有1萬多人。由于賭場每年為當地創造巨額利稅,曾經是布滿地雷的荒蕪之地芒街已從過去的貧困地區一躍成為越南“最大的經濟開發區”,也成為越南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錢基本上都是中國人送來的,”一個中國人如此評價。據說,越南政府已經開始推廣經驗,決定在與中國相鄰的所有口岸、邊貿點開設賭場。 馬來西亞:奢華的“云頂” 陽光 一車的中國游客坐了半小時纜車終于晃晃悠悠到“云頂”,進了大堂,幾乎所有人都忍不住睜大眼睛輕輕地“哇!”地一聲——云頂的LOBBY是我去過所有酒店中最大的一個,大得似乎足夠搞一場室內足球賽;它的前臺也“漫長”得足夠幾十人同時站在那兒為客戶服務。 云頂在吉隆坡東北約50公里處,面積約4900公頃,是東南亞最大的高原避暑地。原名“珍丁高原”(Genting Highlands),由于山中云霧縹緲,令人有身在山中猶如置身云上的感受,故改為現名。 初進云頂時的驚嘆一直持續到上樓看住處:中空的天井式建筑,環繞一圈望過去全是密密麻麻房間,我拿到的鑰匙牌顯示,已是這一層的第一百多個房間,后看介紹才知這里一共有3000間客房,實在大得令人瞠目。以至于導游費了不少口舌告訴大家餐廳、賭場和房間的路線,以免迷路。晚上果然見到不少打聽路的中國人,方知導游之囑并非夸張。 許多中國人都是“新馬泰”之旅開始第一次出境游。按傳統線路,游客通常在馬來西亞停留三晚,除去馬六甲、吉隆坡之外,那一晚就給了云頂。在某大旅行社工作的常潤說,包括吃、住、行,馬來西亞方面這三天一共收取中國的接待費是每人30美元。這個價錢實在低得反常,但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賭場方面給的某種形式的補貼,目的不外乎一個:吸引更多的中國人來云頂。 “云頂”是在亞洲范圍內為數不多的、堪與澳門葡京賭場相提并論的賭場之一。而來云頂的一年前,恰好也曾去過葡京,感覺葡京多靠澳門賭博傳統及其多年的“江湖地位”取勝;而論及規模及氣勢,則略遜云頂。云頂集團的老板林梧桐1918年生于福建,20歲來馬來西亞謀生,是個木匠出身的建筑商。1965年,林梧桐在云頂高原興建酒店。1970年獲首相特許在酒店開辦賭場,到現在林梧桐在云頂共有6座大型星級賭場酒店。據1994年美國《福布斯》雜志統計,林氏的資產逾50億美元,而同期的澳門賭王何鴻只有19億美元。 云頂賭場似乎想營造“賭亦有道”的“尊嚴”。導游老早就提醒大家要正裝進入、男士還要加上領帶。像所有的賭場一樣,通過嚴格的安檢入內。賭場照例維持以大取勝的風格,一個房間套著一個房間,煙霧繚繞、人聲鼎沸。以前只在周潤發的“賭神”系列片中“領略”過賭場,這次親眼所見,很多賭臺上的人表情都一樣地緊張,像電影里演的一樣,拿到牌后緊貼著桌面微微抬起,僅個人能看清手中的牌。 云頂是馬來西亞惟一合法的賭場,門口的告示上說,雪蘭峨州和彭亨州的蘇丹告誡穆斯林教徒不準入內。觀光客如去賭場,要出示護照。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宗教人士反對開賭參賭,政府也對云頂高原賭場作了諸多限制:只許接待外國游客,禁止本國居民參賭,不允許在媒體做賭場廣告。 云頂其實更像是一個大的娛樂城,除了龐大的酒店外,還有花園游樂場、室內體育館及高爾夫球場等。云頂里的“云星劇場”也是華人巨星經常光臨之地。印象很深的是,從大堂到賭場要經過一個長長的扶梯上,抬眼全是港臺大明星的巨照,當時最醒目的就是情歌王子張信哲的演唱會。后來看到從老牌的羅文、張帝到陳慧嫻、BEYOND,直到新生代林志穎、謝霆峰都在這里開過演唱會。這種將賭博與其他娛樂業“打包”在一起的方式,或許也正是云頂的老謀深算之處。 在一個禁賭的國家開設賭場,云頂的目標客戶群顯然更是在亞洲范圍。賭場內絕大多數為黃皮膚、黑頭發的亞洲人,而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各種口音的漢語也不絕于耳。來這里賭的中國人也很多樣化:與我們同團來的來70多歲的老婦,玩老虎機一直到凌晨3點,直到女兒下來將她“挾持”回房;團里另一個單身旅行的老板模樣的中年男人,坦言就是來“賭”一把,第二天早上告知大家他輸了2000美元,但最讓他吃驚的是他親眼見到一個華人婦女一晚上不動聲色地輸掉了30萬港幣。- 杭州:城鎮化中的股份制賭博集團 農貿市場、竹林、茶室、偏遠石礦內,一塊地板、一張毛毯就能組成一個簡易的賭博窩點。2004年7月起,杭州市上泗郊外突現四大賭博集團。集團為股份制、賭場里實行星級服務,參賭人員出手動輒三四百萬元。 賭場老板靠放高利貸獲取巨額利潤,參賭人員皆為當地生意人和農民。許多賭客傾家蕩產,還欠下巨額高利貸。 上世紀90年代末期,杭州加快了郊區農村城鎮化步伐。許多農民在獲得了征地補償款后,開始做生意。幾年時間暴富,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錢包鼓起來了,空閑時間多了。這些“農轉非”的富人,業余文化娛樂生活卻沒有質的改變。賭博成了他們消磨時間、冒險積累更多資本的一種快捷方式。杭州的標本可以被看作中國境內暗流涌動的賭資需求的一種寫照 記者◎王家耀(發自杭州) 四大股份制賭博集團 “我被非法拘禁,快來救我!”2004年9月16日晚7時,杭州市西湖區龍塢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求救報警電話。該男子自稱被拘禁在龍塢鎮葛衙莊的一家理發店里。值班民警迅速趕往現場,將其成功解救,并當場抓獲犯罪嫌疑人俞豐、陳則虎、陸建忠3人。 龍塢派出所民警很快搞清了事情真相。這是一次因欠高利貸過期不還引起的拘禁事件。被拘禁男子姓楊,余杭人。楊某在龍塢一賭場賭博輸光了身上的錢后,在賭場里向俞豐等人借了5萬元高利貸,隨后再次輸光,無法償還。俞豐遂將其拘禁逼其還錢。民警審訊發現,俞豐等人背后是組織嚴密的大賭博集團。 至此,活躍在杭州市西湖區上泗地區的四大股份制豪賭集團浮出水面。 龍塢賭場:大股東黃金祥,開場次數56,單場最高抽頭金額86.8萬元。中村賭場:大股東鄭洪福、章冬山,開場次數60,單場最高抽頭金額82.2萬元。轉塘賭場:大股東來莉萍、陳長峰、周剛,開場次數3,單場最高抽頭金額3萬元。瓶窯賭場:大股東陳小根,開場次數40,單場最高抽頭金額20萬元。 杭州警方在新聞發布會上稱,盤踞在杭州上泗地區的四大賭場,涉賭人員120多人,賭場內流動資金最高時近千萬元,是浙江省近年來查處賭資最多、性質最為惡劣的賭博案件。 四大賭場均為股份制集團,組織嚴密,經營網絡健全,實行星級服務。參賭人員有專人聯絡、轉車接送;賭場外有人放哨、賭場內有“跑道員”負責送水遞煙,賭徒輸光了錢也不用擔心,賭場內有老板負責“拋資”(高利貸),借一萬元,最高日利息達到500元。 為了安全,賭場是經常流動的。因此其設施非常簡單。上泗郊外的農貿市場、竹林、茶室、偏遠石礦甚至甲魚塘內,只要一塊木板、一張毛毯,就能組成一個簡易的賭博窩點,有的干脆直接由鴨棚、豬棚改建而成。 賭場實施企業化管理,分工明確。大股東黃金祥負責召集賭博人員;胡朋、潘潮法等人接送賭徒和場外放哨;俞豐、陸建忠等人則輪流上場陪賭,他們的任務是“拋資”——給那些輸得一文不名的賭徒提供高利貸。為了防止參賭人員作假和起哄鬧事,黃金祥特意從江西請來練拳擊的陳則虎等兩人充當保鏢,又讓黃鴻洲管理“抽頭費”。按規定對進場賭博的坐莊人員上莊時抽取總金額的5%的費用;坐莊過程中,莊家每贏一萬元就抽取3%,下莊時若莊家贏了,每一萬元再抽取5%。大股東黃金祥平均一天的“抽頭費”在20萬~30萬元之間。 最賺錢的還是賭場內的“拋資”,賭場內的高利貸每一萬元每天要扣取500元利息費,賭場外的高利貸則在100~150元不等。一個“拋資”能在兩個月時間里,從10萬漲到80萬元。 大股東是賭場的幕后“主宰”,他們操縱著賭家的輸贏概率,也操縱著賭場資金的流向。賭徒們是很少贏錢的,他們沉浸在一輪輪充滿刺激又毫無希望的博弈中,最后被榨干了身上最后一分錢。 一批批賭客,很多是熟面孔,他們大多在30~40歲之間,其中多數人過一段時間就消失了。龍塢賭場大股東黃金祥說,在賭場里一次輸幾十萬元毫不稀奇,賭場里有很多人欠的高利貸一輩子都還不清了。 參賭之前,多數賭客都有豐厚的家資。陳小根開辦的賭場有一個特點,參賭人員必須具備百萬元以上的家底,而且必須要帶3萬元以上的賭資。因此,四大賭場的大股東手上都有一份名單,上面有上百名有背景的“老客戶”,這些“老客戶”不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生意人,就是傍著大款的富婆。 另外一個參與賭博的群體是當地一些暴富的農民。 賭博——暴富后的財富增值方式? “如果不是手中有了錢,又有了空閑時間,怎么會有人去賭博?”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政治處的章官翔警官分析說,杭州人歷來有“小搞搞”的愛好,本地盛產龍井茶,茶農們每年都有很可觀的收入。上世紀末期,杭州開始全面推進城市化發展,一大批郊區農民獲得了大批征地款,他們借這次機遇大富了起來。章官翔和政治處的葛警官認為,郊區大多數農民的年收入要三倍于杭州市公務員。至于生意人,章官翔笑稱:“他們的收入沒法說,或許幾百萬,或許上千萬,但只要老老實實做生意的,一般都有幾十萬以上。”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長期研究杭州農村問題的馮鋼教授向記者描述了那次城鎮化進程:當時主要是由村里集體和政府就土地討價,好多政府領導都是當地人,因此在征地款上大多不是很苛刻。多數“農轉非”的村民一下子拿到了十幾萬、二三十萬的征地款。村里將留的10%的開發地,統一建成市場,然后再分給村民,當作商鋪經營。“杭州城郊一下子冒出了幾千家飯店、茶樓、農貿市場、服裝市場。就這樣,祖祖輩輩的農民農轉非后一下子發了。” 這是杭州郊區農民掘到的第一桶金。離杭州市區不足20公里的典型江南小鎮——轉塘鎮,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月13日晚剛剛下過小雪,轉塘鎮地面濕漉漉的。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上許多積水。這個小鎮的房子多數是二層、三層樓,一些樓房甚至是歐式建筑。街道兩邊店鋪林立,靠近鎮政府的馬路旁邊停了幾百輛出租車。包圍著小鎮的是群山,半山坡上全是茶樹。轉塘鎮境內有之江國家旅游度假區和望江山療養院。 風景區建起來了,相關的配套設施足了,旅游的客人隨之多了起來。本就銷量很好的龍井茶一下子供不應求。轉塘鎮雙流村的老李告訴記者,清明前上市的龍井茶價格特別高,一斤茶葉賣到四五千元很平常。2004年,杭州曾出過四兩龍井茶葉賣到了500萬元的事情。即使是普通的龍井茶也要賣到四五百元一斤,而茶葉一年三季,搞好了,一年幾十萬元沒有問題。“守著龍井茶就不怕沒錢花。”如今老李雇人種茶,自己則經營茶莊。 農貿市場、服裝市場、茶樓也紅火起來了。轉塘鎮政府黨辦一名負責人稱,這些生意基本不用投資。很多杭州市區人或外地游客,來風景區吃農家飯,喝龍井茶,當地人都是當作客人招待,根本不用繳稅。客人臨走一般都要買一些龍井茶。當地的建筑業、房地產業也開始興旺。有生意頭腦的人購進了挖掘機做起了建筑生意。當地人介紹說,僅轉塘就有1000多臺挖掘機,一臺挖掘機價值50多萬元,一些大老板都有四五臺。在建的杭青(杭州——青島)高速路、郊區的別墅區都需要挖掘機,每年的收入相當可觀。 杭州得天獨厚的旅游文化生態資源和杭州的城鎮化戰略讓郊區的農民迅速暴富,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暴富之后,“空閑時間不‘小搞搞’,還能干什么?”記者在3天的采訪中,問及空閑時間的娛樂方式,接受采訪的“農轉非”村民、生意人說得最多的就是“小搞搞”。看電視、搓麻將、打牌是當地“農轉非”人的三大娛樂方式。 以前都是“小搞搞”(小賭),村頭街尾、集貿市場、茶葉市場,農民或生意人閑暇時,玩兩把,也就是幾百元,最多上千元。西湖區公安分局政治處章官翔警官說,近年來,郊區眾多人暴富,空閑時間多了,賭博市場大了。 西湖公安分局資料顯示,前幾年,該局每年處罰的賭博人員只有400余人次。到了2004年,該局查處的賭博治安案件多達700余起,被治安處罰的人數高達2300余人次,治安拘留600余人,勞動教養9人,被處罰者中,本地人占80%。 以前僅一年三季種、采、炒茶葉就忙得農民不亦樂乎,只是冬天有些時間“小搞搞”。可現在“農轉非”后的村民,雇人種、采、炒茶葉。杭州周邊郊區的茶農多數雇用了安徽、江西等地的打工者搞茶葉。本地人多數只照顧茶樓或市場的生意,這樣空閑時間就多起來。 農民和生意人富了起來,但其文化娛樂生活并沒有質的提高,只是在量上加大了。明顯的例子就是,不再滿足于往日的“小搞搞”,加大了賭注和參賭次數。以前是隨處“小搞搞”,現在則參與到股份制賭博集團“大搞搞”。 賭博吸引當地人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賭博可能讓他們手中的錢快速增值。記者調查發現,“農轉非”的村民和暴富的生意人,很少出入市里的高檔娛樂消費場所,他們一般叫不出這些場所的名字。當地人認為出入這些場所,錢白花了,而賭博則不同,賭博也是一種投資方式。 龍塢賭場的大股東黃金祥就是靠賭博發達的。黃金祥本是龍塢鎮農民,起初做茶葉生意,積攢了一點錢。茶葉淡季或平常空閑時,黃金祥就進出各賭場,一開始是“小搞搞”,2003年在“筒子功”賭博中贏了150多萬元,隨后黃金祥聯絡多人以股份制形式開辦賭場,隨后日進萬金。 正是抱著既能贏錢又能打發時間的心態,當地人前赴后繼地走進了賭場。針對日益嚴峻的賭博形式,浙江省決定今年1~5月全力開展禁賭專項活動。重點整治職業性豪賭、互聯網賭博、賭球、跨境賭博等。四大賭博集團于是被成功摧毀。 概率論:起源于賭博 ◎邢海洋 兩年前,我和清華大學數學系教師豐德軍做Roommate,那時,美國加州一名華裔婦女買彩票,中了頭獎,贏得8900萬美元獎金,創加州彩票歷史上個人得獎金額最高紀錄。消息傳播開來,很多人躍躍欲試。豐德軍的反應是典型的數學式的,他說,數學家不會買彩票,因為他們知道,在買彩票的路上被汽車撞死的概率遠高于中大獎的概率。 每年,全世界死于車禍的人數以數十萬計,中了上億美元大獎的卻沒幾個。這樣看,數學家的命題是正確的。按數學的語言,是“真”的。但死于車禍的人中,有多少是死在去買彩票的路上呢?這恐怕難以統計,因而“死于車禍多于中獎”也成了無法從當事人調查取證的猜想。在概率論里,“買彩票路上的車禍”和普通的車禍是完全不同意義的事件,是有條件的概率,這個概率是建立在“買彩票”和“出車禍”兩個概率上的概率。解法不知是否可通過兩個事件的概率的乘積求得。不管怎么說,這都應該是一個極小的概率,它的概率比中大獎的居然大,可見中大獎的難得和稀奇。 但買彩票的人卻比參與賭場賭博的人多得多,不能不說公眾缺乏對數字的理解。通常,賭場的賠率是80%甚至更高,而樂透彩的賠率還到不了一半,但公眾卻熱衷于彩票,渴望一夜暴富,一把改變命運。商家了解大眾心理,不在每件商品上打折,而是推出購物中大獎之類的活動,也和彩票異曲同工,既節約成本,又滿足了顧客的“僥幸”心理。理解了數字,你也就知道,中六合彩的概率遠比擲硬幣,連續出現10個正面的“可能性”小得多,手邊如果有硬幣,又有時間,你不妨試試,看你用多長時間能幸運地擲出自始至終的連續10個正面。連續10個正面的概率是10個1/2相乘的積,意味著每次拋擲,你都“幸運”地得到了你所希望的,占整個可能性1/2的好結果。這個概率應該是1/1024,想想吧,千分之一的概率讓你碰上了,難道不需要有上千次的辛勤拋擲做后盾? 賭博就是賭概率,概率的法則支配所發生的一切。以概率的觀點,就不會對賭博里的輸輸贏贏感興趣,因為無論每一次下注是輸是贏,都是隨機事件,背后靠的雖然是你個人的運氣。但作為一個賭客整體,概率卻站在賭場一邊。賭場靠一個大的賭客群,從中抽頭賺錢。而賭客,如果不停地賭下去,構成了一個大的賭博行為的基數,每一次隨機得到的輸贏就沒有了任何意義。在賭場電腦背后設計好的賠率面前,賭客每次下注,都沒有意義了。 概率里有一個重要的概念是事件的獨立性概念。很多情況下,人們因為前面已經有了大量的未中獎人群而去買彩票或參與到累計回報的游戲,殊不知,每個人的“運氣”都獨立于他人的“運氣”,并不因為前人沒有中獎你就多了中獎的機會。設想一下,前面10個人拋硬幣,沒有一個人拋出了正面,現在輪到了你,難道你拋出正面的可能性就大于其余的人?拋硬幣出現正反的決定性因素是硬幣的質地和你的手勁,每個人拋的那一次,都“獨立”于其余的人。拉斯維加斯的很多賭場,老虎機上都頂著跑車,下面寫著告示,告訴賭客已經有多少人玩了游戲,車還沒有送出,只要連得三個大獎,就能贏得跑車云云。但得大獎的規則并無變化,每人是否幸運,和前面的“鋪路石”毫無關系。 概率論滲透到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19世紀法國著名數學家拉普拉斯所說:“對于生活中的大部分,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只是概率問題。你可以說幾乎我們所掌握的所有知識都是不確定的,只有一小部分我們能確定地了解。甚至數學科學本身,歸納法、類推法和發現真理的首要手段都是建立在概率論的基礎之上。因此,整個人類知識系統是與這一理論相聯系的……”有趣的是,這樣一門被稱為“人類知識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數學卻直接地起源于人類貪婪的產物,賭博,文明一點的說法,就是機會性游戲,即靠運氣取勝的游戲。 希羅多德在他的巨著《歷史》中記錄到,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為了忘卻饑餓,經常聚集在一起擲骰子,游戲發展到后來,到了公園前1200年,有了立方體的骰子,6個面上刻上數字,和現代的賭博工具已經沒有了區別。但概率論的概念直到文藝復興后才出現,概率論出現如此遲緩,有人認為是人類的道德規范影響了對賭博的研究——既然賭博被視為不道德的,那么將機會性游戲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也就是大逆不道。第一個有意識地計算賭博勝算的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卡爾達諾,他幾乎每天賭博,并且由此堅信,一個人賭博不是為了錢,那么就沒有什么能夠彌補在賭博中耗去的時間。他計算了同時擲出兩個骰子,出現哪個數字的可能最多,結果發現是“7”。 17世紀,法國貴族德.梅勒在骰子賭博中,有急事必須中途停止賭博。雙方各出的30個金幣的賭資要靠對勝負的預測進行分配,但不知用什么樣的比例分配才算合理。德.梅勒寫信向當時法國的最具聲望的數學家帕斯卡請教。帕斯卡又和當時的另一位數學家費爾馬長期通信。于是,一個新的數學分支——概率論產生了。概率論從賭博的游戲開始,最終服務于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理財 > 商界精英 > 正文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