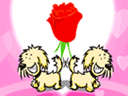|
葛紅兵的長篇新作《財道·富人向天堂》一問世,便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財道小說。
1990年代初期,王朔在北京說“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是金錢關系,最干凈的也是金錢關系”,當即遭到了痛罵,遭罵的原因不是他說的不對,而是說的時間不對。十多年過去了,葛紅兵在上海說“我要錢,我要過得富貴”,贏得了一片掌聲,畢竟這十多年來中國的
變化太快了。
從古至今,金錢與罪惡總是相伴相生的。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股市這樣一個資本高度密集的地方,無疑也是一個滋生罪惡的地方。《財道》中的富人認為,“錢就是男人的膽和魄”,“錢就是愛的能力,錢就是愛的工具”。怎么樣得到錢呢?小說中邢小麗有一句很精辟的話:“你想錢,就要做錢的孫子,要比錢更卑賤!”這樣,“卑鄙就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證”。為了錢,女人不惜出賣肉體;朋友不惜勾心斗角,分道揚鑣。因為錢,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簡化為了“利用,再利用”。
在中國這樣一個不規范的股市里,叢林原則一再上演:“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股市大鱷們翻云覆雨,日進斗金;而無數的散戶們則戰戰兢兢,他們的“錢放在股市上就像放在不上鎖的錢柜里”,小說中賣報的王阿姨用畢生積蓄買股票,結果股票大跌,欲哭無淚;這種小人物的遭遇是中國千萬股民炒股經歷的真實寫照,讀來令人感慨。顯然,《財道》是一本極具現實關懷的書,它提出了有關富人原罪、貧富差距等重大現實問題。
股市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從上世紀80年代的
雙軌制、到90年代國有企業改制、到今年房地產市場的跌宕起伏,有許多人像股市上的富豪一樣,一夜暴富,成為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
錢,這個貨幣符號成了欲望者心中的主神。小說主人公崔鈞毅就是因為沒有錢,被岳丈趕出了故鄉三余,在上海備受歧視。而大航集團的老總周重天,對錢頂禮膜拜,為了挽救自己的股票,不惜把女婿逼到絕路;為防止情人邢小麗分享財產,不顧她有孕在身而斷然與之分手。如果說周重天是中國的葛朗臺的話,那么,小說中崔鈞毅以“義”為中心的財道思想,老范以“舍”為中心的財道思想,武瓊斯以“取”為中心的財道思想則展示了時下國人不同的財富理念。其價值取向自有褒貶,但無論哪種行為,都是為了完成自我的救贖,得到靈魂的安息,最終獲得走向天堂的入場券。
然而,天堂真的是向富人敞開的嗎?財富的追逐者們呼吸到了幸福的空氣嗎?小說的結局給出了一個否命的回答,就像絕大多數以尋寶為主題模式的武俠小說的結局那樣,是一個空無。崔鈞毅從窮人變成了大富翁,卻沒有獲得預期的幸福,失去了朋友(黃平自殺),失去了愛人(邢小麗最后接納的是別人),失去了英俊和健康(被毀容)。經過這場劫難,崔鈞毅浮躁和騷動的心平靜下來,攜手張梅隱居他鄉,實現了喬峰和阿朱的宿愿。
崔鈞毅的身上有《紅與黑》中于連的影子,他們均出身草根,為改變命運而負重向上,但這種向上都具有不穩定性和破壞性,他們的人格基調是中性、甚至灰色的。命運給于連開的玩笑,是將他送上斷頭臺,而給崔鈞毅開的玩笑,是以身體的傷殘為代價,換取了財富上的輝煌。
范建華是《財道》中最傳奇的人物。如果按圖索驥,無論崔鈞毅、武瓊斯、邢小麗還是周重天,在現實中都隱約可覓,惟獨范建華,他在鬧市中賣盒飯,在崔鈞毅接管黃浦證券后出山,看
到崔鈞毅輝煌背后的隱患時,毅然激流勇退,這種對財富超脫于物外的態度,頗有老莊之風,也是直面財富時惟一的清醒者。這種清醒,是對人性深處的巨大欲望保持警惕。正如他對崔鈞毅說的,“我是認命和躲命,你是不認命,挑戰命運的啊!”我相信,作者精心描述的一個并不存在的范建華,其實代表著世人面對財富時的不知所措。
我們對金錢的態度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幼稚的,突如其來的金錢,并沒給生活帶來幸福,而是多舛的命運。在金錢面前,人性已經被剝光了最后一塊遮羞布,尊嚴已蕩然無存。在財富面前保持人性的尊嚴,是《財道》留下的巨大懸念,也是掩卷沉思的重要命題。
“茍富貴,勿相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其實中國人很早就對富貴有清晰的認識和追求,只是后來的文人越發的扭捏作態,心里想錢想得發瘋,口中卻把仁義道德、革命理想掛在嘴上,念念不忘。
葛紅兵想來是參透了人的自私的本性,看穿了人虛偽的外衣。在《財道》篇首,即借崔鈞毅之口道出“我要錢,我要過得富貴”,那個差點成為他岳父的老人給了他一耳光。想必這一耳光非常響亮,把人們從各式的發財夢中驚
醒,原來還可以這樣直白地表達理想啊?
崔鈞毅無疑是個理想人物:他拼命掙錢不是為個人享受,而是為了成就感、尊嚴感,為了回報親友,從未喪失自己的道德底線,而且單憑細膩的味覺和嗅覺就能識人,其實是一種見微知著的靈氣或悟性。崔鈞毅之所以沒有重蹈武瓊斯和周重天的覆轍,就是因為他始終葆有一顆敞開的善良之心。
上海是個海。一片財富、商機、資本、金融涌動的汪洋大海。自開埠以來,無數職業經理人、投資者、冒險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劇便不斷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綜觀二十世紀的上海文學史,除了茅盾的《子夜》運用社會分析的手法開創了民族工商業題材小說的先河,其他如“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或者張愛玲、蘇青等人的創作,或者沉溺于勾欄瓦肆等消費場所的風月描寫,或者取材于家庭日常倫理的沖突,而對于宏觀的資本和金融世界來說,“海派”文學相對是失語的。上世紀90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畢飛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舊上海為背景,對個體人物的歷史命運進行深層開掘,但作品缺乏對當下時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發覺了海派文學的這種缺失,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全景式地描繪商業開放時代,但因為缺乏成功的人性刻畫,也很快趨向沉沒。但是對于小說家,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小說家來說,能否對當下生活發言、能否揭開生活表象背后的人生密碼,或者說揭示出當下都市生存的內在精神,又是衡量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從這種意義上說,葛紅兵的小說《財道·富人向天堂》以一個蘇北青年在上海證券業的迅速崛起為視點,將
個人的成長與中國當代證券、金融業的整體面貌加以整合表現,正是試圖開掘出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新一代財富創造者的生存圖景和當下時代內在的精神品質。(10H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