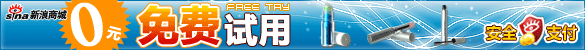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
末代學徒的無奈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9日 02:40 第一財經日報
本報攝影記者/楊彥如今瓷器造假不僅技術越來越高,手法多種多樣,更有甚者自己出書,把假的寫成真的蒙騙大眾。據徐國喜透露,這類造假者出書的數量能達到所有瓷器類書籍的30%到40%之多。因此他建議藏家購買古玩瓷器的時候,還是要認準名望較高的文物商店,并且找一兩位行家幫忙把關。 一副厚重的粗框眼鏡和一把小型帶燈放大鏡是古玩鑒定家徐國喜的標志。每每有人拿來一件瓷器或玉器請他鑒定,徐國喜總是不緊不慢地把放大鏡貼到他厚厚的眼鏡片前,再湊近到器物周身游走一遍,就有了結論。通常在這之后,徐國喜還會意猶未盡地在一些細部上再多看幾眼。鑒定這個過程,徐國喜非常享受。這也是為什么他現在64歲、生活寬裕,卻還整日往外跑,給人上課,幫人鑒定。 從18歲進入古玩商店拜師學藝,到60歲從上海友誼商店退休,徐國喜浸淫古玩行業42年,可算是民間古玩鑒定界的前輩級人物。 在他眼中,古玩鑒定家一要見得多,二要記憶好。徐國喜見過“文革”前滬上眾多大收藏家珍藏的近萬件瓷器古玩珍品,尤其對一些罕見的精品過目不忘。他的腦袋猶如一個大型資料庫,任何一件東西到他手里,只要與資料庫中的真品一比對,真假好壞就一目了然了。 “末代學徒” 全國最懂古玩的人集中在四個地方:北京、南京、沈陽和上海。前三者都是古都,皇城根兒里好東西多,自然懂行的人也多。而“文革”前,上海是資本家、企業家、藝術家的聚居地,這些人通常也是大收藏家。 徐國喜外祖母的娘家也是當時上海灘上頗有地位的人家。兒時的徐國喜去舅公家玩耍,常常流連于他家里數不清的古玩瓷器。后來,長大一點的徐國喜跟著父親到淮海路上班。坐在有軌電車上,徐國喜一路數著淮海路上“幾十家首飾店,十幾家古玩店”。那里,成了他的樂園。巧的是,18歲中專畢業后,徐國喜竟然被分配到其中一家“新龍古玩店”工作。這令徐國喜欣喜萬分。 1962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古玩店實際上已經收歸國有,然而由于“新龍古玩店”是世代相傳的老字號,因此牌子和原來的私方經理都留了下來,古玩行當的學徒制也保留了下來,只是國家又給店里配了一位公方經理,子承父業的傳統也一并打破了。于是原來的老板袁昌泰便把剛剛收下的這位小徒弟當作自己兒子一樣教導,希望他能繼承自己的事業。從此以后,徐國喜每天吃在店里、住在店里,算是搭上了學徒制的末班車。 僅僅過了一年多,“新龍古玩店”就正式并入了國家文物商店,徐國喜和袁昌泰的師徒緣分也告一段落。然而徐國喜在這一年里學到的東西,卻是其他經歷都無法比擬的。 徐國喜說:“當時古玩商店里東西比較少,好東西都在大藏家手里,我師父就對我說,你要看到好的東西,必須到大的收藏家家里去。”袁昌泰祖上世代經營古玩店,上海的古玩收藏大家,如蓋叫天、薛貴笙等,幾乎都是他的故交。于是袁昌泰就帶著徐國喜一家一家地拜訪,藏家們買袁昌泰的面子,都給予了熱情的招待。 徐國喜還記得第一次拜訪的是京劇名角蓋叫天在東湖路上的大洋房。當時蓋叫天正在庭院里翻跟斗。袁昌泰跟他說明來意后,蓋叫天很爽快地對徐國喜說:“你盡管看,就是要小心不要打碎,你不懂可以問我,還可以請你先生講給你聽。” 于是師徒二人如同逛博物館一樣,師父邊走邊講,徐國喜則邊看邊記。“蓋叫天家有兩三間大房間專門用來放古玩。打開門四周都是古玩,地上也都擺滿,瓷器少說也有幾千件。”師父指著其中一尊明朝瓷器大家何朝宗所制的白釉達摩像說:“這是明朝德化窯珍品,而且又是大家之作,你要仔細地看,認真地記住它的特征,包括它的釉、胎、造型和面相,以后你看到假的,就會發現不一樣。” 徐國喜端詳這尊達摩像。只見其釉色呈象牙白,滋潤肥厚,此釉色在建窯中是屬于最上乘的。達摩面相自然、慈善,非常富態。衣著飄帶瀟灑自如,線條簡單而不繁復。佛像背后有“何朝宗”三字葫蘆型的落款。整尊佛像的胎質厚、胎色白中透紅。乃是一件明朝珍品之作。 徐國喜仔細記住了這些細節,晚上回到店里還興奮得睡不著覺,于是他把當天所見、所學一一回顧了一遍。就這樣,一年下來,徐國喜不僅見到了別人都見不到的好東西,而且上手的瓷器數量達到近萬件之多。尤其是對較為珍貴的瓷器他都深深地印在腦海中,至今難以忘懷。 “文革”后,當時這些大藏家的藏品紛紛流散到各處,有的到了國外,有的進入博物館。如今已很難再找到藏品數量如此之大的私人收藏家,而像何朝宗達摩像這樣的瓷器珍品也已經非常罕見。隨著時間的流逝,如同這些藏品一樣,藏在徐國喜腦中的這本瓷器檔案也愈發顯得珍貴。 耿直的鑒定師 近幾年來,徐國喜在市場上常常見到何朝宗的仿品。有一天早上,他在城隍廟福佑路小商品市場的“鬼市”里就看到了一尊仿何朝宗觀音像。徐國喜一看,這尊觀音不僅神態不自然,而且胎質、釉色都明顯存在問題。“它的釉色偏青,而不是象牙白。從這一點就能看出它是后仿的。明朝是沒有這種偏青的釉色的。” 像這樣的仿品在徐國喜眼里只算是低層次的仿品。如今瓷器造假不僅技術越來越高,手法多種多樣,更有甚者自己出書,把假的寫成真的蒙騙大眾。據徐國喜透露,這類造假者出書的數量能達到所有瓷器類書籍的30%到40%之多。因此他建議藏家購買古玩瓷器的時候,還是要認準名望較高的文物商店,并且找一兩位行家幫忙把關。 徐國喜見過很多藏家,在瓷器上投資了數百萬元,請他過去一看卻發現全是贗品。遇到這種情況,其他鑒定師往往會礙于情面不點破實情,而是委婉地說“這件東西你可以自己玩玩”。但是徐國喜卻總是直言不諱。“你不相信,我們可以保留意見,但是你要我說它是真品,我絕對做不到。” 5年前,一位藏家從市場上買來一件明宣德青花纏枝蓮大盆,請徐國喜幫忙看鑒定。徐國喜仔細一看發現原來是一件高仿。它的造型、紋飾幾乎和真品相差無幾。但是它的青料卻露出了破綻。 明朝的青料都是進口自伊朗,分蘇泥勃青和烏蘇里青兩種。這兩種青料都含有氧化鐵的成分。所以如果是真品,燒制以后,氧化鐵會均勻自然地分布于釉下,呈深黑色,并且在邊角處略帶淺咖啡色。但是后仿品所使用的青料本身不含有氧化鐵。造假者也注意到了這點,于是在用青料繪好紋飾后,另外又補上了少許氧化鐵。這樣色彩是到位了,但是卻有一個無法彌補的破綻。由于這層后加的氧化鐵在瓷器表面上形成了突起,因此上釉后釉彩會順勢淌下。于是最后的成品中,氧化鐵全部暴露于釉上。 這位藏家買來的纏枝蓮大盆,正是這種情況。藏家原以為自己買來一件珍品,還滿心期待著徐國喜的認同,不想等來的卻是徐國喜的這番評價。他心里當然十分不快,于是又請來了其他專家鑒定,結果還是同樣的結論,才不得已接受了這個事實。 古玩價格的“操盤手” 深究古玩造假的背后,無非是一路攀升的市場價格在誘惑著造假者。而價格上漲背后的一連串因素,徐國喜最為清楚。 1965年,年僅21歲的徐國喜晉升為上海文物商店的部門主任;1970年,在古玩一律被貼上了“四舊”的標簽不允許在國內經營的情況下,徐國喜又來到專營出口的友誼商店出任古玩部經理,繼續經營古玩。 這兩個商店坐擁上海當時最大的兩個古玩倉庫。曾經領導過這樣兩個“大倉庫”的徐國喜,幾乎成為了古玩市場價格的“操盤手”。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幾乎每年都在抬高瓷器定價。”徐國喜回憶道。此后古玩市場經歷了兩次大幅度漲價。1985年左右由于大量港臺地區古玩商人打通了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通道,于是古玩價格有了一次飛躍;而上世紀90年代初,內地拍賣市場形成后,又掀起了新一輪漲價風。 然而在徐國喜看來,無論是這兩件事情本身,還是如今支撐著瓷器價格保持高位不跌的原因,追根究底還是庫存越來越少。 “現在東西是賣一件少一件。比如說,一件瓷器原來賣100元,下一個人來買就是150元,這件賣掉以后,再下一個人來買就是200元,再下一個人來買就是300元。到2003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感到情況非常危急了。因為我們自己的庫存已經很枯竭了,到外面也買不到好東西了。人家到我們店里來要好東西,我們嘴上都說有,但是心里知道倉庫里已經拿不出貨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徐國喜加價的幅度也一年比一年大。 1964年,徐國喜從當時急于離開上海的德國商人施德志手中收得了一批仿古月軒的琺瑯彩。施德志是一個“中國通”,尤其喜愛中國瓷器。于是他在民國早期,專門請來清宮里制作琺瑯彩的原班人馬定制了這批瓷器,并制成圖錄出售。因此這批琺瑯彩雖是仿品,但仍然非常名貴。 當時這樣一只仿古月軒的琺瑯彩鼻煙壺,價格只有1000多元。徐國喜不舍得賣,就把這批琺瑯彩一直保存在倉庫中,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逐步上柜。“那個時候一個鼻煙壺能夠賣到2萬元已經很高了,”徐國喜說,“但是1992年的時候我就加到了4萬元,6年前又加到了5萬元一個。” 前幾年,一位阿聯酋王儲來到友誼商店,看中了其中一只琺瑯彩花瓶。上世紀80年代,這只花瓶標價只有20萬元,但是現在的價格已經達到了500萬元人民幣。連王儲都喊貴,還價到300萬元不成,最后只能失望而歸。 如今,賣了40多年古玩的徐國喜終于可以“解甲歸田”自己搞收藏了。然而看著被自己“一手抬高”的古玩價格,徐國喜卻倍感無力。 當初看著大藏家家中和古玩商店倉庫里琳瑯滿目的好東西時,徐國喜不止一次夢想過有一天自己也能擁有一件頂級藏品。然而近幾年他陸陸續續積累下來200多件藏品中,沒有一件可以令他滿意。于是徐國喜始終帶著他的放大鏡,四處幫人鑒定,只希望能夠看一眼真正的好東西也好,可惜如今連這都難了。 呂寧
【 新浪財經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