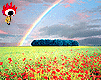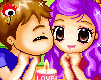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
書信或曰書札,其實是一種藝術。西方人稱它是“最溫柔的藝術”,言其親切細膩有類于日記。溫柔與否當不盡然,但名之以藝術卻毋庸置疑,尤其是中國舊時毛筆書札。究其原因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由其內容特性所決定;二是由其制作形式使然。
就內容而言。揚雄《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劉勰《文心雕龍》曰:“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
。”書札乃人際交流,直抒衷腸胸臆之作。性情所至,信手為之,娓娓如訴。不必矯飾造作,毋恐天譴人責。“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文明從容”(《文心雕龍》),酬獻心聲,或激越,或溫柔,或志高文偉,或詞采翩翩。諸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東方朔《難公孫弘書》、揚雄《答劉歆書》、嵇康《與山濤絕交書》等,均可謂千古絕唱。是書札之藝術性決不減其他文學體裁,甚至超而軼之。
就其形式而言。陸機《文賦》曰:“函綿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劉勰《文心雕龍》曰:“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其“尺素(帛)”或“簡牘”蓋我國紙發明之前的主要文字載體。我們知道中國漢字的書寫載冊是由筆、墨和書寫材料共同完成的。筆即毛筆,墨乃炭墨,自古一以貫之。書寫材料則先帛后紙,判然有別。紙的出現、普及并最終取代簡帛作為書寫材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其意義除導致漢字使用和文化傳播效率大大提高之外,還有重要而特殊的一項,就是使漢字的日常書寫脫離其實用性而升華為一種藝術成為可能。因為只有紙,嚴格說來只有中國紙,才可能使毛筆的性能發揮到極致,才可能真正做到“筆筆還其本分”,使藏出、曲直、起伏、濃淡、枯潤、薄厚、遲速、收放諸如此類書法藝術的基本規則或法術真正得以實現。于是乎,魏晉以降文人墨客便自覺不自覺地“寓性情、襟度、風格”于筆墨詞文之中,似乎于不經意之中創造出了極其賞心悅目的韻致,由之大大增強了其筆下,包括書札在內的文字作品的形式感染力和藝術性。而其審美價值有的并不亞于甚至高于條幅、中堂、對聯之類刻意為之的書法作品,有的則被人直視為書法藝術佳作,成為書法創作的永恒范式和不祧法本。
如魏晉士人尤其二王手札,其無論大王之《平安》、《何如》、《奉桔》、《快雪時晴》;還是小王之《鴨頭丸》、《地黃湯》、《中秋》、《豹奴》,無不神采飛揚,輝文含質,筆墨相得,天機自動,“爽爽有一種風氣”,其內容似乎已變得不太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了。
《顏氏家訓.雜藝》記載南北朝時流傳一個諺語,曰:“尺牘書疏,千里面目。”書札,古時稱尺牘,作為人際間不拘異時異地,傳情達意,進行社會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相知相識如同面語。可見其必為人類文明發展到相當高度的產物。其產生之條件,我以為起碼有二端,其一是物質的,即書寫工具和書寫材料的出現及初步發展;其二是精神的,即人文的覺醒。后者當更為重要。
書札分公私二種,《文心雕龍》首次有所區別,劉勰在公牘歸之于《奏啟》、《章表》之屬,私札則歸于《書記》一節。公文書札產生較早。文字產生,“絕地天通”,步入文明社會之后即可能出現,《尚書》實已見其端倪。《詩.小雅.出車》:“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講西周大臣南仲率師討伐凱旋,歸心似箭,途中擔心周王再下告急文書。此“簡書”即指周王下發的軍書,這是最早而明確的書札記載。私人書札產生較晚,當始于春秋。其間禮崩樂壞,“智識下逮”,人文大覺醒,社會交往從此日以擴大和頻繁,于是知識分子之間書信交通勢在必然。《左傳》中《昭公六年》載“巫臣自晉遺書責子反”,《襄公二十四年》載“叔向使詒子產書”,《文公十七年》載“鄭子家為書與趙宣子”,《成公七年》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范宣子”等即是明證。于異國異域,士人之間“其辭皆若對面(《文心雕龍.書記》)”,這在生產力相對落后,交通不便,特別是神權主宰,“學在官府”的歷史階段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說上揭《左傳》所載仍屬政治性人際交往書札,或所謂“行人挈辭”之類,難稱“抑揚乎寸心(《文心雕龍》)”,其溫柔的私密性尚不凸顯的話,那么戰國以降,情況則大大改觀了。1976年初湖北云夢睡虎地四號秦墓兩通木牘家書的發現,則提供了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家書實物。二簡均是用毛筆蘸墨寫于長23.1厘米(正合漢尺一尺)的木版上,內容是向家人敘述從軍征戰情況,并向母親索要衣物和錢。到了漢代,我國郵驛體系和封泥簽發制度基本建立,人際書信交往與日俱增。同時,書札的基本形制,即長度以一尺為限,也大致確定,這就是后世稱書札為“尺牘”的由來。上揭司馬遷、東方朔、揚雄諸札及楊惲《報孫會宗書》,馬援《誡兄子嚴敦書》,孔融《與曹操論酒書》等等均是此間出現,并傳誦至今的書札范本。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大分化、大變革時期,屬之“亂世”,是突出的多國多君時代。其間政治昏暗,戰爭頻仍,民生凋蔽,“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宗白華語)。”于是人文精神大發育,思想和學術大開放,儒、道、釋相互滲透影響,終于釀成比戰國百家爭鳴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玄學哲學誕生了,建安文學和抒情詩出現了,陶淵明的田園文學、謝靈運的山水詩、顧愷之的畫、王羲之的書法都先后在此間放射出奇異的光彩。于是魏晉文人墨客極盡風騷文雅之能事,創作出大量風情瀟灑、天資自然、清通簡暢的書札精品。
當年梁實秋先生曾寫過一篇小品文,名《信》。其中講:“我國尺牘,尤多精粹之作。”何以為精粹之作呢?我認為非名人書札莫屬。道理很簡單,舊時名人之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行,或有名緒、名業。必有超常之智慧、超常之能力、超常之才藝、超常之生活,更重要的是必有超常的素質,而非如現下某些名人或由外力使然。因此名人間用于社會交流的書札必然多精粹者,較一般書札必然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也更有藝術性。諸如李斯、司馬遷、賈誼、東方朔、揚雄等秦漢名流書札;諸如上揭魏晉名士書札;諸如唐宋八大家、蘇門六君子、竟陵、桐城諸派以至南社社員等歷代顯達的書札之作,無不名實相得。
前幾日,我收到一部書稿,題為《名人信札的收藏與鑒賞》,是北京大學程道德教授和全國總工會方繼孝先生從他們多年之書札藏品中遴選的精品結集。共收入自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近100多年間的社會各界名人的115件名札。從洋務運動魁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到戊戌維新領袖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從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王國維、疑古派史學大師顧頡剛,到大學者、思想家章炳麟、嚴復;從大教育家蔡元培、胡適、馬寅初,到文學巨匠魯迅、郭沫若、巴金;從書法大家張裕釗、沈尹默、于右任,到大畫家齊白石、徐悲鴻、劉海粟,以至科學家翁文灝、丁文江、李四光,均赫然名流顯士。可謂五彩繽紛,九流鱗萃。其書則功力老到,或行或草,或柔或剛,或碑版,或館閣,或宗法鐘王,或自出機抒,皆真率本分,天機自動。信由情性所致,全自蘊藉中來。是書家自不同凡響,不以書家名者亦不弱于書家。洵乃琳瑯滿目,洋洋大觀。
名人書札的收藏同其他藝術品,尤其古文物收藏一樣,無疑要以欣賞和鑒定作為基礎。欣賞是第一位,即首要的是對書札有感覺、有興趣,必須樂于親近、了解它,愿意與之交朋友,作知音,而最終達到與之心靈溝通,情感交融。因為古人書札與古文物一樣,本身是有思想、有生命的。它凝聚著作者的情感和智慧,或者說,它是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而所謂贗品則為他人比著葫蘆畫瓢制作而成,是以賺錢為惟一目的。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真情感,不可能有真韻味,章法亦必支離而斷氣,結字必呆板如木雞,總之勢必會暴露出某種匠氣、傻氣或火氣。
其次才是鑒定。鑒定是一種專門而古老的學問,是文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大抵從文物造假出現之日就產生了。孫過庭《書譜》云:“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于耳目也。”這里揭示了藝術鑒賞的一個通理,即必須首先要“玄鑒精通”。通俗一點,即必須要懂。而要懂,要“玄鑒精通”,我以為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要有相當的藝術審美能力和文化素養;其二是要有一定的真切感受或實踐經驗。然后則需要了解三方面的問題:了解所鑒定對象的意,了解所鑒定對象的技術,了解所鑒定對象的歷史。說到底,也就是要明了古人所謂“道、器和通變”。所謂道,即意義、規律或法則;所謂器,即技術、工具等;所謂變通。即演變的歷史。對于書札而言,就是要充分了解其性質、功用、意義、文化價值和材質、制作方式、形制特點以及歷史演變、時代特征等,這是書札鑒定不可或缺的基本功。這是其一。
其二,書札鑒定同其他文物鑒定一樣需要有參照系。與玉器、青銅器、瓷器等文物鑒定須以考古學文化材料為參照物不同,書札以及書畫、古籍、碑帖拓本之屬的參照系則是真實可靠、流傳有緒的傳世品。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去接觸、熟悉和研究傳世書札原件,要從內容到形式全方位地考察。其中最主要的是了解該作者的文筆風格特征,尤其是書法用筆特點。如果說我們前面所論乃是近代書札產生和存在的時代背景和總的時代風格特征,此乃書札鑒定的基點。那么文筆風格和書法用筆特點則屬于個性,而個性乃是藝術品鑒定的主要依據———藝術風格之三要素中的核心所在,或曰鑒定之主要法門。所以文筆風格,尤其是書法用筆特點才是書札鑒定的根本的和最后的依據。因為風格即人格,書札鑒定一如人品鑒賞,只有熟悉了解了某人,才能正確地認識鑒賞他。而此種熟悉只能從根本上,通過個性把握來實現。另外書札所用紙張的鑒別也要通過與參照物的比對來進行。如果紙確為當時產品無疑,那則需要特別對墨色做認真的考察。這也是書札鑒定的重要方面。
其三,要有一個好的心態。一是不要有任何僥幸心理,不要做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今如此浮躁,如此急功近利的社會現實下,唯利是圖之輩無所顧忌,無所不能,古董要什么就有什么,書札要誰則作誰,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警惕,最好隨遇而安。二是不過于自信,隔行如隔山。考古與文物研究是相當專業的學問,造假售假也是很專業化的行當。我經常看到一些高知、教授上當,其原因主要就是過于自信;我也經常看到一些大款、企業家上當,主要原因還是自信。
最后我們要說,收藏貴在成之體系。只紙片札,古今東西,云鱗霧爪,星散支離,充其量只是吉光片羽。倘若限定某一特定時段,聚焦某一專題,刻意收羅,日積月累,假以時日,則勢必會成就一個羽翼豐滿的收藏序列或體系,其價值自然非斷金碎玉可比。(張辛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