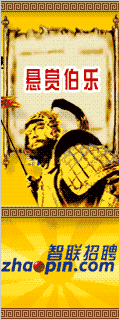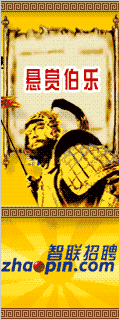|
元瓷足底是否有釉有款?
□ 文/張 英
自《文物》雜志1994年第2期發表筆者關于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至正年制”款釉上牡丹花卉紋五彩瓷碗(見圖1至圖3)的研究報告后,近十年來在全國各刊物上,不斷看到有
持異者。如江西曹淦源和歐陽世彬、廣西李鏵、北京呂成龍、香港葛師科等先生們提出“元瓷足底澀胎無釉,因為足底無釉,自然也不會書寫款識”的看法。筆者以為,這種觀點原出民國年間古玩商眼學對元瓷的一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這在現代考古學中是絕對找不到任何根據的。用眼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古代陶瓷的歷史,不能說它是科學的。
“元瓷足底澀胎無釉”一說,如今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并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這種提法最早出于民國初年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款識第六章,文中謂:“元瓷款識惟官窯有‘樞府’二字,其余民窯底有字者甚少,縱有字亦不掛釉,在器物底隨意成,若可識不可識之間,成花紋及轆轤形者亦間有之”。1942年北京古玩商趙汝珍先生著的《古玩指南》一書中,對許氏元瓷足底無釉之一說,一字無誤原樣收入書中且有發揮。在許氏一說中又補入“絕無以年號為款字者”一句。許氏是位文人,民國初年曾任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是研究曲學和中國音樂史的學者,業余嗜好古瓷;趙氏1937年于北京琉璃廠開設萃珍齋。他們所謂的元瓷足底無釉之一說,又未必是指元青花和五彩,因斯時舉國上下還沒有一個人承認元代還能燒制青花和五彩者,另外又屬一家之談,我們當無可非議。解放后,因為我國文博系統工作尚屬起步,許多琉璃廠人猶如陳重遠先生在《收藏》雜志著文:“新中國成立后,琉璃廠古董商中有‘真才實學者’,被國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各地方博物館聘為顧問、副館長或分配在文物鑒定組工作有數十人之多。1986年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成立,吸收了20多位出身琉璃廠古玩鋪學徒的老行家參加,并被選為常委和委員,……陶瓷鑒定專家,人們稱他們是‘國寶’人物。”正因如此歷史背景,許多傳統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文博隊伍。特別是《文物》雜志在1965年第11期和1966年第3期上,先后連續發表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孫瀛洲先生撰寫的《元明清瓷器鑒定》一文,這篇文章影響學瓷者最深,文中謂:“元代瓷器帶款識的極為少見,除青釉盤中印著‘樞府’或‘太禧’款的以外,一般青花、釉里紅器物均無正規款識”;又說:“大致說來,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釉而質粗”。孫瀛洲先生談元瓷之此說,基本是許之衡《飲流齋說瓷》和趙汝珍《古玩指南》的翻版,且又有所發揮。自此以后截至今天,便成了定論,再不見有人論述元瓷足底澀胎無釉及款識方面的文章,更無一人懷疑許、李、孫氏三位先生關于元瓷的這一說法,有無文獻,考古資料方面的佐證,致使元瓷足底澀胎無釉無款的一說,令許多文物和古玩界學瓷者奉之為“圭皋”,深信不疑,其說勢力之大,無人敢與之抗衡,甚至還有人為此說絞盡腦汁進行鋪墊。筆者以為用這種莫須有的理論來研究中國陶瓷史,不能說它是科學的。
應當說元瓷特別是青花和五彩瓷器的底足有的是施釉,有的是不施釉的,不可一概而論。從考古資料上看,施釉者,除吉林扶余岱吉屯墓出土釉上牡丹花卉紋五彩瓷碗,足底施釉并書有礬紅“至正年制”款識和同出的五彩“福”字款瓷碗(見圖4和圖5)可作佐證外,1964年保定市發現一處元代窯藏,出土有六件青花瓷器,其中有的砂底,有的滿釉,如青花釉里紅蓋罐、青花八棱梅瓶均是砂底,而青花八棱玉壺春瓶和(八棱)執壺則是滿釉,足端露胎。另外我們還從1978年以來,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清理珠山底下堆積中,出土的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龍紋碗盤和高足杯進一步得到了證明,元瓷足底有的是施釉的且有款識。今日從考古學說,瓷器上凡書、印八思巴字者,均已為古陶瓷研究者斷作是元代的產品。諸如1956年至1961年浙江龍泉大窖、安仁口、麗水寶定窯址出土的瓷器有八思巴字;廣東南海窯瓷器上發現有圖章款的八思巴字;60年代末北京德勝門豁口窖藏中發現的兩件景德鎮影青碗底部用墨書一個八思巴字,譯成漢字為張或章;山東淄博窖藏出土4件鈞窯月白釉淺腹盤的圈足內墨書八思巴字,也應為姓氏等。
綜上所述,元代青花和五彩瓷器的足底并不是都不施釉的。所以舉一反三,即使發現元瓷足底寫有‘福’字款、“長命富貴”款也就無須自驚自怪了。其實在元代的中晚期有些青花和五彩瓷器,足底施釉的工藝技術十分簡單,如圓器的盤碗,只要采用正燒的方法,燒前平切并斜削足底,防止坐在大于圈足之上的墊餅相互粘連,也就完成足底施釉的工序。所以說元瓷足底施釉或澀胎,并不能以此作為判斷元瓷的依據,更不能用老師的“亂說”,作自已研究元瓷的理論基礎,否則會出一些笑話。
景德鎮珠山至今未發現元青花瓷堆積地層的主要原因
據筆者所知景德鎮原始元、明、清三代官、民窯燒制青花瓷器的中心,可是至今景德鎮那里連一個元代青花瓷器堆積的地層都沒有發現,另外還有許多有關元瓷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又從哪里得來大量元代資料呢?
其實,解放以后,全國各地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方面的實物資料十分匱乏。我們一些同志對它的研究至今基本仍是步外國人的后塵,霧里看花沒有什么新的發展。景德鎮珠山原是元代御窯的故址,所以許多人都企盼若是在那里發現元代堆積的地層,哪怕是一個灰坑,那無疑將是對元代及其以后青花瓷器,諸如類比、斷代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遺憾的是解放以后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解決。一般地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元代中晚期,景德鎮珠山御窯廠已經大量燒制青花瓷器供作宮廷日用的器皿,許多殘次品的遺留,肯定會在珠山地下有大量的存在。筆者以為有許多跡象表明,假若不是我們走入誤區,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仍按傳統觀念視為明代中晚期產品的話,在珠山那里是絕不可能不發現元代御窯廠所遺留的青花瓷器的。
中國對元代青花瓷器的發現和研究很晚,及至解放后50年代,中國還沒有一個人承認元代還能燒制青花瓷器,古玩商成了“專家”,這是一個不可爭的事實。若論元瓷,猶如1942年北京古玩商趙汝珍著《古玩指南》書中所說:“元代以蒙古入主中華,不重文藝,且享國不及百年,完全渡征剿生活,無暇于享樂事業,故元代瓷業無特殊進展,……元器多仿鈞窯”,又說:“元代官瓷最少,其器有青器、白器、印花、劃花、雕花等,進御之器亦甚精妙,器內均燒印有‘樞府’字號。”趙氏卻不知元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發展時期,不僅有天文學家郭守敬、農學家王禎、女紡織技術家黃道婆、水利家賈魯,還有文學家關漢卿等,假若沒有當時農業、紡織、水利、天文科學以及戲曲的發展,能夠產生出這些杰出的人才嗎?但是趙氏《古玩指南》之一席話卻后果不堪設想,它不僅說明國人這時對于認識元代青花瓷器的一無所知,嚴重的是同時也將國人對青花瓷器的研究推向歧途。因為如此來元代沒有青花瓷器,無疑不論出土或傳世的元代青花瓷器都全部被混跡到明代中晚期產品序列之中,且一一作了定位。1952年美國波普博士根據英國人霍伯遜發現帶有“至正十一年”銘的青花五爪云龍瓶為標準器,對照伊朗阿特別爾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博物館所藏元代青花瓷器進行對比研究,發表了兩本書,這時國人剛剛如夢方醒,才知道景德鎮元代窯工還能燒制青花,且美不勝收。中國人雖然這時也開始承認元代有青花瓷器的存在,但仍堅持過去被他們混跡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瓷器依舊是明代中晚期的產品,至今我們很難看到一件過去曾被混跡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從中分離出來,也從未見過有誰提過這方面的異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陶瓷史的悲哀。
景德鎮珠山那里至今沒有發現元代青花瓷器堆積地層的主要原因,宏觀地說,就是我們沒有仔細研究國人對元代青花瓷器的認識是如何起步的,又是如何從過去否定再否定元代青花瓷器的歷史。假若仍從民國年間古玩商的視角,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視為明代的產品,那么景德鎮珠山元代御窯的地層,也就休想發現了。這里有一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有人提出1987年景德鎮珠山出土了幾件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云龍盤和碗,其中一件碗口徑11.2厘米,發表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出版的《景德鎮出土陶瓷》一書上;另外還有一件碗,口徑22.8厘米,發表在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館《皇帝的磁器》一書中。這兩件碗被標明是出土于珠山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地層中。
美國弗立爾美術館對館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龍紋盤的年代更正
筆者曾三次去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得劉新園所長等同仁關照,并親眼見過珠山地下出土的這幾件八思巴字款青花云龍紋碗和盤,另外還有一件澀胎云龍紋高足杯,龍均五爪。在碗盤和高足杯足底所書的八思巴字款識,不僅一樣且十分規整。他們說是所里一位年輕人發現的,具體情況并不十分清楚,把它斷代是明正德年的產品只是根據民國年間的一種通說。他們所謂的這種通說是最早來于國外,出自1920年美國華盛頓弗立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龍紋盤,由于當時在國內外大家還不知道元代有青花瓷器的情況下,被該館波普博士斷作它是明代正德年間景德鎮的產品,所以至今在國內均對波普博士關于青花八思巴字款瓷器年代的看法深信不疑。如耿寶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鑒定》一書中,對正德時期青花瓷器的各方面的特征,就談到正德瓷器“亦有八思巴文書寫的款識”就是指此。英國人霍伯遜包括國人一些同志,還為此說編了一些離奇的故事應聲附合。
但是我們有些人并不清楚,其實波普博士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弄清所藏青花瓷盤上的八思巴字款的內容,因為款識重要的屬性是它標識瓷器燒制的年代。波普博士故去后,1992年,美國弗立爾美術館似乎對館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龍紋瓷盤原定的年代產生了懷疑,所以是年特派詹尼博士(注:美籍華人蘇芳淑女士)利用參加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考古學術會議機會,攜帶八思巴字文題字來北京請相關部門幫助確認。據筆者所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十分慎重。他所派人請同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八思巴字專家、研究員蔡美彪先生予以鑒定,結論為款識當縱讀,是元朝亡國前順帝妥歡貼睦爾“至正”的年號和“年制”四字。同時又指出,款識右面兩個字不是“正德”,更釋不出“嘉靖”的讀音。“至正”與“正德”、“嘉靖”,兩個朝代,前者是元代年號,后者明代中晚期朱厚照、朱厚-的紀年,兩者時間相距一個半世紀,可謂是天差地遠。之后,美國弗立爾美術館已根據中國專家的意見,更正了他們對館藏青花八思巴字款龍紋盤的年代,改定元代末年燒制,不再稱其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產品,并記錄于館藏檔案中(編者注:見文后所附檔案)。幾年后,在不知上述情況的前提下,吉林考古研究所劉振華研究員再次對景德鎮珠山出土的青花龍紋碗上八思巴字款進行詮釋,結論也是元“至正年制”四字。
筆者以為明代地層如若不經擾亂是絕對不會出現八思巴字款瓷器,因為這種猶如天書的文字創制極不科學,是一種音標式文字,并無標示聲調的符號,如果用它來拼寫漢字的讀音,也只能做到約略地描寫漢字的聲韻構成,而不能反映聲調的差異。所以說元朝雖然多次詔令推行全國使用八思巴字,也難為漢人接納,只好暫時在官書上應用,明初已經廢行。另外我們從考古學資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就是我們所發現的無論是墓葬或是遺址還從來沒有見到過明初和其以后的年代,在器物上或是碑碣有書刻八思巴文的內容,所以也進一步說明這種文字在元代之后已為人摒棄。既然八思巴字是元代產物,可見景德鎮珠山元代御窖故地出土諸多的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龍紋碗盤和高足杯,包括同出的大量青花和其它的瓷器,就絕不可能是在明代堆積層發現的,這也就是筆者與諸先生討論話題目的的所在。當今景德鎮那里仍把原本是元代御窯和其它民窯地層堆積中發現的青花等器物,照本宣科錯誤地按傳統觀念把它們都視為明代中晚期的產品,并用它做所謂“標準器”,顯然是混淆視聽且對后學者是一種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