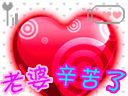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十多年前拙劣的賬外經營手法始終不死,意味著操作風險依然巨大,也就意味著有理由對當前改革的順序進行思考
在某種程度上,銀行案件恰如“礦難”和“禽流感”。
與礦難相同的是,在現有的銀行組織管理框架下,處于科層結構末端的支行所發生的
種種交易恰如數百米下的礦井,高層管理者與基層的信息不對稱的情形,只能用“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困境加以描述,其心態亦只能是自求多福。與禽流感相同的是,金融交易風險往往在瞬間就可以在整個銀行體系中傳染,特別是票據融資,在一系列的承兌、貼現、轉貼現過程中,大量的銀行都可能被拉入一個致命的交易。
當然,恰恰是這些現象構成了中國金融改革的依據,由此進一步提示我們應該沿著怎樣的道路實施正確的銀行治理。
剛剛案發的中國銀行雙鴨山四馬路支行的9.146億元承兌匯票大案,在技術手段上并無任何新奇之處,幾乎是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銀行信貸賬外經營的翻版——銀行內部人“借用”重要空白憑證實施賬外放款,繞過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以進行“地下金融交易”。
由此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深刻的:第一,為什么如此不具備技術含量的盜竊行為可以在十多年間連續重復?第二,地下金融這一似乎只能與地下錢莊等非法金融形式相關聯的操作,如何不斷出現在正規金融機構層面上?第三,面對涉案金額巨大的銀行案件,我們需要的是等待改革績效漸進式地顯現的耐心,還是需要在既定的銀行改革大方向下,認真踏實地思考某些具體步驟安排的輕重緩急,以此尋求最優的金融轉型順序安排?
圍繞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對單個銀行的管理體制、銀行體系的風險傳遞,以及當前的銀行金融服務體制進行多層次的思考。
不統一的法人與地下金融交易
銀行法人治理已經是一個被說濫了的名詞,但是,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于按照西方經典的法人治理理論進行中國式銀行改革的實踐之時,許多不可逾越的障礙迅速出現在我們面前。
比如,我們關心的內部經營者與外部所有者之間的矛盾問題,在中國的銀行業改革中顯然被夸大了——有理由認為,無論銀行的最高層經營者面臨怎樣的激勵或約束,其經營銀行的積極性是無需加以懷疑的。其面臨的根本問題,不在于自身是否具有向所有者負責的正確激勵,而在于其管理是不是一個“統一的”法人。法人的統一性在于,在一家銀行內部,其分支機構是否能按照法人的整體經營方略進行操作;如果不是,那么我們依然需要著手解決“名義上的統一法人、實質上的諸侯銀行”問題。
反思四馬路中行的案件特征,我們發現的是一個不統一的銀行法人內部的地下金融組織體系。
一是“寄生牟利”。簡單地說,四馬路中行的票據案是一種賬外經營形式而不是簡單的詐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六章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惡意串通,故意使用過期或作廢的票據,騙取財物的,屬于票據欺詐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里的關鍵因素,在于票據是否在交易前或交易進行中就已經“作廢”。
事實是,《金融時報》在2006年2月11日公告雙鴨山中行的34張票據作廢,而案發則是在之前的2月7日。票據流通的基本特點是其“無因性”,這是各國的通例,即為了保證票據的流通性,票據的接受方只要明確知道票據的真實性,就可以放心接受并進入下一步轉貼現、再貼現等交易。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作為票據接受方的建設銀行萊鋼支行,并無證據顯示其存在交易環節上的過錯,問題出在出票的四馬路中行。事實上,“作廢在后”而“交易在前”這一基本事實,說明了中行雙鴨山四馬路支行主要負責人通過賬外經營以寄生牟利的手段:其出具的銀行承兌匯票在交易期間并非假票或廢票,各種簽章也具有完全的真實性,惟一的問題是,作為法人的銀行自身被基層的操作者蒙在鼓里。因此,整個交易并不完全適用于《票據法》所定義的“票據詐騙”,而是中國屢禁不止的賬外經營。
賬外經營的初衷,是交易的直接操作者依托正規金融機構進行的地下金融交易,目的是通過寄生于正規金融組織以獲得自身的利益或關聯融資利益。因此,交易的基礎不在于銀行外部,而在于銀行內部的基層管理者,后者的寄生牟利是整個交易的基本出發點。
二是“共謀交易”。雖然沒有完全的證據證明作為持票人的民營企業主朱德全與四馬路中行的利益交易關系,但其共謀卻是不爭的事實。自2003年3月起,四馬路中行的96張承兌匯票被“盜用”,如果沒有里應外合,其盜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問題在于,雙方的交易行為卻嚴格屬于共謀以損害銀行權益的行為,且必然存在某種利益分割。
一方面,銀行的賬外經營因其地下金融的特點而幾乎無一例外具有“高利貸”性質,這種高利貸實際是一類風險貼水,是對冒險違規的補貼;另一方面,借款人也面臨著風險-收益的衡量。只要資金成本在社會平均成本附近,且屬于自身可承受范圍內,接受這種交易本身并無不妥。但是,由于是賬外經營,整個銀行將面臨極度危險的狀態,大量資金通過賬外流入實體經濟,導致所謂的“貸存比”、“資本充足率”、“風險資產總額”等水面上的統計指標根本無從反映水面下的真實風險。
三是“偶然事發”。人事輪換導致銀行案件事發是另一個通例,四馬路中行的情形也不例外。恰恰是后任行長不認前任行長的賬外賬,才導致之后的票據宣布作廢。這一案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常規的內部稽核為什么無法發現合規性上的漏洞,操作風險是否必然在人事輪換之后才能被發覺。案發的偶然性導致了犯罪的低風險。
因此,這里的問題依然在于,中國的分支機構眾多的大型商業銀行能否真正在制度上建立縱向一體化,各層次信息流、數據流完整通暢的管理體系。雖然我們已經實現了追究責任人的體制進步,但是,真正需要問的依然是:誰應該為銀行不統一的法人格局承擔責任,是具體責任人還是銀行管理制度?
系統性金融風險下信用基礎的動搖
票據是具有高度流通性的債權、債務憑證,其高度流通性體現在票據融資的承兌、貼現、轉貼現、再貼現等一系列過程。至少在當前,銀行間的票據交易,實際上把各家行的信貸在整個銀行體系內進行了重新組合,而這種資產的組合實際上意味著風險的傳遞。四馬路中行票據融資案,就充分體現了風險在整個銀行體系中的流轉。這種風險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其結果是整個社會信用制度基礎的動搖。
一是從非系統性風險通過傳染與擴散,演變為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票據的簽發行與票據貼現行往往不是一家機構,如果票據本身存在權利瑕疵,其貼現行因貼現導致資金已經交給持票人,往往面臨損失。我們回顧案發一開始的情形,中行宣布票據作廢,實際上是并不承認自身承擔的承兌責任(無條件見票即付),這意味著建設銀行承擔了中國銀行法人治理缺位導致的事實上的信用風險。倘若貼現的機構又發生了轉貼現,把債權進一步轉移到其他機構,其風險就具有了傳染性。
我們不能肯定,在龐大的票據流通市場上,到底有多少匯票具有地下金融的色彩。這一疑問是合乎情理的——畢竟在四馬路中行主要負責人輪崗之前,其簽發的56張匯票經歷了承兌、貼現和承兌行支付,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因此,整個事件可以視同四馬路中行發生的單個銀行的非系統性風險通過票據交易在整個銀行體系中的傳染;盡管交易過程中并未出現癥狀,但如果發案就等于死亡。這種因法人治理上的漏洞導致的地下金融如果具有普遍性,則整個市場的風險難以設想的。
二是信用基礎和金融生態的進一步惡化。票據存在的惟一理由是流動性;銀行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信用;票據造假的結果是兩者存在的理由幾乎蕩然無存。有大量的個案證明,社會信用基礎的薄弱,與銀行自身內部控制和交易形式有關。
四馬路中行的案件同樣證明了這一點。一方面,賬外經營導致具有權利瑕疵的票據在銀行間票據市場流通,那么,銀行之間的不信任將導致信用基礎的動搖:各方對于對方承兌的票據持懷疑態度,其結果是市場流通性的下降,而對于票據而言,便捷流通幾乎是其存在的惟一理由。缺乏流動性意味著市場的萎縮。另一方面,銀行基層內部人自身的造假行為,證明了銀行不僅僅是金融生態環境的受害者,也是惡化金融生態的直接或間接責任者,其行為顛覆的是銀行賴以生存的惟一理由——信用。
改革次序需要重新評估
四馬路中行案件給我們的心理沖擊是巨大的。十多年前拙劣的賬外經營手法沉渣泛起,意味著操作風險依然巨大,也就意味著有理由對當前改革的順序進行思考。
顯然,目前按照從所有制到管理流程的方式進行改革,那么,機構的扁平化、風險控制的條線垂直化等管理模式,是否必須滯后進行?顯然,當務之急是把一家銀行變成真正統一的法人,至少其總行對支行的實際情況有充分的了解,其次才有理由進入股權、產品創新乃至服務等層次的變革。畢竟,對于銀行而言,安全性永遠是高于流動性和盈利性的第一要素。
對比電信、石油行業的重組,中國大型國有銀行改革中存有“重上市,輕重組”的取向。這里或許包含著“以上市促重組”、“以開放促改革”的無奈,但現實的教訓提醒我們,應當在堅定改革決心的前提下,對于銀行改革的步驟做出更理性的安排。如果各家銀行均以上市為核心目標,并以上市時間表倒推安排各項重組工作,極易使改革更多地停留在財務重組層面,而上市前對于銀行治理結構、業務模式、風險控制等深層次的重組則難以展開。
電信和石油行業改革的經驗表明,只有堅持以重組為本,改革才能真正取得理想的效果。中石油在2000年上市之前,按照業務板塊對整個集團進行了脫胎換骨的縱向重組,財務實現了垂直管理,取消了多法人層次,完成真正的商業化改造。
反觀幾大國有銀行,除了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比率、撥備覆蓋率等財務指標在大量公帑注入后達到或接近了國際水平,并未進行針對性的組織結構調整、建立戰略單元;統一的財務管理、信息管理和風險控制系統均未建立;人事管理和激勵約束機制的改革行之未遠;分行一級的改革尚未完成。總體上看,改革仍停留總行層面,并未觸及到銀行龐大的真正肌理,銀行經營運行機制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七分重組,三分上市”,四馬路中行案的教訓,再次提醒人們這一被市場重復了無數次的基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