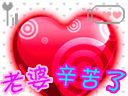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圈內此前頻繁傳出《書城》《萬象》的消息,據說他們都“劫后余生”了。和中國所有雜志的命運一樣,以《書城》《萬象》為代表的小眾人文雜志的命運并不比別人更幸運,也并不比誰更凄慘。小眾人文雜志一面還要在文學文化的傳統領域內跋涉,另一方面則必須轉身面對一個超級多元的、日漸豐富的、變化萬千的商業新時代———它和今天中國所有雜志的歷史命題是一樣,那就是要解決從傳統雜志向現代商業雜志的轉型問題。
業界普遍認為,《書城》和《萬象》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這當然沒錯,但絕對不是問題的全部。《書城》和《萬象》,盡管一個從歷史上找來了淵源(老《萬象》),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找到了榜樣(《紐約客》),但從時代背景來說,他們生不逢時。
現在已經不是理想主義的1980年代,不是所有大小知識分子都得看《讀書》、談論存在主義的年代,說句刻薄點的話,文化已經回歸了它本屬的領域,這注定了《書城》和《萬象》不可能像1980年代的《讀書》一樣成為社會輿論焦點以及文化的議題中心。與經濟問題相比,我以為,這類雜志的主辦者以及主事者保持對時代變遷的清醒認識至關重要。
經濟問題是所有雜志的“一般性命題”,而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步伐才是小眾人文雜志的“特殊性命題”。以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小眾人文雜志”來稱呼這類雜志再合適不過。從1980年代文學、文化占據輿論中心,到1990年代的經濟、法律逐步歸位,到2000年以后的“全球性接軌”,《書城》、《萬象》這樣的雜志已經失去了時代號召力。因為,即使是這類雜志中的領軍讀物《讀書》也一樣不能把握這個時代的精神核心。
正視“特殊性命題”,而不被“一般性命題”所誤導,《書城》、《萬象》的命運就是為他們所中意的那些小眾人群而生存下來。如果《書城》《萬象》還想辦下去,我以為主事者的思路應該做出如上的轉變。與思路相關的則是具體的操作手法以及應對手段。比如,主事者必須意識到網絡閱讀對此類雜志的沖擊,必須意識到設計元素在此類雜志的大行應用,必須意識到要用商業手段來穩固自己的小眾讀者,必須意識到此類雜志要在作者資源上多重整合。
反正站著說話不腰疼,如果《書城》復刊,《萬象》也不停刊,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新變化:《書城》千萬不能再老是刊登北大教授不痛不癢的長篇學術論文,《萬象》也不能成為固定的圓桌論壇,老是那些老頭子在懷風花雪月的舊。有變化就好,盡管他們的前途依舊未定,旅程依舊充滿艱辛。
□本報文娛評論員 蕭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