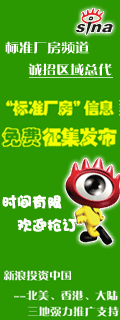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超女超男是對藝術(shù)的玷污”,全國政協(xié)常委兼科教文衛(wèi)體委員會主任劉忠德先生的這一說法引起軒然大波。4月24日,他就此進一步明確表態(tài):“作為政府文化藝術(shù)有關(guān)管理部門來講,不應(yīng)該允許超女這類東西存在。參加超女的被害了,看這個節(jié)目的也被害了,我就這么一個看法。”(4月25日《華夏時報》)
對于超女超男是否“是對藝術(shù)的玷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有發(fā)表意見的
權(quán)利。我不想摻和。可是,“不應(yīng)該允許超女存在”的高見一出,我卻覺得有摻和的必要了。
“不應(yīng)該允許超女這類東西存在”,有何憑據(jù)?是因為其違反了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還是因為其有悖于公序良俗?似乎并沒有見劉忠德先生給出這方面的有力論據(jù)。
“開窗開門新鮮空氣進來,肯定也有蒼蠅蚊子進來”,劉忠德先生只不過是霸道地將超女定性為“蒼蠅蚊子”,并武斷地認(rèn)為“觀眾是在用扭曲的心理、不健康的狀態(tài)看這個節(jié)目……不能讓我們的年輕人在娛樂和笑聲當(dāng)中受到毒害”。別人是否懷著扭曲的心理觀看、是否在笑聲中受毒害,劉忠德先生又是如何知道的呢?這是想當(dāng)然,還是拿著大棒壓人?我不是超女迷,自然談不上劉忠德先生所說的被“害”,可是我身邊的“玉米”、“涼粉”、“盒飯”們的思想、精神似乎依然都很健康,沒見被“害”成啥樣。
超女或許不是什么“陽春白雪”,但即便是屬于“下里巴人”,難道就連存在也不被允許了嗎?要知道,“下里巴人”才“曲低和眾”,而且超女并不比其他一些流行的文藝更粗俗,反而有可取之處。對某一種文藝的風(fēng)行,只要它合乎法律、不乖風(fēng)俗,還是不要管得太具體得好。
在逝世前兩天的1980年10月8日,電影表演藝術(shù)家趙丹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文章。他認(rèn)為,“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非要管得那么具體,就是自找麻煩,出力不討好,就是禍害文藝”,“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的,也限制不了的”。這是趙丹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慘痛經(jīng)歷寫下的肺腑之言,振聾發(fā)聵。他曾經(jīng)在“管得太具體”中,多少年想演魯迅而不可得,“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更曾在“管得太具體”中,只能在“牛棚”中空耗年華。為何不引以為戒,卻依然想管得細致而微,以至于要不允許某一種文藝存在呢?既然“大可不必領(lǐng)導(dǎo)作家怎么寫文章,演員怎么演戲”(趙丹語),那更大可不必將某一種文藝扣上個帽子予以封殺。
“文藝究竟屬于誰?當(dāng)然屬于人民!”巴金據(jù)此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把文藝交還給人民”。超女之所以受到追捧,或許也與其把文藝交還給人民有相當(dāng)?shù)年P(guān)系——公眾得以更直接地參與,并在積極的參與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樂趣,文藝變得更可親可近。
罷黜超女,就能讓所謂的高雅文藝獨尊起來嗎?實在很不見得。人民為何對某些所謂的高雅文藝不待見,大約與其失去了人民性而只成為少數(shù)人的自娛自樂,也不無關(guān)系。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有價值的自會流傳下來,沒有價值的最終只能湮沒無聞。強行扶持什么,不見得有效。強行封殺什么,也終于是徒勞。對于文藝的興衰更替,就應(yīng)該抱有這樣的心態(tài)。不要自以為是地認(rèn)為自己的見識更高明,更不要想當(dāng)然地替公眾作出價值判斷。要相信人民能把握好屬于自己的文藝。
在劉忠德先生的所謂被“害”與“管得太具體”之間,我寧愿選擇被“害”,也不愿選擇被管得沒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