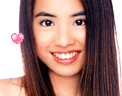|
“全體宗室在首都過著富足的生活,卻不能擁有任何政治權力,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賈志揚筆下的宋朝宗室呈現給我們的最突出印象,就跟趙匡胤奠定的這一宗室管理的制度傳統密切相關
墨斗/文
想當年第一次見到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浩浩長卷擺在面前,還來不及品其中細節,首先注意到畫面的時代背景是“北宋末年”。“末年”的國家不是兵荒馬亂、民生凋敝,而有如此繁榮,著實令我詫異不已。后來讀得多了,方知兩宋之有異于前朝的特點:它沒有之前晉朝那樣血腥的中央權力斗爭(如“八王之亂”),沒有之后明朝那些突如其來的政治斷裂(如“土木之變”),也沒有唐王朝逐漸坐大的地方割據勢力;它一直在或強或弱的危機中經營自己手中的地盤,發展經濟,鼓勵文學藝術。也因此,它求生的過程以及最后的滅亡都顯得格外悲情,看完之后,對這300多年的歷史,生出一種半是向往半是哀憫的情感。
近來有消息說,杭州“五個一工程”要出一部電視劇“精品”——《南宋王朝》,不單要為秦檜和宋高宗翻案,而且要把岳飛塑造成抗拒民族融合的逆天之人。如果不是有意要討罵的話,我想劇組成員還是趁早解散為好,因為宋朝牽連著一種十分牢固的民族情結,與“夷夏之辨”、與民族融合無關的情結,不是“戲說”或者“新說”能夠輕而易舉地解構掉的。最有說服力的事實之一,就是在北宋滅亡的那幾年里,徽宗、欽宗因為自己的政治無能被擄,康王趙構隨即在南方順理成章地即位。他當時有著很強的號召力,開封一陷落,追隨趙構的官員就開始請求他盡快稱帝。賈志揚教授的《天潢貴胄》暗示,這或多或少能夠表明,宋朝的宗室制度對于維持王朝的運轉是有效的,對比各自為戰的南明政權,趙家的其他后裔并沒有因為群龍無首而分頭行動起來。當然,宋朝宗室常年聚居開封,被金兵入犯的時候殺害、擄掠走了大半,也是康王得以順利登基的原因之一。
這種相對團結是賈志揚筆下的宋朝宗室呈現給我們的最突出印象,也跟趙匡胤奠定的宗室管理的制度傳統密切相關。每個朝代的開國之君常有雄才大略,宋太祖對宗室的控制無疑是澤被后世、影響深遠的。“全體宗室在首都過著富足的生活,卻不能擁有任何政治權力,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這種交易使得皇帝樂于追封他們的祖先,厚賜他們的家族,雖然他們是皇位潛在的競爭者。”宋太祖在開國之初就為“敦宗睦族”煞費苦心,公元964年夏歷十一月十二頒布的《太祖皇帝玉牒大訓》是一份奠基性的文獻,趙匡胤把趙宋王朝與此前中原的五個短命朝代區分開來,靠的正是對宗族的強調,樹立宗族完整意識和高度的榮譽感。一方面,此后的宋朝歷任皇帝都重視安撫宗室,提倡教育;另一方面,禁止宗室人員接觸政治權力被嚴格執行,除了趙汝愚在南宋孝宗、光宗、寧宗年間當過30年宰相之外,其他宗室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兩方面之間是一種良性循環的關系。
可以說,宗室生活的穩定狀態,為宋朝給后人帶來強烈認同感確立了一部分基礎。一個王朝內亂的苗頭最容易在皇帝變更時期產生,宋朝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盡管南宋的幾代君主都欠缺子嗣,導致宋孝宗、宋理宗兩人都是從宗室中挑選出來的,但這并沒有導致政局不穩。這實在是太祖當初深謀遠慮的結果。而唯一突破慣例、官至宰相的趙汝愚,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能臣,為偏安一隅的南宋鞠躬盡瘁,只是后來受到權臣韓侂胄的迫害,才退出政治舞臺。賈志揚的分析十分有道理:宗室從政者,他們自己的身份總是難以避免成為彈劾的由頭,大宋300多年歷史上,“天潢貴胄”注定要以儀式性功能為主,能發揮的政治作用總是很有限的。
宋朝主要的失敗在于始終無法擺脫來自北方的威脅,它的軍隊里如楊業、狄青、岳飛、韓世忠這樣的人才均未能建下功勛,反而一個一個成了悲劇人物;宋朝主要的成功在于維護了一個完整的“家天下”,到了南宋,隨著亡國陰影越來越大,宗室在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也隨之增加,他們在制度上打破了太祖設定的框架,但在觀念上,絕大部分人仍能保有祖輩的忠誠,南宋走到末日的時候,他們規模并不大的抵抗運動贏得了足夠的同情分。“Branches of Heaven”——這個書名譯作“天潢貴胄”,其中的氣魄和美感讓人滿心喜悅,與早些年魏斐德教授的那部代表作的書名譯做“洪業”(Great Enterprise)有異曲同工之妙。宗室這一側面,給趙宋王朝增色不少;能讀到這樣的著作和譯本,則是我們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