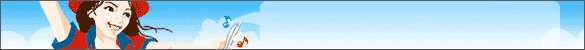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衛西諦
《天邊一朵云》,開場就是個長達一分半鐘的“魚眼鏡頭”,幾乎令人坐立不安,這種“靜態開場”似乎是所有蔡明亮電影的標志。鏡頭呈現了一個變形空間,以及兩個女人(女主角陳湘淇和抱著西瓜的AV女優)的交替而過。這個貌似不知所謂的幽冷鏡頭,等到影片結束才蒸騰出所有內在的熱氣來。從某種角度去看,蔡明亮電影的開始和結束都是最厲害的
,但中間似乎一成不變。這種一成不變不是侯孝賢那種生活化的狀態,而是戲劇感的狀態。并不是說,我們可以完全剔除它的中段,而是說它的中段都是一種“單一的”情緒和情感的量的累積,而非情節性的質的變化。這種累積冗長得讓人透不過氣來,或許只有如此,才能體味到結束時的震撼。就如同《天邊一朵云》的最后,李康生(小康)身體內部的那次無與倫比的噴射。
如果說,有很多電影需要依靠觀眾共同完成的話,蔡明亮的電影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作品必須經過觀眾的讀解、觀看、厭惡——甚至拒絕——來完成。他的作品直接解剖社會生活和情感,但從不“具體地”去描述。對蔡明亮的影迷來說,蔡的作品是通過所謂“符號”來閱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意象是水。無論是以往作品的多雨還是《天邊一朵云》的干旱,“水”這個意象始終不變。他的電影畫面從不缺少或空或滿的保特瓶,也從不缺少體液。在《天邊一朵云》中,西瓜是最重要的意象和道具,它聯系著男女。這種符號性解讀,對于蔡明亮之前的所有作品而言,都有過類似評論,這次不外乎需要加上影像媒體、政治等層面,并加上丟棄又尋回的鑰匙等道具。
但,如果拋開影片的道具/符號,《天邊一朵云》是我所看到的蔡明亮作品中“最愛情”的一部。“愛情”這個主題,即便是在那部叫《愛情萬歲》的電影中,也被蔡明亮做了如下表述:所謂愛情,就是某種平行的、間隔的空間關系。與《天邊一朵云》有血緣關系的《你那邊幾點》,愛情依然是兩個時空之間不可交流的未知物。在后者中,天橋上賣手表的小康和去法國留學的湘淇第一次邂逅;之后拍攝的短片《天橋不見了》里,湘淇回來卻發現天橋被地下通道代替了,在地下通道里,她和小康擦肩而過,彼此未能看見對方;到了《天邊一朵云》中,他們終于在公園碰面,湘淇問——“你還賣手表嗎?”這句兩人之間唯一的對白,喚起了觀眾對他們的所有記憶,也打碎了他們之間一切浪漫的可能性想象(從純粹感性的體驗來說,這句對白的確令人狼狽不堪,蒼涼無比),因為在《天橋不見了》開始,小康就已經不再是一個賣手表的,而成為了一個AV男演員。在那部精彩的短片中,空間建筑的變化,帶來的是身份的轉換或迷失。
說《天邊一朵云》是“最愛情”的,不僅因為小康和湘淇長時間停留在共同的空間里,無語地進行戀愛;更因他們最終得到了溝通,達到了“共同的高潮”。即便是在與之歌舞編排形式相仿的《洞》的最后,李康生拯救了楊貴媚,但那種“愛的表達”也沒這般直接、徹底。而蔡明亮電影的結尾大都關于“溝通”,手段是“無性愛意味的”性愛,最典型的是《河流》中小康和父親的相遇。《天邊一朵云》之間表現愛的挫折和完成,并非使用語言,也非使用行為,而是使用身體。身體主宰了小康和湘淇的愛。根據巴塔耶的理論,相對勞動而言,性活動是一種形式的暴力,因為作為自發的沖動,它會干擾勞動。那么當該活動成為勞動(工作)本身呢?在《天邊一朵云》里,它又成為“正常的”性愛的障礙。作為AV男演員的小康,對湘淇的身體產生一種自然的抗拒,就像他在生活中抗拒作為“工作”道具的西瓜一樣。
直到最后一場戲,我們才能完全體會第一個鏡頭的意味:湘淇終于看到小康是一個AV男演員,他當著她的面,和昏睡不醒的女優做愛(工作),半只西瓜作為道具;到了最后一場戲,西瓜這個靜物、這個客體被尸體一般的女優替代,而大聲呻吟的是旁觀的湘淇。小康和湘淇的眼神第一次變得不再木然,最終兩人完成了影片中唯一一次“非職業化”的做愛——蔡明亮的畫面就是那樣直接。而湘淇的面部這時流下一顆淚水,晶瑩剔透、驚心動魄,混和著絕望、壓抑、熱情、空洞、激動……那顆淚水或許有著多重的象征意味,又或許是最世俗、平凡的一顆女人的眼淚。這時候影片結束。
說《天邊一朵云》是“最愛情”的,不僅是因為身體,還有這個片名。至于身體,蔡明亮自己說:“我的每一部電影都與身體有關。身體是什么?身體可以很美麗,也可以很丑陋;可以很高貴,也可以很下賤。身體是有階級的,是可以被販賣的。身體就像天上的一朵云:天空是永遠存在的,而云卻是漂泊無根的。云朵在天空中有相遇,有分離,來去很偶然,很不確定。我們習慣于濫用我們的身體,我們因此而付出了代價。”白光的一首老歌是片名的來源,被特意安排在片尾。而這片名也是一個具體的鏡頭,在影片中成為“神來之筆”:在戀愛的某夜,小康獨自睡在潔白的床上,床帳、被褥白得無瑕,他仰望天花板,上面畫著藍色的天空和一朵云,然后他緩緩拉上棉被緩緩遮住了自己身體的全部。有人說這是“宗教性”的一個鏡頭,我也可以說那是最詩意的一個鏡頭——那朵頭頂的、“天邊的”云顯然純粹是精神的,純粹是關于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