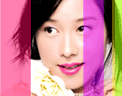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阿戍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地方,不是旅游的必備景點,卻在旅行者之間口耳相傳,使此后慕名而來的人急急探訪,必欲觀之而后快。比如說希臘邁錫尼王城迷宮一般的巷道和威武的獅形拱門,韓國珍島云林山房全景如詩的建筑和收藏的水墨壽石,或是西班牙潘普洛納被狂奔的牛蹄磨亮的街路和象征雄性與勇氣的紅圍巾。
每一個城市也會有這樣的地方,常居此處的人們不會頻繁造訪,卻始終在心里為其辟出一塊空間———或用來收藏,或用來守望。比如說巴黎左岸可以模仿的咖啡香味和無法模仿的悠閑心情,開羅尼羅河岸邊跳動的燈火和隔岸相望的蒼茫,或是羅馬許愿池中沉睡的祈禱和許愿池邊少女的微笑。
北京當然也不例外。景山公園往往會被行色匆匆的觀光客忽略,而老北京知道,從景山的至高處———萬春亭看故宮才是最有味道的角度;一提到西山大覺寺,第一反應是那里的禪茶,但少有人知此處月過中天時分滿庭清輝之美,而這樣的時候,無論是誰都只想靜靜地賞月,哪還有閑心管這百年的護城河里養不養得下一只螃蟹。記得2003年的夏天,跟朋友在后海迷宮一般的巷子里信步夜游,經過醇親王府,聽到院墻內仿佛有二胡的琴音隱隱傳來。在驚喜和疑惑之中又走了幾步,才發現琴聲的主人原來是院墻旁邊小胡同口坐著的一個小女孩。
像這樣的地方,在北京還有不少,但一旦點綴于這個城市1.6萬多平方公里方圓其間,也只能如晨星般微茫。大部分地方高樓大廈林立、街道密如棋盤,即便有許多聞名遐邇的美景,卻不知在哪里曲徑通幽。也難怪北京總是容易給人這樣的第一印象———真的很大,但是似乎有點深沉得過頭。
所以,很多朋友跟我描述他們第一次接觸北京的感覺時,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到“灰色”。當然這不是說北京的天氣總是在跟沙塵肉搏,或是影射北京的城市景象有頹敗之嫌,我想,他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只是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中接觸過太多關于歌頌首都的東西,對北京多少醞釀著一種脫離實際的想象。而現實的北京何止天安門或是長安街,并且這些地方也不會真的發出什么光芒。與祖國的心臟握手的興奮感漸漸平息之后,灰色自然成為北京深沉的主基調。
不過,北京更招牌的顏色一定是“紅色”———紅旗的紅,也是紅墻的紅。
一個從事設計的朋友說,第一次看到故宮城墻時,感到顏色有點別扭,仿佛因為時間久遠而微有褪色,總覺得可以更鮮亮一些;在北京待了一段時間后,越來越能體味這顏色的韻味與內涵。后來,他以此為創意完成了服裝設計作品,一反以往用明黃為主表現中國古典宮廷服裝風格的傳統,最終為他贏得了獎項與掌聲。
而對于北京城的文化氣質,令我感受最深的既不是深沉的灰色,也不是磅礴的紅色,而是從北京老百姓簞食瓢飲的日常生活中散射出來的“透明”。
雖然作為昔日的皇城和今天的首都,北京有其無法回避的象征意義,但是北京地處南北交通要沖,自古傳承燕趙地域文化,北京人性情中更多的是一份熱情豁達和與人為善。他們不會因為自家樓上200年前住過一個詩人而感覺身價倍增,也不會因為隔壁現在就住著一個詩人而覺得那是個笑話。他們對自己的傳統有著特殊的抬愛,燈節和廟會被他們描述起來怎么就那么好玩和熱鬧;同時,他們也不吝于對外來者顯示自己的友好。比如在北京問路,通常是三言兩語說不清的,如果碰巧這位得閑,又發現連比劃帶說不能解決問題:“得,甭費這嘴,我帶您走一趟得了。”我初到北京時,就曾不止一次領受過這樣的待遇。這種感覺,就像冬天從樓群的陰影里一下子走到了透明的陽光之中。
所以,后來即便看到報章雜志上抨擊北京人的人情味兒里隱晦地透著傲慢,我也會認真地相信那并不是某種無意識的精神排外,而有可能是因為熱情的尺度往往難以把握,文化的差異也容易帶來誤解。但隨著類似的評價逐漸擴散成一種聲音,我開始由衷地為北京擔心。
因為這種誤解的破壞力是相當驚人的。對一個城市居民的評價會很快蔓延成為這個城市的形象定位和文化釋義。而扭轉一種成見,往往需要花去幾代人的努力。對于這一點,曾一度被刻板形象困擾的上海,應該有足夠的心得可以跟北京分享。
不過擔心歸擔心,北京必定還會不斷迎來新面孔,問題只在于北京究竟會給他們什么感受。是一頭撞入的驚艷,還是似曾相識的熟悉?是和我一樣憂慮北京古道熱腸的人文傳統在現代性結構中的式微,還是能在這個城市的盛名與形象之外找到一種仿似已經書就多年的文化共鳴與心理默契?無論如何,有一點我相信,像北京這樣的城市,絕對是宿命中注定要與它邂逅的人永遠無法做好心理準備的對象。
有幸在北京跨進新世紀的門檻,也許還會在北京停留很長時間。至今清晰地記得闖蕩北京前后,自己的心態由輕狂到平和的變化,以及感受從惘然到清晰的更迭。那么,即便多年以后回憶起來,也該歸結為我與這個城市有緣。因此,我才得以行走于其間,收起略顯輕浮的舉止,保持誠意謙卑的態度,從一種“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的氣質里去解讀這片都市叢林延綿幾個世紀的枯榮。
《國際金融報》(2006年01月13日第二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