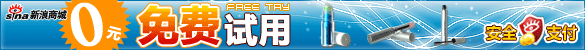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歐巍是誰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08日 19:07 《環(huán)球企業(yè)家》雜志
歐巍是誰? 1990年代中期外資PE試水中國的見證人、新橋進入深發(fā)展的最終促成者、中國首家本土PE渤海基金掌舵人……一個低調(diào)先行者的個人旅程 文 《環(huán)球企業(yè)家》記者 羅燕 “你怎么對一家銀行的股東及主管單位解釋,一家私人股權(quán)投資公司的價值呢?” 短暫停頓后,渤海產(chǎn)業(yè)基金總經(jīng)理歐巍對《環(huán)球企業(yè)家》說:“這確實很難回答。”再度沉默之后,他說:“到今天,進入銀行的私人股權(quán)投資還是只有一個成功案例。而新橋能夠進入深發(fā)展,根本上還是因為它有銀行業(yè)的成功經(jīng)驗。” 這是2007年11月20日。素少面對媒體的歐巍在天津接受專訪后,即奔赴機場,“去西北,肯定不是去玩”。2天之后,他在成都宣布,渤海產(chǎn)業(yè)基金將收購成都市商業(yè)銀行大約10%的股份。 新橋進入深發(fā)展,渤海投資成都商業(yè)銀行,是歐巍所參與過的兩次私人股權(quán)投資進入中國銀行業(yè)案例,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商業(yè)史上僅有的兩次由私人股權(quán)投資公司投資中資銀行——這無疑讓39歲的歐巍成為了一個符號性的人物。 12月初再度接受本刊專訪時,提及在成都商業(yè)銀行的競購中的“國字號”優(yōu)勢,歐巍并不否認。但他隨即以極快的語速反問說:“你認為我們進去就只是因為人家看著我們是國資的背景嗎?你知道有多少國資的在搶嗎?沒錯,進去就是勝利,但怎么進去的?單純是因為你有錢肯定不行,單純是因為你是國資肯定不行,肯定有別的原因。會不會因為他覺得你對這個行業(yè)有更深刻的認識呢?會不會是覺得你和老外合作過?會不會是看到你如何應(yīng)對豐隆銀行呢?” 一系列反問過后,他再次恢復笑容:“說不定是因為我長得英俊”。 正如這片刻之間的變換,歐巍或許是中國私人股權(quán)投資領(lǐng)域最難被認識的投資者。他并不高調(diào),永遠對自己不愿涉及的話題不予置評。外界對他的了解只取決于一點:他總能在恰當?shù)臅r間出現(xiàn)在恰當?shù)牡攸c。 歐生于北京,8歲以后遷居香港,后赴加拿大讀書。作為最早進入中國PE業(yè)的投資人士,他被貝恩資本董事總經(jīng)理竺稼被評價為“非常聰明”。其人好讀古書,自稱從中研究中國人的心理和政治,但與多數(shù)嚴肅的投資者不同,他會補充說:“從古書到毛選到蠟筆小新,我都看”。 探索 渤海基金自2006年12月30日正式掛牌,今年4月4日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時才選定高管人員和五位投資委員會成員。在此之前,渤海基金的正式員工只有歐巍一人。 但比業(yè)內(nèi)多數(shù)人預期為快,在開始招聘、培訓之后僅半年時間,渤海基金就相繼宣布了兩筆交易:15億元購買天津鋼管集團部分不到20%的股權(quán);9億元購買成都商業(yè)銀行近9.23%的股權(quán)。 在中國這個各方PE競逐的市場,歐巍保持著兩個基本原則。其一是充分發(fā)揮國資私人股權(quán)運營公司的優(yōu)勢,投資那些外資審批較難通過的行業(yè),比如天津鋼管和成都商業(yè)銀行分別所在的國有鋼鐵業(yè)和銀行業(yè),形成差異化競爭。其二是不以價格獲勝。在當前經(jīng)濟“流動性過剩”、眾企業(yè)價格隨著A股市場瘋長的時候,唯一避免“買高”的方法便是發(fā)現(xiàn)真正有價格和抗風險能力強的企業(yè),即便在市場進入低潮之后也能挺過。 比如,以渤海基金購買天津鋼管的價格,天津鋼管的估值達到了近百億人民幣,被外界評論為“太貴”。對此,歐巍的解讀是:“如果是一家簡單的鋼鐵企業(yè),說它估值高,我不反對”。但天津鋼管是中國最大的石油管材生產(chǎn)基地,屬于石油配套產(chǎn)業(yè),利潤率比寶鋼等鋼鐵行業(yè)主要玩家更好。隨著油價高企,這個行業(yè)的發(fā)展前景是可預期的。 關(guān)于天津鋼管的投資,業(yè)內(nèi)還有另外一種質(zhì)疑:根據(jù)預期,天津鋼管離上市大約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看起來并非一個需要太多判斷力的投資項目。 這是歐巍并不反對的。他將此定性為“風險承受能力”和市場機會的平衡。對于剛剛起步的渤海基金,不能刻意追求高難度的項目,“作為一名基金管理者,不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取向去做項目,基金首先是為投資者創(chuàng)造回報,這最重要。什么東西能獲得高回報?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定義,”他告訴《環(huán)球企業(yè)家》。而且,在不同市場環(huán)境下,基金的戰(zhàn)略也應(yīng)該有相應(yīng)的不同。“在一個調(diào)整中的市場,只能做些高風險的事情;而在一個上升的市場,就能做一些搭便車的東西。”天津鋼管便是一個“搭便車”的交易。 而隨后的成都市商業(yè)銀行,則更能展示渤海基金的市場競爭力。 成都商業(yè)銀行的規(guī)模在西部商業(yè)銀行中位居第一。據(jù)歐巍稱,在這次成都商業(yè)銀行的競購中,除了最終進入的十幾家機構(gòu)之外,還包括另外數(shù)十家競爭者。并且,在這一輪競購之前,馬來西亞豐隆銀行就已經(jīng)被確定為第一大股東——它投資入股的19.5億元,占19.99%的股份。 因豐隆的介入,對于眾多競購者而言,一個重要的挑戰(zhàn)就是,不僅需要說服成都商業(yè)銀行,還需要和豐隆銀行達成利益一致。關(guān)于如何說服豐隆銀行接受,歐巍稱:“這是一個商業(yè)秘密。” 但渤海基金之所以能突出重圍,歐巍總結(jié)為“對金融業(yè)的深刻認識、作為內(nèi)資不需要審批、決策程序簡潔、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和各方的合作,包括和外資的合作體現(xiàn)了專業(yè)性”都起了重要作用。 歐巍曾是新橋投資韓國第一銀行投資時投資委員會的一員,也從頭至尾參與過新橋和深發(fā)展的談判,至今還擔任深發(fā)展的董事,對于銀行業(yè)發(fā)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都有著相當?shù)慕?jīng)驗。 另外,兩筆交易的共性還包括,渤海基金都并未占據(jù)主導地位,以及都有戰(zhàn)略投資者的加盟。對于并未占據(jù)主導權(quán),歐巍有一個極為實際的看法:在過去兩年資本市場大熱階段,獲利最豐厚者,并非某個項目的主導人,而是在所有上市項目都以招股價投資,隨漲退出的恒基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兆基。 同時,成都商業(yè)銀行引入了豐隆銀行,而天津鋼管已經(jīng)和太鋼組建了合資公司,并有可能進一步接受太鋼的戰(zhàn)略投資。可以推論,對于剛剛起步、在行業(yè)經(jīng)驗上還需培育的渤海基金來說,這能為其省卻很多力氣。 但是,歐巍也表示“渤海現(xiàn)在所做的事情,還是處于行業(yè)的低端,離國際水平還差很遠,要發(fā)展成一個有國際水平的投資者,肯定還要做一些更加復雜更加大型的交易”。為此,在其規(guī)劃中,渤海基金發(fā)展的早期將盡可能多地和國內(nèi)外PE的合作。比如,聯(lián)手華為收購美國電信公司3Com的貝恩資本便與其有所探討,頗有機會合作。 見證者 在中國,私人股權(quán)投資的發(fā)展不過近十年的時間,并明顯地分為三個階段:1990年代,在中國經(jīng)濟剛剛起飛之時,私人股權(quán)投資公司曾掀起投資中國的第一輪熱潮,和大量國企組建合資公司,卻因為缺乏退出渠道而損失慘重;第二階段則由亞洲金融危機引發(fā),亞洲宏觀經(jīng)濟的低迷使得PE加大了對該地區(qū)的投入,基本上是從這時起,凱雷、華平、新橋在亞洲包括中國活動才更加頻繁;第三階段來自近年來中國經(jīng)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外資PE爭相涌入中國,背靠火熱的A股市場而興起的人民幣基金則可能和他們形成競爭之勢。 作為為數(shù)很少參與到這三個階段的歐巍,也從另一個角度體味了中國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2002年新橋提出收購深發(fā)展時,曾花費大量時間在“交易價值”上說服總部——當時,曾有多家外資機構(gòu)考察過深發(fā)展,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等大型投行,但由于其資本充盈率較低都未敢投資,而新橋內(nèi)部也存在“是否值得投資”的長期爭論。五年之后,深發(fā)展的股價已經(jīng)比2004年交易成功時翻了四倍多。如今,在成都商業(yè)銀行的這個交易上,已經(jīng)是明顯的競爭過熱:“以前談的是中國折價,現(xiàn)在談的是中國溢價”,歐巍感嘆到。 在十二年的PE生涯中,歐巍與國企的交道甚多。1993年,剛從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畢業(yè)一年的歐巍,在香港科爾尼咨詢公司所做的第一個項目,便是來到四川的一個縣,幫助提姆·克利索德考察當時嘉陵摩托的一個零部件加工廠。 著有《中國通》一書的提姆·克利索德,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叫“祈立天”。他于1989年開始來華,1992年開始作為安達信中國負責人,為想進入中國的投資者尋找項目、提供咨詢服務(wù),是鄧小平南巡之后第一批來華將華爾街資金注入內(nèi)地的投資家之一。當年,克利索德和同伴在中國投資時考察的起點,便是山路連綿不絕的四川省。“有那么一兩次,我們的車輛在兩壁都是懸崖的山谷底部爬行,沿著蜿蜒的土路開上整整一個下午,才最后在山谷最深處發(fā)現(xiàn)一個巨人般的工廠”,他在書中寫到,幾千員工在那里生活,有著自己的幼兒園、醫(yī)院、電影院等。 在四川之行的末尾,克利索德終于從幾位喝高了的中方人士那里獲得選址的原因—— 六十年代中期中蘇關(guān)系惡化之后,蘇聯(lián)工程師撇下正在幫助中國搭建的工業(yè)體系,帶著圖紙全都撤離中國。之后不久,為防御戰(zhàn)事,所有的兵工廠都從城里和沿海地區(qū)撤出,搬到荒無人煙的大山深處,以避開轟炸機的視線。然而,從1990年代起,很多兵工廠得不到政府的資金支援,便利用自己的生產(chǎn)技術(shù)開始了漫漫轉(zhuǎn)型之路。歐巍所去的零部件加工廠便是其中之一。當時,這些企業(yè)除了相當窮困之外,“這邊在工作那邊還能聽到槍聲”,歐巍回憶到。 兩年之后,年輕的歐巍便加入剛成立的新橋資本,當時,新橋第一支基金是完全針對內(nèi)地的中國基金。歐巍先后對維維豆奶、冠生園等國有企業(yè)進行投資,建立了合資企業(yè)。不過,當時的熱潮有著明顯的缺陷:在缺乏在香港上市的紅籌模式之時,投資者們并不清楚退出途徑。新橋在其中“做得還算不錯”,歐巍回憶,維維豆奶采取賣給戰(zhàn)略投資者的方式退出,而冠生園則是賣給了上海市政府。并且,在和國企的多次接觸中,歐巍逐漸形成了一個理念:國企的質(zhì)量一直大于在國企外的人的判斷,它們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進行股東多元化。 而在這一波浪潮退掉之后,新橋終于找到了它在中國的最大獵物——深圳發(fā)展銀行。 破冰 新橋進入深發(fā)展兩年多的漫長談判,以及其閃電般宣布“聯(lián)姻”到對峙公堂、再到皆大歡喜的戲劇性切換,一直給外界留下一個很大的謎團。關(guān)于歐巍在這個交易中的作用也眾說紛紜。一種說法認為,新橋和深發(fā)展的談判全程,單偉健一直起著相當關(guān)鍵的作用。而另一種認為,擔任第二輪談判首席代表的歐巍起到了扭轉(zhuǎn)整個局面的關(guān)鍵作用。 “故事有很多版本了,”當記者問及這個話題時,歐巍如此開場。他也表示,在重啟的第二輪談判中,新橋方僅由他帶著一個助手進行談判并游說政府進行審批。2004年底,新橋入主深發(fā)展一事終于以“交易通過審批成功締結(jié)”的為團圓結(jié)局時,他和另外三個參與交易的同事,四個大男人在一起抱頭痛哭,晚上喝得伶仃大醉,而在這四個人中,并不包括代表深發(fā)展進行第一輪談判的新橋董事總經(jīng)理單偉健。他們的感慨,是因為過程“太難了,太難了”,關(guān)于各種復雜條款簽署的協(xié)議有五六寸厚,“即便是在后面的政府審批環(huán)節(jié),都有幾次即將脫軌的危險”。 對于他們個人來說,這是一場漫長的、隨時可能落入深淵的歷險,但是,對于中國銀行業(yè)的發(fā)展和私人股權(quán)投資在中國的發(fā)展,這確是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 在新橋購買深發(fā)展之前,盡管新橋、凱雷等私人股權(quán)投資公司已經(jīng)進入中國,但是對于私人股權(quán)投資的概念,普通民眾和監(jiān)管部門的認識幾乎為零。于是,當2002年十月,深發(fā)展第一次發(fā)出公告,宣布和新橋締結(jié)戰(zhàn)略時,甚至有媒體用“背景復雜,來歷模糊”來形容新橋資本。 2002年,距離新橋成功擊敗匯豐銀行,收購韓國第一銀行51%股權(quán)的驕人戰(zhàn)役已經(jīng)兩年的時間。在這兩年中,以單偉健和歐巍為首的中方人員在韓國第一銀行的成長中充分驗證了銀行在亞洲這個新興市場的巨大價值。于是,他們也力圖在中國尋找類似的大獵物。歐巍表示,當時,新橋在中國考察過的銀行“有很多家”。 但是,在國家對外資控股的明確規(guī)定中,單個外資股東持股不得超過20%。只有在股權(quán)高度分散的深發(fā)展,才能在獲得不到20%股權(quán)的情況下掌握控制權(quán)。同時,深發(fā)展擁有全國性的銀行牌照,有一定數(shù)量的網(wǎng)點,主營業(yè)務(wù)率一直在同業(yè)中位于前列,因此,這個選擇對新橋基本上是“唯一”的。而當時正逢深圳市政府退出深發(fā)展、引進外部本的決心甚為堅毅之時——在發(fā)布公告之后,新橋派駐深發(fā)展的收購過渡期管委會甚至全面接管了深發(fā)展的許多業(yè)務(wù)。 所以,新橋的最初預計是,這起交易2002年底就應(yīng)該能完成。卻沒想到,談判在半年之后非但沒有達成協(xié)議,反而陷入僵局。2003年,深發(fā)展撤銷新橋的收購過渡期管委會。而新橋則起訴深發(fā)展及其國有股東“違反協(xié)議條款”。 當提及雙方談判的最核心矛盾是否是價格問題時,歐巍當即說“這是一個小問題”,旋即表示“價格是一個因素,還是蠻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是“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系列的問題。就像那個雜技,轉(zhuǎn)幾個盤子,九個盤子可以同時轉(zhuǎn),一個盤子摔下來,那就都摔了。因此一個問題,而是很多東西的配合。”而據(jù)知情者稱,臺灣“中國信托商業(y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新橋競爭者的參與和新橋方因有銀監(jiān)會支持而具有的強硬態(tài)度是矛盾的關(guān)鍵所在。 雙方的僵局一直持續(xù)了一年左右,歐巍回憶到,直到大家都覺得官司這么鬧下去,對誰都不利。正在此時,李澤楷介入,作為中間人說服雙方重歸談判桌,成為峰會路轉(zhuǎn)的關(guān)鍵所在。 關(guān)于李澤楷的介入,歐巍不作任何評述,只表示,無論如何,在李澤楷介入之后,深發(fā)展和新橋都重新獲得了一個平心靜氣、再度談判的機會。 新一輪的談判,歐巍代替單偉建成為新橋方的談判代表。歐巍表示這“可能是一個雙方面的意見”。新一輪談判他力圖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得氣氛融洽——首先要達成共識的是:這個事情是不是最終對雙方都好的?在這個前提之下,再博弈也就是在這個范圍里頭,是為了成這個事情的博弈,而不是不成這個事情的博弈。 于是,第二輪談判進展出奇地快,從撤銷訴訟到協(xié)議簽訂,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可是,這并不代表著交易就能順利締結(jié)。新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各個監(jiān)管部門的解釋和答辯。 盡管當時已經(jīng)發(fā)生了幾起國外投資者進入的事情,比如匯豐進入交行。但是,監(jiān)管部門對于PE的概念卻非常陌生。歐巍必須向銀監(jiān)會、證監(jiān)會等政府機關(guān)逐個解釋PE的概念、新橋的背景等等。“整個審批過程是相當長,相當復雜”,歐巍表示,他2004年5月之后,基本上都在北京,提交各種各樣的報告以及接受各種答辯。 在說服政府的過程中,新橋所用的是之前的成功案例,即韓國第一銀行的收購案。在成功收購韓國第一銀行之后,新橋通過注入資金、知識、經(jīng)驗、資本等專業(yè)要素資源,幫助它實現(xiàn)再造和資源整合,使起規(guī)范運作。這些信號表示:新橋雖然不是銀行的經(jīng)營者,卻是銀行經(jīng)營的內(nèi)行,知道在進入之后如何幫助其消化不良資產(chǎn)和確保新增資產(chǎn)的健康。 2004年底,這個PE在中國銀行業(yè)首次破局之戰(zhàn),終于完成。事后回顧,歐巍表示“以和為貴”是他做事的最重要風格。至于是不是自己的特殊之處影響了談判,他表示:“希望如此。” 新冒險 經(jīng)歷了深發(fā)展的漫長談判和復雜交易,在到新橋第十一個年頭的時候,歐巍決定趁年輕的時候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而外界傳言,在新橋的談判中和單偉健造成的關(guān)系隔閡,也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對此,歐巍并不置可否。 而給他帶來“新冒險”的,正是被稱為“紅籌之父”的梁伯韜。 歐巍和梁伯韜很早就熟識,在新橋和深發(fā)展洽談收購之時,正是歐巍請來當時在所羅門銀行的梁伯韜擔任深發(fā)展的財務(wù)顧問。 2006年6月,梁伯韜找到歐巍,表示他正在參與渤海基金的組建,希望在這個行業(yè)多年的歐巍能在組織架構(gòu)等多方面提供一些建議。然而,正當渤海基金組建進展順利之時,梁伯韜卻因為電訊盈科的收購案沖突,不能出任渤海基金的負責人。于是,歐巍便成為最終人選。之所以選擇這條路徑,和2006年的宏觀經(jīng)濟形勢有關(guān):中國股市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進入高漲時機,人民幣基金的退出渠道得到保障,歐巍覺得,利用國內(nèi)基金進行投資的“時機到了”。 “你當時有沒有考慮過作為第一支國資人民幣基金的壓力,包括發(fā)改委商務(wù)部諸多政府機關(guān)和部門都在關(guān)注?” “從沒有想過”,歐巍仰起頭,大聲地否認后舒緩的解釋道,“首先認定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再試著去做。如果今天做其他國外基金,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這個東西是特殊的,好玩的。”
【 新浪財經(jīng)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