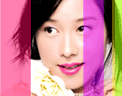奚志農:野生動物攝影師的孤獨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1月13日 16:59 國際在線 | |||||||||
|
中國是“世界上最難拍攝野生動物的國度”,不僅大型哺乳動物數量稀少,動物對人還懷著高度戒備之心。奚志農把拍攝野生動物看做是一種責任,并為瀕危物種的生存危機憂心忡忡。 “在野生動物的安全和你的照片之間,野生動物的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2004年12月1日,中國第一個野生動物攝影訓練營開營,在培訓課上,活動的組織者奚志農反復強調一
作為一名職業野生動物攝影師,奚志農希望每個攝影師都能和他一樣,在按下快門的同時,還能想到一些其他的東西,比如責任。 奚志農需要同伴,在孤獨地拍攝了20年后,他迫不及待地開始親自傳道。 無人問津的行業 在中國,野生動物攝影的落后不言而喻,從《動物世界》到《探索》頻道,電視臺所播節目畫面幾乎全部引自國外,國內的自然地理類雜志無力像美國《國家地理》那樣培養自己的攝影師隊伍。在中國的自然保護區,經常見到的多是國外的攝影師。 奚志農是個例外。在陜西長青自然保護區工作的賀明銳說,他在長青見到的惟一一位國內職業野生動物攝影師就是奚志農。 1990年代,《動物世界》決心要拍自己的野生動物紀錄片,奚志農因此有機會成為央視的臨時工。當時最成功的一次嘗試,是攝影師祁云拍攝了一部6集的片子。 但央視在嘗試之后得出的結論是:拍攝成本高于引進國外紀錄片所需的費用,收視率還不如國外的片子高。最終央視失去了興趣,卻留下了像奚志農這樣欲罷不能的“愛好者”。 從1983年因為“喜歡鳥兒”而產生學攝影的念頭,到變成今天的著名“環保斗士”,奚志農人生的20年就這樣在山林間溜走,而自己抱定的職業卻愈發凋敝,孤獨和疲憊之感常常莫名地襲來。 “每天都有物種在滅亡,而我們還有那么多的物種,從來沒有被影像記錄過。”奚志農說。 “為保護而拍攝” 短短一周的訓練很快結束了,營員們分別返回各自的工作崗位。奚志農自己也要趕往秦嶺,最近兩年,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那里。 秦嶺作為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目前是除青藏高原以外最容易見到大型哺乳動物的地區,有近20個自然保護區和保護地分布在此。奚志農的目的地是周至自然保護區——中國川金絲猴種群最集中的區域,大約有1500只川金絲猴在那里生活。 從1992年以來,奚志農一直在追蹤拍攝有雪山精靈之稱的滇金絲猴,他有一個夢想,就是讓滇金絲猴走上《國家地理》的封面。2001年他在英國“BG野生動物攝影年賽”上獲得“瀕危物種”單項大獎的照片就是一張滇金絲猴的影像。 奚志農與金絲猴有著非比尋常的關系,拍攝金絲猴讓他獲得了國際聲譽,也使他成為了著名的“環保斗士”。1995年,剛剛結束了對滇金絲猴的艱難追蹤后,奚志農聽說云南省德欽縣政府準備砍伐白馬雪山南部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那片森林是滇金絲猴最后的家園。于是他開始拿著自己剛剛拍攝的照片四處奔走吶喊,最終為金絲猴留下了一小片棲息地。 奚志農對這個結局并不算太滿意:“那些種群,被分別桎梏在幾平方公里的狹小區域,不能和其他種群交換遺傳基因,最終將導致物種退化。”但這畢竟在中國是“第一次”,美國《新聞周刊》在1996年以“中國正在萌芽的綠色革命”為題報道此事,并認為“這將成為中國人環保意識的分水嶺”。事實正如其所料,當3年后奚志農再次將一組充滿了凄涼和憂傷色彩的藏羚羊照片呈現在國人面前時,中國民眾的反響前所未有的強烈,似乎每個人都成了環保主義者。 可以說,滇金絲猴事件堅定了奚志農“為保護而拍攝”的理念。在那些寧靜的富有表情的動物肖像面前,幾乎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拍攝者與自然的對話,這被其他攝影師稱為“奚志農風格”。 “我對物質的要求不高” 西北大學在周至保護區內設立了一個基地,常年有實習的學生和研究者駐扎在那里,經過長期投食和觀察,這些有著金色毛發的猴子已經習慣于被人窺視,這種“奢侈”的待遇是奚志農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 對于野生動物攝影來說,一張高質量的照片需要無限近的距離。不幸的是,中國被國際攝影界稱為“世界上最難拍攝野生動物的國度”,不僅因為大型哺乳動物數量稀少,還因為動物對人懷著高度戒備之心。 1992年開始,奚志農在云南白馬雪山拍攝滇金絲猴,守候了3年,但只有兩次拍攝到這些“雪山隱士”的身影。2003年他去了一次加拿大,那里野生動物數量之多和它們對人的親善讓他感到嫉妒,但他很快冷靜下來:“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拍到了3萬只雪雁同時飛起來的鏡頭,但那又怎么樣呢?任何一個有相機的人,按照攝影手冊上的說明,在指定的時間到達指定的地點,都能拍到3萬只雪雁。” 1999年,奚志農遇到一位美國《國家地理》的攝影師,當他得知對方一年要消耗7000卷反轉片時,不禁暗自驚訝:“我這輩子恐怕都拍不了這么多反轉片。”1992年,為了上白馬雪山,他奢侈地買了8卷過期的反轉片,而他當時拍過的反轉片總共還不到200卷。 奚志農的妻子史立紅當年出于仰慕而愛上他,后來成為他事業上志同道合的伙伴。2003年,奚志農歷時十年拍攝的紀錄片《追尋滇金絲猴》在第十一屆“自然銀幕電影節”上獲得了“TVE獎”,這是中國紀錄片首次在該電影節上獲獎,而與他們競爭的其他參賽者包括BBC、美國國家地理、探索等世界頂級制片公司。 一個職業野生動物攝影師在中國如何生存,奚志農說:“我對物質的要求不高,只知道一直拍下去,然后就堅持到現在。”對此史立紅看得更清楚:“奚志農一直只按照自己的興趣拍攝,而不是按照市場的需求。他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但同時失去了市場化的可能性。這些優點和缺點,同時在《追尋滇金絲猴》里表現無遺。”她覺得,那個獎項的授予多少有些鼓勵的味道,因為這部片子是當年惟一一部由發展中國家制作的獲獎影片。 與動物溫柔接觸 看過奚志農拍攝的照片的人幾乎都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照片中的動物仿佛具有某種智慧,而且似乎正在預備和人做某種交談。 多次和奚志農一同赴野外拍攝的攝影師,供職于陜西長青保護區的賀明銳解釋了這個玄妙的問題:“那就是動物本身的表情,要捕捉到這樣的表情,關鍵是你不能驚擾它們,不要讓它們看到你,或者即使看到了,也要讓它們覺得你是無害的。” 在國外,這種理念早已經深入人心,以研究黑猩猩而聞名的女科學家珍妮·古道爾,曾經為人與動物的接觸立過一個最高的標準:“如果你坐在它們的身邊,它們都不理你,你就達到了人與黑猩猩之間的和諧境界了。” 不過,有時候這種“溫柔的接觸”是相當驚險的。賀明銳在和奚志農一同拍攝羚牛時,經歷了一次超近距離的接觸。開始時和羚牛的距離稍微有點遠,他們為此放棄了隱蔽,過了一會兒,一部分羚牛注意到他們,朝他們沖過來。賀明銳看見鏡頭里的牛頭越來越大,最后超出了取景框。他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扭身逃走,羚牛肯定會發動攻擊,所以他只好像奚志農一樣穩穩當當地站著繼續拍攝。等羚牛對他們失去興趣走開后,他們估算了一下距離:不到3米!而通常應該在100米左右。 周至的金絲猴給了人們溫柔地接觸的機會,這里常年聚集著研究者,猴群似乎對人早已習慣,人們從營地出發步行30分鐘,就能在一片樹林里看到它們。夏天時奚志農已經接觸過這個不怕人的金絲猴家族,這一次,他希望能夠拍到它們在雪天的生活起居場景。 從他來的第二天起,周至接連下了好幾場雪,溫度也在不斷下降,即使在室內生上爐子,氣溫也在零度左右,但奚志農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對他來說,在野外工作,還能住在房子里,就已經是非常奢侈的了。這一點,和奚志農同來的攝影師關克表示既佩服又害怕,這個看上去文弱單薄的人,總是用自己的吃苦耐勞去鼓勵和要求別人。 幾場雪后,關克心滿意足地先走了,這幾天他們的運氣不錯,不僅拍到了金絲猴,還拍到幾種珍稀鳥類。奚志農留下來,等待天氣預報中說的更大的一場雪。前幾次來周至,拍攝都不是很順利,奚志農希望這一次能夠有好運氣。 憂心的“和諧” 12月下旬的一個早晨,秦嶺鋪上了一尺多深的積雪,奚志農對此覺得心滿意足,并催促那些還在吃早飯的人加快速度。 像往常一樣,他們沿著營地旁的一條小路,來到猴群通常逗留的地方,但沒發現猴群。按照經驗,奚志農向叢林更深處走去。 猴群棲息地的下面站著幾個人,他們是營地的學生雇來的,手里拿著食物,但猴群似乎興趣不大。最后,這幾個人失去了耐性,開始用恐嚇的方法,企圖把猴群趕往指定的地方。 眼前的這一幕撕下了某些看似美好的表象。 1999年,昆明市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滇金絲猴定為吉祥物。作為第一個將滇金絲猴介紹給大眾的攝影師,奚志農覺得亦有榮焉。世博會前,當地電視臺特地去做一個節目,然而為了便捷地拍攝到滇金絲猴的圖像,攝像師動員了一批村民去驅趕猴群,兩只小金絲猴因此從母親的懷里掉了出來。缺乏經驗的人們沒有立刻撤走,而是把小金絲猴帶到了昆明,最后經動物專家搶救無效而死亡。更不可思議的是,人們完全忽略了他們給猴子帶來的災難,卻在報道中大肆宣揚對猴子的拯救,稱之為“人與自然的和諧”。 這一次,奚志農請求農民們停止驅趕猴群,并撤回來試圖說服研究者們走到地勢更高一點的地方,而不是強行要求猴群來遷就,這個要求也被拒絕了。天氣確實是太冷了,無論是那些被食物誘惑的猴群,還是這群等待觀察猴子的研究者,都失去了運動的欲望。 失去耐性的村民開始往猴群里扔東西,搖晃猴群端坐的樹。奚志農的勸阻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在盡職盡責的村民用了兩個多小時的威逼利誘后,猴子終于屈服了。目睹了這一切后,奚志農拒絕和別人交談,并于第二天下山。 2004年12月29日,他筋疲力盡地回到北京。“我在怪別人,更在怪自己。經驗早就告訴我,真正的野生金絲猴群是絕不可能和人保持這么親密的關系。我卻這樣視而不見,欺騙了自己,還這樣拍攝了那些可憐的猴子好多次。”情緒低落的奚志農自責道。 對于奚志農而言,一次又一次地目睹這樣的事情就像針扎一樣難受:“看到了這一切,我又做了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把這一年多來拍的照片封存,從此不到那個地方。” 20年的拍攝,將奚志農塑造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沉默寡言,身體愈加瘦弱。盡管已經下定決心,要拍到無法再拍的時候為止,但在內心里,他對自己所拍攝物種的未來似乎不甚樂觀:“我所能做的,只是盡我個人的最大努力。有些事情,是一個人無法改變的,是注定要發生的。”(李梓)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財富人物 > 正文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企 業 服 務 |
| 股市黑馬:今日牛股! |
| 做女人事業,賺女人錢 |
| 06年暴利項目揭秘 圖 |
| 網絡招商首次揭秘 |
| 2006年最賺錢的行業 |
| 年薪百萬的財富之路 |
| 360行賺錢驚天內幕 |
| 二折提貨,千元做老板 |
| 2006藥界金礦招商指南 |
| 泌尿頑疾——大解放! |
| 最新療法治結腸炎!! |
| 治氣管炎哮喘重大突破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治高血壓獲重大突破! |
| 高血脂!脂肪肝請留意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6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