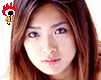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陳燮陽:一切都與音樂有關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1月26日 16:09 《全球財經觀察》 | ||||||||
|
他帶著一只不銹鋼水杯和三支細長指揮棍,輾轉世界各地演出;他在莘莊的別墅里種滿鮮花,閑時愛欣賞花團錦簇。已經65歲的陳燮陽回望自己大半生,一切都是與音樂有關。站到指揮臺上,背對著觀眾的時刻,便是他最沉醉最快樂的時刻 文|蘇德
上海交響樂團在湖南路105號的大院子里,甬道兩旁布滿喬木群,越走向深處越是平坦的安靜,偶爾從排練廳里傳來斷續的大提琴聲,顯得更為幽謐。下個月,上海交響樂團就要赴臺演出,因此這些天,平均每天5小時的排練時間對每個參演團員而言是逃不掉的,這其中也包括了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陳燮陽。 從排練廳下來的時候,陳燮陽已經滿頭大汗,順勢朝團長室的皮椅上一靠,倦態顯然。接著,他開始修改一張節目單。他脫下眼鏡,湊近了節目單仔細看,一筆一畫地勾勒,格外謹慎,圈畫到自己熟悉的曲目,還不自覺地哼出聲來,像個剛進音樂學院的孩子。節目單搞定后,他順手從面前桌子上拿起一只不銹鋼細長水杯,倒了些水,邊喝邊說:“它跟著我快要跑遍全世界了。” 從外表來看,花白的頭發,精瘦的骨骼,陳燮陽有些吝嗇言辭。但面對面交談的時候,若有些言笑,氣氛也還融洽。問起這幾十年來跟在他身邊最“情深”的東西是什么時,沒想到面前一只普通水杯的“情深度”竟然超過了指揮棒,成了一位指揮家最離不開的物件。 作為一個著名指揮家,陳燮陽個人也會接到很多演出邀請,往往是接連著跑幾個國家,和不同的樂隊合作。無論到哪里,陳燮陽說自己都離不開這只細長水杯,沒有特殊的原因,只是習慣了,到哪兒都帶著,就像是個跟隨自己多年的朋友。而對于指揮棒,他也有自己特殊的喜好,只用得慣材質輕巧的幾支,也隨身帶著,如今常用的那一支跟隨他已有三年光景。“每到一個國家,和當地樂團合作,除了用英文交流外,就是這一支指揮棒,它是我站在舞臺上所有情緒的表達。”他說。 每次出國表演結束后,如果還有休息時間,陳燮陽也會和團員們一起在當地看看,在摩洛哥的海邊散心,在俄羅斯劇院瞻仰。這種旅行演出的日子,給了他工作之外閑散的短暫度假。 現在回想第一次站上舞臺,背對觀眾的情景,陳燮陽還是記憶深刻。 “樂隊指揮和其他成員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必須背對觀眾,但對于身后觀眾的任何一絲風吹草動又要了如指掌。”陳燮陽第一次作為指揮登臺還是在音樂附中念初中的時候。在那之前,他學的是鋼琴和作曲,但學校老師非常敏銳地發現他具有作為樂隊指揮的統領氣質和熟悉各種樂器的長處。后來,陳燮陽自己編寫了一組交響樂,交給班里的同學組成樂隊演奏,自己就做了這個樂隊的指揮,開始將背部對向觀眾,雙臂張開,面朝演奏者。 “當時的感覺很興奮,整個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樂隊里演出時感覺不到的一種緊張又完全隨性的激情。謝幕的時候,當我轉過身去再一次面對觀眾時,如潮的掌聲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給予的滿足感。”陳燮陽說,自己可能天生就是適合做指揮的人。只要站上舞臺,燈光亮起,他就是整個樂隊的領袖,一切都會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后來,即使是背對觀眾,陳燮陽仍然能從演奏廳的安靜程度來洞悉觀眾的反應。“如果臺下的觀眾在演奏過程中出現一些騷動,這很容易影響到臺上整個樂隊。有的時候,觀眾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想咳嗽一下,或者說一句話,這似乎司空見慣。可對于一場演出而言,是很傷的,這時候我必須要用自己的情緒來感染整個樂隊,讓所有的演奏者能夠完全集中精神于我的指揮棒。這就是做指揮家最關緊的地方。” 陳燮陽說,指揮家站上舞臺的那一刻既要無我忘我,又要牢記自己身系整個樂隊,他必須帶著整個樂隊走,駕馭曲譜。因為,即便臺上所有演奏者都進入忘我狀態,完全沉浸于音樂,多年來的條件反射仍然會讓他們“聽命”于一支纖細的指揮棒。所以往往在略顯嘈雜的演奏廳里,他要給整個樂隊的就是一個完全無他的世界,這全然靠他指揮的感染力。 和陳燮陽合作過的演奏家、音樂家很多,大家都知道在排練過程中,他從來不會發火。即使作為交響樂團團長,在日常排練中,他也絕少會對團員發脾氣。 “有的指揮家會罵演奏者,尤其在某段總是排練不好的時候,老出錯。但我不這樣,因為誰不會出錯呢,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到演奏正確了就行。你急,其實他比你更急,因為整個樂隊都等著休息吃飯呢!”這時候的陳燮陽又有了長者慈善的寬容。25年前,當他第一次走進上海交響樂團的大門時,身份已經是這家遠東第一的百年樂團的團長,從那時起,他便將此視為自己的家。現在團里比陳燮陽年齡大的團員也有,對于他們,陳燮陽始終視如長輩,而比自己晚進團的團員則都是他的孩子。這二十多年來,在團里待的時間遠要比在家里多。 這些年,陳燮陽幾乎沒有長時間的假期。每到周末,若是有空,他和愛人都會開車去位于莘莊的別墅。在院子里,陳燮陽種了很多花,每當花開的時候,坐在院子里看繁花錦簇,他說自己心里會有滿足的欣慰,是忙碌過后的恬淡。而唯一愧對愛人的,是陪她的時間太少。 偶爾,陳燮陽還會約上一些朋友在市中心住所附近的咖啡館或者酒吧一起聊會兒天,聊音樂也談人生。音樂已經占去他大部分的人生,這輩子和音樂是脫不了干系了。 在不熟悉的人看來,陳燮陽有些冷漠,說話也比較露骨且苛刻,但他說自己還算是個隨和的人,只是不太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把自己完全打開了給別人看。說起自己的名字,“燮理陰陽,是中國古語里面陰陽調和、百事順暢的意思,念起來也挺威風。”陳燮陽說小時候經常會有老師叫不出“燮”這個字,反倒讓更多的老師記住了這個外表看來性格有些怪怪的孩子。 最后,陳燮陽從辦公桌前站起身來,走回排練廳。在一樓樓梯口,懸掛著一幅巨大的海報,里面的陳燮陽正橫握著一支指揮棒笑對鏡頭。他說這幾年團里的運作經費有近三分之一需要靠演出來籌集,因此作為一團之長要當好這個家,還真不容易。 當推開排練廳大門的時候,里面獨坐著一位拉大提琴的演奏者,抬起頭來看到陳燮陽,叫了一聲:“陳老師。” “你剛才有個音拉錯了。”陳燮陽露出寬藹的笑容,走過去,站上指揮臺,翻開樂譜。用手一邊比畫一邊哼唱,即使演奏席上的其他座位空空如也。 上海交響樂團在湖南路105號的大院子里,甬道兩旁布滿喬木群,越走向深處越是平坦的安靜,偶爾從排練廳里傳來斷續的大提琴聲,顯得更為幽謐。下個月,上海交響樂團就要赴臺演出,因此這些天,平均每天5小時的排練時間對每個參演團員而言是逃不掉的,這其中也包括了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陳燮陽。 從排練廳下來的時候,陳燮陽已經滿頭大汗,順勢朝團長室的皮椅上一靠,倦態顯然。接著,他開始修改一張節目單。他脫下眼鏡,湊近了節目單仔細看,一筆一畫地勾勒,格外謹慎,圈畫到自己熟悉的曲目,還不自覺地哼出聲來,像個剛進音樂學院的孩子。節目單搞定后,他順手從面前桌子上拿起一只不銹鋼細長水杯,倒了些水,邊喝邊說:“它跟著我快要跑遍全世界了。” 從外表來看,花白的頭發,精瘦的骨骼,陳燮陽有些吝嗇言辭。但面對面交談的時候,若有些言笑,氣氛也還融洽。問起這幾十年來跟在他身邊最“情深”的東西是什么時,沒想到面前一只普通水杯的“情深度”竟然超過了指揮棒,成了一位指揮家最離不開的物件。 作為一個著名指揮家,陳燮陽個人也會接到很多演出邀請,往往是接連著跑幾個國家,和不同的樂隊合作。無論到哪里,陳燮陽說自己都離不開這只細長水杯,沒有特殊的原因,只是習慣了,到哪兒都帶著,就像是個跟隨自己多年的朋友。而對于指揮棒,他也有自己特殊的喜好,只用得慣材質輕巧的幾支,也隨身帶著,如今常用的那一支跟隨他已有三年光景。“每到一個國家,和當地樂團合作,除了用英文交流外,就是這一支指揮棒,它是我站在舞臺上所有情緒的表達。”他說。 每次出國表演結束后,如果還有休息時間,陳燮陽也會和團員們一起在當地看看,在摩洛哥的海邊散心,在俄羅斯劇院瞻仰。這種旅行演出的日子,給了他工作之外閑散的短暫度假。 現在回想第一次站上舞臺,背對觀眾的情景,陳燮陽還是記憶深刻。 “樂隊指揮和其他成員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必須背對觀眾,但對于身后觀眾的任何一絲風吹草動又要了如指掌。”陳燮陽第一次作為指揮登臺還是在音樂附中念初中的時候。在那之前,他學的是鋼琴和作曲,但學校老師非常敏銳地發現他具有作為樂隊指揮的統領氣質和熟悉各種樂器的長處。后來,陳燮陽自己編寫了一組交響樂,交給班里的同學組成樂隊演奏,自己就做了這個樂隊的指揮,開始將背部對向觀眾,雙臂張開,面朝演奏者。 “當時的感覺很興奮,整個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樂隊里演出時感覺不到的一種緊張又完全隨性的激情。謝幕的時候,當我轉過身去再一次面對觀眾時,如潮的掌聲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給予的滿足感。”陳燮陽說,自己可能天生就是適合做指揮的人。只要站上舞臺,燈光亮起,他就是整個樂隊的領袖,一切都會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后來,即使是背對觀眾,陳燮陽仍然能從演奏廳的安靜程度來洞悉觀眾的反應。“如果臺下的觀眾在演奏過程中出現一些騷動,這很容易影響到臺上整個樂隊。有的時候,觀眾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想咳嗽一下,或者說一句話,這似乎司空見慣。可對于一場演出而言,是很傷的,這時候我必須要用自己的情緒來感染整個樂隊,讓所有的演奏者能夠完全集中精神于我的指揮棒。這就是做指揮家最關緊的地方。” 陳燮陽說,指揮家站上舞臺的那一刻既要無我忘我,又要牢記自己身系整個樂隊,他必須帶著整個樂隊走,駕馭曲譜。因為,即便臺上所有演奏者都進入忘我狀態,完全沉浸于音樂,多年來的條件反射仍然會讓他們“聽命”于一支纖細的指揮棒。所以往往在略顯嘈雜的演奏廳里,他要給整個樂隊的就是一個完全無他的世界,這全然靠他指揮的感染力。 和陳燮陽合作過的演奏家、音樂家很多,大家都知道在排練過程中,他從來不會發火。即使作為交響樂團團長,在日常排練中,他也絕少會對團員發脾氣。 “有的指揮家會罵演奏者,尤其在某段總是排練不好的時候,老出錯。但我不這樣,因為誰不會出錯呢,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到演奏正確了就行。你急,其實他比你更急,因為整個樂隊都等著休息吃飯呢!”這時候的陳燮陽又有了長者慈善的寬容。25年前,當他第一次走進上海交響樂團的大門時,身份已經是這家遠東第一的百年樂團的團長,從那時起,他便將此視為自己的家。現在團里比陳燮陽年齡大的團員也有,對于他們,陳燮陽始終視如長輩,而比自己晚進團的團員則都是他的孩子。這二十多年來,在團里待的時間遠要比在家里多。 這些年,陳燮陽幾乎沒有長時間的假期。每到周末,若是有空,他和愛人都會開車去位于莘莊的別墅。在院子里,陳燮陽種了很多花,每當花開的時候,坐在院子里看繁花錦簇,他說自己心里會有滿足的欣慰,是忙碌過后的恬淡。而唯一愧對愛人的,是陪她的時間太少。 偶爾,陳燮陽還會約上一些朋友在市中心住所附近的咖啡館或者酒吧一起聊會兒天,聊音樂也談人生。音樂已經占去他大部分的人生,這輩子和音樂是脫不了干系了。 在不熟悉的人看來,陳燮陽有些冷漠,說話也比較露骨且苛刻,但他說自己還算是個隨和的人,只是不太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把自己完全打開了給別人看。說起自己的名字,“燮理陰陽,是中國古語里面陰陽調和、百事順暢的意思,念起來也挺威風。”陳燮陽說小時候經常會有老師叫不出“燮”這個字,反倒讓更多的老師記住了這個外表看來性格有些怪怪的孩子。 最后,陳燮陽從辦公桌前站起身來,走回排練廳。在一樓樓梯口,懸掛著一幅巨大的海報,里面的陳燮陽正橫握著一支指揮棒笑對鏡頭。他說這幾年團里的運作經費有近三分之一需要靠演出來籌集,因此作為一團之長要當好這個家,還真不容易。 當推開排練廳大門的時候,里面獨坐著一位拉大提琴的演奏者,抬起頭來看到陳燮陽,叫了一聲:“陳老師。” “你剛才有個音拉錯了。”陳燮陽露出寬藹的笑容,走過去,站上指揮臺,翻開樂譜。用手一邊比畫一邊哼唱,即使演奏席上的其他座位空空如也。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財富人物 > 《全球財經觀察》2004 > 正文 |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