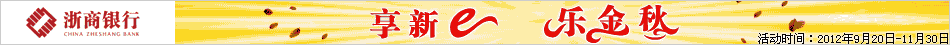奶源爭奪戰:這仍舊是巨頭們的游戲
 21世紀商業評論封面。
21世紀商業評論封面。
作者:羅東
內容導讀:對于大牧場,每個人都有意見,但是沒有人喊停。
自有牧場,對于乳業巨頭們而言,成了一種經營必備的“儲備金”。
在大牧場大勢所趨的背景下,230萬郭建軍這樣的個體奶農何去何從?熟悉北美大工業化奶牛養殖路線的蘇浩擔心,如果只是讓缺乏資本和技能的奶農退出行業,到了2030年,這個行業里將沒有農民只有產業工人。
牧場!大牧場!私家大牧場!
這場始于2009年、于今年上半年已幾近烈火烹油的大牧場熱潮,參與者囊括了伊利、蒙牛、三元、光明、完達山、雅士利、雀巢、新希望等幾乎所有一二線乳企全員,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完工的大牧場已超20個,已公布未來計劃投資總額過百億元。
2007年夏天,北京東石北美牧場科技股份公司(下稱“東石公司”)總經理蘇浩在流火的南京參加奶業展覽時,看著手中伊利高管的名片還很茫然。作為一家提供牛舍的床墊以及相關的牧場設備的專業公司,他在北美和加拿大的客戶幾乎是一水的牧場主。為什么會有一家奶制品公司關注他的展臺?困惑一閃而過。
但很快,他發現這張令人疑惑的名片背后是一個新的利基市場,“這些單純的乳品加工商從來沒有建造大型牧場的經驗,那時,他們正急著尋找能夠提供牧場管理的服務商”。
忽然蜂擁而入的牧場建造者正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為重建行業信用而焦頭爛額的乳企們。2008年11月,國家發改委、農業部、工信部等13家部委聯合制定的《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要求到2011年10月底前,乳制品生產企業基地自產生鮮乳與加工能力的比例要達到70%以上。
自有牧場,對于乳業巨頭們而言,成了一種經營必備的“儲備金”。
乳業巨頭們開始以可媲美當年“蒙牛速度”的宏大氣魄開出自建牧場清單:
蒙牛通過與現代牧業參股、合建了14座萬頭以上超大型牧場,并許諾未來5年再投35億元建20-30座大型牧場。
伊利通過上市公司定向增發募集資金超過35億元,2011年投資14億元自建牧場7座,2012年計劃再投入12億元。
光明斥資7億元在湖北、河北等建造3個大牧場。
三元公布未來3到5年將投資超過20億元興建大牧場。
新西蘭乳企恒天然則專注地在河北籌劃它含有5個牧場的超大牧場群,總計奶牛15000頭,年產奶量1.5億升,最后一期資金專項投資5.57億元都已確定。
甚至連在全球運營中一貫堅持集中于乳品加工環節、不進入上游奶源的食品加工商雀巢,也疑似感染了牧場熱,開始涉足產業鏈上游。今年6月,雀巢在傳統奶源基地黑龍江雙城投資25億元,為奶牛飼養培訓管理中心配備了從1520頭牛的奶牛小區、1200頭牛的大型農場到8000頭牛的超大農場三種型號的培訓牧場。
又見巨頭 又見資本
這仍舊是巨頭們的游戲,但卻是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游戲。
2009年10月,當蒙牛宣布在四川眉山投資3億元建立的生產基地竣工時,僅60公里之外便是同時投產的現代牧業投資3.4億元建造的洪雅現代牧場。如此明顯的同進同退意味著這對上下游盟友將攜手對抗西南戰場上的最大對手——擁有10萬頭奶牛的新希望和控制重慶地區90%以上奶源、并宣布將新建50個牧場和小區的重慶天友乳業。
第一代乳業巨頭們的勝出之道,在于輕,在于所謂專注。出走伊利的牛根生在資金寥寥的情況下發明了影響中國乳業長達十幾年的“先建市場后建工廠”模式,連工廠都可以租用,遑論牧場。讓奶農養牛、奶站收奶、租賃工廠、集中資金做市場,這一模式令蒙牛脫離地心引力一般獲得超越式增長,其靈活、輕盈和杠桿能力令大多以“牧場-工廠-品牌”模式按部就班經營發展的地方乳企和農墾出身乳企望塵莫及。
越來越多的中國乳企開始模仿和追隨,它們剝離了身上沉重的、帶有農業要素的負累,如新希望、三元這樣依舊拖著牧場甚至飼料草場前行的乳企并不常見。然而,在三聚氰胺事件后,對供應穩定、原料安全的迫切需求是幾乎所有乳企不可回避的挑戰。是否擁有安全的、品質穩定的、可追溯的自有奶源,將會是下游加工企業未來的行業準入門檻。
中國在養殖和種植的環節,至今散落著各種小農作業方式,尚未形成媲美歐美的大型現代農業企業。乳企要想獲得安全優質的奶源,必須從加工的環節進入上游的奶牛養殖環節,牧場更是成為乳業市場競爭中的核心配置。客觀地說,這也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拉動奶源從舊石器時代進入現代化的產業力量。
早已習慣全國市場一盤棋的乳業巨頭們,此次主導驅動的牧場興建大業,自然具有高舉高打的風范。內蒙、新疆、東北、河北四大黃金奶源帶上,乳企們的私家領地標簽早已層層疊疊;新興奶源帶河南和四川也已被陸續分割蠶食,甚至以往并非奶源戰略要地的云南、安徽等業已戰火連綿。
以現價計算,建設一個萬頭牧場最低要1.5億元資金投入,據三元和現代牧業的牧場承建方四方力歐的估算,7年回收成本是一個合理預期,而東石的估算亦在6至10年之間。單憑乳企自身的實力和經驗,面對資本密集型的大牧場也難免肌無力。
由政策驅動的奶牛養殖產業整合、2008年之后的中小乳企兼并倒閉潮、將持續倍增的市場需求,資本毫不掩飾期望從乳企吞并、重塑上游奶源的趨勢中獲益的意圖。
2009年,乳業尚未從丑聞中完全恢復,資本卻早已高調介入。7月中糧集團與厚樸基金61億港元入股蒙牛,8月紅杉資本以6300萬美元入股飛鶴,9月凱雷和復星入資持有雅士利23.3%的股權,現代牧業與蒙牛簽署10年有條件獨家供應合約……產業資本、風險基金紛紛注入乳企,而其中,奶源、牧場更是成為焦點。
繼生豬之后,奶牛成為又一個令資本聞風而動的經濟動物,至少他們在萬得妙的崛起中看到機會。
異軍“萬得妙”
兩小時車程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邵祈能在一大早把凌晨新鮮“出爐”的鮮牛奶送到北京太平洋百貨的貨價上。由于拒絕采用“食品罐頭式”的加工方式,他的鮮牛奶只有10天保質期。
在這個一袋牛奶2元多錢、保質期48天的時代,邵祈是個異類。他在距離北京很近的河北三河市創建了華夏畜牧牧場,這個現規模8000頭的大牧場,算是北京周邊較早出現的現代化大牧場。雖然它每天只能生產29噸牛奶,但是早已實現乳業巨頭們在建造大牧場時心里隱隱懷抱的夢想:進入被進口牛奶壟斷的高端市場。
華夏牧場大部分產出被各大牛奶廠商訂購制作高端奶,哈根達斯緊鄰它設廠便是看中其優質奶源,大約3%的原奶貼上他創建的牛奶品牌“萬得妙”進入終端銷售。萬得妙只賣采用巴氏殺菌的鮮牛奶,只有全脂牛奶、脫脂牛奶、含糖酸奶和不含糖酸奶四種,主要在北京高端的咖啡連鎖店、餐廳及酒店、面包房和部分高端超市銷售。
邵祈是個做IT起家的美籍臺灣人, 性情冷靜,幾乎看不到任何戲劇性的部分,他并不會像其他同行那樣喜歡談論如何讓一年銷售額翻一倍的大想法。但在大牧場被視為“可剝離資產”的2004年,邵祈在河北三河盤下330畝地作為養牛場,還有300畝地用來儲存牛的食物青貯飼料和苜蓿,1200畝地種玉米,開始了從飼料源頭玉米到生產牛奶的養牛大業。
前期籌備時,他花了半年時間考察當地的生態環境。他看到的場景“慘不忍睹”:當時,中國的奶牛大部分處于散養狀態,牛就睡在牛糞上。牛奶緊俏時,農民擠完一桶奶擺在屋外就有人來收。桶上只蓋一層紗布,上面飛滿蒼蠅。“我們當時的感覺是:中國的養牛業至少落后西方50年。”
這并不是個刻薄的判斷,落后50年,是外界對中國奶牛養殖業落后程度的普遍評價。其實,在20多年前,大多數城市周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當地乳企擁有的小型規模化牧場。但伊利、蒙牛憑借保質期長達幾個月的液態奶產品可以在常溫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運送,極大地克服了運輸與銷售半徑的限制,侵入全國各地市場。很快,在大品牌的擠壓下,很多地方性乳企紛紛破產或被并購,當地牧場的發展越來越退居次要。
華夏畜牧的應對之策很簡單,舍得花錢給牛喂貴價的優質飼料,從擠奶到包裝上架全程維持高標準作業和恒定低溫。2006年,華夏牧場開始經營自有乳制品品牌“萬得妙”,“當第一批成品出來的時候,奶的細菌值只有幾千個,而中國現在的標準一毫升里面200萬的細菌便是合格的。”
500ml萬得妙全脂鮮奶的零售價約為17元人民幣,比其他品牌的高端奶還要貴30%。但是,在消費者的權衡中,與萬得妙比價的是來自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法國的進口牛奶,而并非蒙牛和伊利。截至2011年5月,中國進口常溫奶達6000-7000噸,而2008年以前,“洋牛奶”的進口量一年僅有2000-3000噸。
在乳業巨頭坐視進口牛奶抓住食品安全危機占領中高端市場之際,一批本土的優質牧場抓住了這一機遇,作為“洋牛奶”的本土替代品,打造一批不做品牌推廣、小眾口碑傳播的“無印良品”。
東石,無心插柳
蘇浩是邵祈之外的又一個獲益者。
蘇浩是規模牧場的推崇者,但他也無法回答:中國乳業由大躍進式的市場擴張導致的問題,能夠通過大躍進式的奶源建設來彌補嗎?2007年以來,找上門的客戶開始變多,他發現并非所有公司都意識到從“爬坡忽然切換到攀巖”的難度和危險。這一被巨額資本和宏大規劃忽視的技能鴻溝,被他視為東石的利基。
他的第一步轉型,是從設備供應商變為“來自北美的牧場專家”。他這樣描述當時東石的典型客戶:大批20多歲的年輕人,高學歷,理工科背景,沒有動物養殖經驗,沒有參加過農業生產。原本在乳企中是最活躍的中堅力量,被派往上游牧場,希望開拓第二個職業戰場。但對于建造牧場所需要的兩項基本技能:養牛和建筑,可謂一片空白。
在前期,東石的專家主要任務就是跟這些五谷不分的年輕人講授什么叫動物福利,什么叫奶牛舒適度,怎么樣讓奶牛舒服地臥下來,提高產奶量,更不要說學科交叉,地面為什么做防滑槽,牛如果滑倒是前后滑還是側滑……
然后,他發現這些急于在三五年內完成一個宏大目標的客戶,需要的并不是一個教師。
牧場是一個復雜性不亞于小城鎮的系統,設備、建筑、軟件、硬件缺一不可。萬頭牧場奶牛養殖不僅對地理環境、飼料、水源、物流運輸等要求很高,對環境的承受能力也有嚴格要求。即便是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人少地廣,青貯飼料豐富,適合大規模養殖,這些國家平均每個牧場奶牛養殖也不過幾千頭;而人多地少的荷蘭,單體牧場奶牛存欄通常只有幾百頭。唯一可資借鑒的超大牧場經驗來源是美國南部高度工業化的奶牛養殖方式。
工業化的正面是效率,背面則是違反自然規律所帶來的風險。將數千乃至上萬頭奶牛集中飼育,像流水線一樣喂養、擠奶、活動,在短時間內掌握牛的飼養、牧場建設以及飼料種植,足以令乳業巨頭們手忙腳亂。無論大牧場是否科學可行,速成都導致中國近幾年新建的大牧場比國外同行更為脆弱。據媒體報道,到2011年底,大牧場建造最為活躍的現代牧業旗下安徽馬鞍山牧場、肥東牧場、山東汶上牧場皆出現沼液污染問題。中國大多數牧場管理團隊在生物防疫、污染物處理等方面尚缺乏經驗。“如果這些環節再出現問題,行業還會經歷陣痛。如果處理不了,回過頭來,還是會直接影響食品安全。”蘇浩說。
圍繞這場飛速發展的乳業大牧場風潮,設備、飼料、牧草、醫療、育種行業的機遇隨之而來,但也考驗著它們面對這群客戶隨機應變的能力。
在與6家美國不同專業的公司合并后,東石推出了整體交付服務,從規劃設計、建造、設備配套到運營培訓服務,直到奶牛進場甚至擠出第一滴奶,才算完成。在全球高度專業化細分的環境下,東石卻在一片空白的中國市場變成了牧場建設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商。在完成了華夏、好一多、恒天然的牧場建設之后,它剛剛接下了雀巢雙城奶牛飼養管理培訓中心的牧場建設工程。
農墾派的猶豫
在上一個乳業奇跡輩出、激情燃燒的年代,三元和完達山這類有著農墾血緣的公司,始終都無法成為最長袖善舞的那個。
種種機制困擾和無法甩脫的牧場,成為它們沖擊全國性乳企的障礙。但到了以自家牧場論短長的刻下,它們又陷入另一種猶豫的情緒:作為長年運營牧場的乳企,它們正在學習如何“單純”地將牧場視為可以憑借資本和資源“運作”出來的棋子。
在一二線乳企當中,三元幾乎是最晚公布建立大牧場計劃的一個。
2008年,三元是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最干凈地脫身的乳業品牌,原因正是其對奶源的掌控力。前身便是北京奶站的三元有50多年養牛歷史,其體制原因使得它仍然保持著一部分國營農墾農場的色彩。在其他乳企憑借在市面上四處采購原奶快速擴張時,三元80%的奶是來自北京周邊的30多個自有牧場,剩下的20%則來自長期合作的大規模牧場。
然而令人尷尬的是,三元雖然在別人深陷丑聞時證明了自己的質量和信用,但在別人快速走出泥沼的時候,它的質量和信用卻沒有轉化成營業額和利潤。2010年,乳業出現全面復蘇,伊利年盈利8億多元,蒙牛的利潤高達14億多元,然而三元的利潤則只有7000萬元。
將口碑變現,就需要足夠的產能作為依托。一直在什么才是可持續的發展速度這個問題上糾結的三元,終于公布計劃:在未來3到5年,興建超過10萬頭的牧場,直接投資超過20億元。
從哈爾濱出發乘坐13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到密山縣,轉半個小時大巴到楊樹河子鎮,再驅車半個小時,就能達到完達山的8511農場雙峰牧場。背靠北大荒墾區的完達山建設牧場,也許是最不愁土地、員工和飼料種植田的乳企。
“大牧場?一萬頭牛?不靠譜!”完達山乳業副總經理余寧江聊到“萬頭牧場”時,神情忽然有些“粗暴”,“如果設定一個牧場的奶牛存欄數上限,5000頭就差不多了——當然,規模化牧場一定是我們掌控奶源的重要方向,我們也在摸索。”
去年產能80萬噸、營業額42億元人民幣的完達山目前擁有千頭以上規模牧場50多個,多分布在地廣人稀的黑龍江墾區。雖然對伊利近乎自己10倍的營業收入羨慕不已,但完達山卻遲遲沒有大肆建造萬頭大牧場。因為,“仍然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 。
占地45萬平方米的松北牧場是完達山全資興建的“萬頭奶牛示范牧場”,盡管號稱“萬頭牧場”,但實際奶牛存欄數在5000頭左右。“這是一個相對合理的數字”,牧場所在地區的承載能力有其上限,理論上,即便是圈養,一頭奶牛也需配備3-5畝的土地種植飼料。為了喂飽5000頭牛,松北牧場在周邊大約以每畝380元的價格租種了6000畝地,訂單種植的面積還有4000多畝地。雙峰牧場地廣人稀,配套土地不成問題,但缺乏有糞便處理能力和技術的工廠。
農墾派對自建大規模牧場的瞻前顧后,使得它們成為在自有牧場上先發而遲行的一群。
他們又在講故事
很多乳企的大牧場夢還沒開始,飛鶴的大牧場夢便結束了。
2011年8月,飛鶴乳業宣布,售出位于黑龍江的飛鶴克東養殖場和飛鶴甘南飼養場全部股權,售價1.318億美元,資產中包括1780萬美元的現金和六個季度的生鮮奶供給。
在乳企當中,飛鶴以“全產業鏈模式”聞名,覆蓋飼料種植、奶牛飼養到奶粉生產加工圈鏈條。在大多數乳企還沒有從三聚氰胺中緩過神來,它便已宣布5年內投資50億元建立4個加工基地和10個萬頭原生態牧場,將奶源中牧場奶所占的比重提升到100%。2009年8月,成功由中小板轉至主板的飛鶴與紅杉資本簽訂了“苛刻”的對賭協議,同時獲得了后者6300萬美元的資本注入。
短短兩年,長于管理牧場卻拙于資本游戲的飛鶴便付出了代價。對賭失敗,股價下跌,接踵而至的是引以為傲的牧場被出售,10個萬頭牧場的計劃也銷聲匿跡。這場資本游戲的唯一贏家便是接盤者哈爾濱本地資本Haerbin City Ruixinda Investment Company,比起緊鄰這兩家投資額分別為8億元和12億元的牧場,這家并無奶牛養殖經驗的公司的價格相當合算。
然而另一家將萬頭大牧場作為資本故事核心素材的公司則講述得風生水起。
現代牧業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這家由蒙牛原高管鄧九強創建的牧場運營公司是蒙牛的最大供應商,蒙牛同樣是其最大的客戶,占據其九成以上銷量,雙方訂立有從2008年10月開始的10年承購原料奶供應協議,同時引入的還有來自KKR、鼎暉投資及Brightmoon的四輪股權融資。
萬頭牧場概念迎合了資本市場的期待,從2005年成立到2010年上市,5年中,現代牧業在國內已建成11個大型牧場,約7.2萬頭奶牛。
2005年,現代牧業計劃建第一個萬頭牧場時,便計劃5年收回成本。事實證明,這并非不可能,該牧場總投資2.5億元,但現代牧場的直接投資僅為4000萬元,剩余1.9億元分別來自馬鞍山市農發行貸款和馬鞍山財政配套補貼和項目資金。
地方政府為了爭奪大牧場落戶當地,土地免費使用、修建配套道路、購牛補貼、水、電、糞污處理、防疫、擠奶及飼料基地等配套設施和各項補貼不一而足。
通過借助資本、整合資源,現代牧業的增長速度驚人。截至2011年12月31日,現代牧業擁有16個運營的萬頭規模牧場及4個在建的畜牧場,飼養總共12多萬頭乳牛。同期公司凈利潤同比增加322.7%,但按照其牛奶銷售額11.13億元平攤計算,平均每個牧場盈利只有1000多萬元。而同期,現代牧業獲得政府補貼收入卻高達8870萬元。
2015年前,它計劃建成30個萬頭規模牧場,奶牛存欄超過26萬頭。
奶農的憂傷
郭建軍蹲在綠源奶牛基地門口,茫然地望著200米外,自己土生土長的村子,“2008年的時候一頭奶牛能掙個3000到4000元。但這幾年收奶價格沒提高,飼料錢不斷上漲,算起來我還不如出去打工。” 雙鴨山甚至整個佳木斯地區近年來基建工程增多,一名好的技工日薪可以達到300元。
綠源基地是完達山的散戶集中飼養點,巔峰時期大約有300多頭奶牛。由于企業和散戶之間矛盾重重,越來越多的散戶放棄繼續養牛,如今大部分牛舍空空如也。
這里昔日上演的糾葛,是大多數奶農和乳企之間的恩怨一般無二。散戶抱怨奶站的檢測程序不透明,收購價格波動無標準,養牛辛苦利潤薄,至于防疫、消毒、如何通過飼料合理搭配增加牛奶中營養成分的含量,很少有人教他這些。企業則抱怨這種人工擠奶、不算科學的儲存方式、讓鮮奶時常暴露在空氣中的作坊式產奶,給奶源的安全性帶來了諸多風險。
原先便找不到那個傳說中的“利益共同點”的供應鏈條,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終于崩裂。 與此同時,企業也越來越重視奶源的嚴格掌控,在幾乎所有奶源規劃方案上,規模化牧場和自有牧場都正在將散戶奶農逐漸擠出供應網絡。
目前,完達山來自規模牧場、奶農小區和散戶的奶源比例大約是20 : 50 : 30,但完達山并不敢輕易說出“放棄散戶”,大規模農戶喪失生計造成的惡劣影響不可小視。它提出希望散戶們向奶農小區和個人牧場發展,算是一個“折中方案”。
奶牛小區和其他類似的替代形式,意味著這些奶農正逐步向產業工人轉移。
在大牧場大勢所趨的背景下,230萬郭建軍這樣的個體奶農何去何從?熟悉北美大工業化奶牛養殖路線的蘇浩擔心,如果只是讓缺乏資本和技能的奶農退出行業,到了2030年,這個行業里將沒有農民只有產業工人。
“這股乳企圈地、奶源私有化的風潮是工業推動乳業,把農民排斥在奶業現代化之外。資本是跟著機會走的,農民是跟著土地走的。作為依靠土地的第一產業,牧場行業真正要做好,需要保留對牛和土地有情感聯系的農民能夠長久地留在這里。”蘇浩說。現在很多企業尤其是行外資本推動的大牧場,在建造時將奶農草率邊緣化,等于將長期的養殖風險也壓在自己頭上。
郭建軍對于自己是否被財大氣粗的牧場投資者邊緣化的問題并不關心,但他還是想堅持養一陣子牛再說:“等等看,是不是還有什么政策。”與此同時,他想先弄些副業,在他家院子里,六只鎖在籠子里的藏獒狂吠,幾只幼年藏獒歡快地在院子里撒歡兒,“它們品種不好,我和我哥合伙養著玩。”郭建軍訕訕地解釋。
|
|
|
|